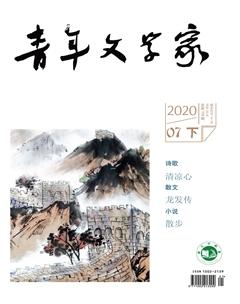小說中人物塑造雙重脈絡的相輔相成
摘? 要:遲子建是一位黑龍江籍女作家,在她的小說《晚安玫瑰》中以俄羅斯風情濃郁的哈爾濱市為背景,講述了一個身世離奇的女子在尋父又殺父的過程中發生的一段人間悲歡。在這部作品中,遲子建在這部作品中每塑造兩個人物,都會用兩種不同的故事脈絡聯系起來。看似不同,又仿佛雙軌并行般在講述同一個故事,凸顯作品想要表達的觀點。這種頗具特色的寫作手法使得人物塑造更加鮮活深刻,讓作者表達的觀點更加完整清晰,值得借鑒。
關鍵詞:人物塑造;雙重脈絡;相輔相成
作者簡介:張園(1980.12-),女,滿族,遼寧省錦州市人,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為現當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21-0-02
一、涼生枕簟淚痕滋——兩個扭轉人生的“弒父”故事
這部作品中有兩個身世曲折的女性主要人物角色:趙小娥和她的房東吉蓮娜。一個因為對利益的貪婪,而犧牲女兒愛情、出賣女兒被下了砒霜毒殺的繼父;一個因滿足私欲,造成母女凄慘人生的強奸犯,被逼跳河的親生父親,他們都是因為自私傷害了女兒,從而被復仇。中國傳媒大學博士后周麗娜在《“弒父”的玫瑰:一個嶄新的兩性故事——評遲子建新作<晚安玫瑰>》認為吉蓮娜和趙小娥的復仇都源于男權施加于她們身上的巨大屈辱,“弒父”則是擺脫屈辱的方式和選擇。繼父與生父帶來的傷害,影響了她們的婚戀觀和生活方式。[1]
作品中塑造的兩個本毫無關聯的女性人物,她們身世的秘密相伴而生。不同的是,趙小娥沒有懺悔之心,在吉蓮娜眼里是“看不到另一個世界的曙光”的表現;而吉蓮娜認為自己的弒父行為是洗刷自我的罪惡,見到小林扮的摩西,坦然離世。趙小娥的弒父行為使她童年的噩夢有了一個了斷,可真正實施之后,她并沒有獲得真正的解脫,直到吉蓮娜離開之后,她意外得知了吉蓮娜的遺囑,才對父親產生了懺悔。[2]
兩個有著極其類似的經歷的女性,秘密的共享讓她們的心靈再一次靠近。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的王海文在《弒親者的迷失與救贖——論遲子建的<群山之巔>和<晚安玫瑰>》中認為,弒父行為代表著女性對父權的一種反抗,無論是吉蓮娜的繼父或是趙小娥的生父,在她們人生的初期階段都是“缺席”的,這種缺席對情感的維系造成了一種隔閡和割裂。[3]不同的是吉蓮娜懷著懺悔之心將這段痛苦的往事藏于內心,而趙小娥卻從最初的痛快到后來的自我折磨,始終無法擺脫罪惡。
西華師范大學文學院的張潔在《冰雪世界中的血色玫瑰——淺析遲子建<晚安玫瑰>中的女性形象》中認為吉蓮娜的弒父罪惡在宗教關懷下得到救贖,趙小娥復仇的罪惡卻成了她的煎熬。[4]雖然作者不吝強調宗教的力量,但內心的力量與觀念的不同才是兩位女主不同人生態度的主要原因。
二、花褪殘紅青杏小——兩段向現實投降的愛情
在趙小娥遇見真愛齊德銘之前,作者交代了她的兩段愛情,一個是她在大學時代的初戀——陳二蛋,一個是工作后認識的宋相奎。不管是淳樸實在的大學同窗,還是貌不驚人的宋相奎,他們一邊喜歡女主,一邊選擇向現實低頭,選擇了家里認為的能生娃的女人和在哈爾濱本地有房子的啞女。兩次失敗的愛情,讓趙小娥渴望關愛的心越來越冷,讓她對后來偶然邂逅的齊德銘無比地上心,而齊德銘的猝然離世自然也對她的打擊十分刻骨。
三、重泉一念一傷神——兩種面對死亡的人生態度
小說中對于死亡的描述貫穿了作者對于死亡的態度,而作家在作品中往往又融合自己人生經歷所造就的觀念,比如遲子建因為在現實中丈夫的猝然離世,她對于死亡的描述既向往平和地接受,又無法擺脫突如其來的極端恐懼。這種心態在小說中塑造的兩個人物形象齊德銘和吉蓮娜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齊德銘作為一個經常需要出門在外的銷售工作者,作者交代他的母親是因為照顧病重的爺爺而累得猝死,齊德銘的父親意外入獄多年來一直懷念他的母親,并且有著很多懷念的方式,比如清明供奉紅皮蛋、插柳枝,七月十五放河燈、撒玉米粒,用這種方式讓齊德銘也相信另一個世界的存在。母愛的缺失和父親跌宕的人生讓他對死亡有著偏激的恐懼,又似乎在平靜地時刻準備迎接它的到來。為此,他在行李箱里備了一件壽衣,可是當趙小娥提問萬一發生事故,和壽衣一起灰飛煙滅,該怎么辦的時候,齊德銘暴怒的反應正說明他對于死亡的恐懼。
而吉蓮娜對于死亡比齊德銘多了更多的淡然,即是多了幾十年人生的賜予,又和她的宗教信仰有關。她經常閱讀猶太經書,并向趙小娥描述她心目中的神——摩西。當趙小娥向吉蓮娜講述夢境中見到的摩西形象的時候,吉蓮娜的驚呆也證明了她對此更加深信不疑。因此她找好律師,立了遺囑,對身后事做了詳細的安排。人生的閱歷和年歲的增長給予了吉蓮娜面對死亡而具備從容的力量,她堅信死后有另一個更加美好的世界。
鐲耳在《讀遲子建<晚安玫瑰>有感:一個為精神而活著的人》中認為,吉蓮娜是一個為精神而活著的人,她是一個經歷非凡的歲月老人,是一個有信仰的女人,是宗教和愛的力量驅散了她心中的陰霾。景德鎮陶瓷學院的何芹、李新青在《救贖與皈依——評遲子建的中篇小說<晚安玫瑰>》中認為,小說背后蘊含的精神世界和宗教問題顯得格外沉重和發人深省。所以,吉蓮娜的面對死亡的淡定態度,較之齊德銘極端,她的力量源泉除了歲月帶給她人生的洗禮和豐富閱歷之外,就是宗教的力量。
四、一寸還成千萬縷——兩段失去真愛的經歷
小說中的兩位女主人公趙小娥與吉蓮娜都有著遇見真愛又失去的經歷,這樣的經歷對她們兩個人的人生都造成無比巨大的影響,前者終身未婚,后者發瘋進了精神病院。
吉蓮娜的余生都在用儀式感紀念與之相愛的蘇聯外交官:別胸針、梳辮子、去馬迭爾用餐,即便唯一的真愛沒有失而復得,她卻一直沉浸懷念。而趙小娥面對真愛的失去,雖然沒有像吉蓮娜那樣貫穿了一生,但也給予了她致命的打擊:“覺得這個世界一下子變得漆黑”、“走在平坦的街路上,我卻有跋涉在泥濘中的感覺”、“三天不吃飯,也不覺得餓”、“夜涼如水時,我渾身燥熱,而陽光燦爛的正午,我卻冷得打寒顫。”[2]這些刻骨的感受來自于作者丈夫猝死的打擊,她把自己突然失去愛情的感受用于對女主的內心刻畫,生動而精準,讀來真實感刻骨。行超在《遲子建中篇小說<晚安玫瑰>:兩個女人與一座城市》中認為,吉蓮娜再沒有愛上過任何一個人,但她卻始終保持著自己年輕姑娘般對美的熱愛,像玫瑰一樣美麗;而趙小娥的愛情更加接地氣,象征了玫瑰的梨刺。
文中兩處巧合略顯牽強,一是趙小娥在齊德銘父親的工廠里偶遇親生父親,也就是她眼中造成她母女悲劇人生的強奸犯穆師傅,就這樣剛好出現;另一處是齊德銘的父親又恰巧是她閨蜜黃薇娜的情夫,報復性出軌的對象竟然就恰巧是趙小娥男友的父親。這兩處巧合雖然將文中人物都貫穿起來,但不免讓人覺得過于牽強,為了巧合而巧合。
總體而言,遲子建的這部作品細膩而真實地展現了當下社會生活中人們的愛情、親情、友情狀態,并且貫穿著人道主義與宗教主義情懷,雙軌并行的故事敘述也是手法的巧妙之處,不失為一部優秀的作品。
參考文獻:
[1]周麗娜.“弒父”的玫瑰:一個嶄新的兩性故事——評遲子建新作<晚安玫瑰>[J].文藝評論,2013,(9):93.
[2]遲子建.晚安玫瑰[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3:143.
[3]王海文.救贖與皈依——弒親者的迷失與救贖——論遲子建的<群山之巔>和<晚安玫瑰>[J].文教資料,2018,(8):22.
[4]張潔.冰雪世界中的血色玫瑰——淺析遲子建<晚安玫瑰>中的女性形象>[J].名作欣賞,2015,(1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