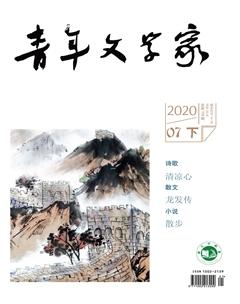從《月落荒寺》談小說的“當代性”與“文學性”
趙靖宏
摘? 要:格非的最新小說《月落荒寺》將視野放在當下的現實生活,從書寫鄉村轉向城市。如何平衡好小說的“當代性”和“文學性”是當下作家們共同面臨的問題,很多致力于“當代性”寫作的作家選擇從荒誕、精彩的新聞事件入手,而格非卻更信任個人經驗,他從自己熟悉的知識分子寫起,通過藝術的手段賦予日常生活神秘性以及多種可能性,在展現這個時代知識分子、中產階級的生存狀態、精神困境,反思人的存在意義的同時也強化了小說的“文學性”。
關鍵詞:《月落荒寺》;現實;“當代性”;“文學性”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20)-21-0-02
格非的《月落荒寺》可讀性很強,敘事行云流水,讀起來令人感到非常順暢,而小說的容量也不容小覷,簡潔有力的結構和語言中蘊含著作者對現實生活多方位的思考。作者深入社會肌理和人性,在對“當下”現實深層挖掘的基礎上建立其小說的“當代性”寫作。
一、小說與現實的距離
文學與現實的關系是一個老生常談話題,我們都知道“藝術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同樣,文學創作不能脫離現實,但又不能等同于現實。蘇童說寫作是“離地三千尺的飛翔”,作家既要以俯瞰的姿態關照現實和人類,又不能離地太遠。好的小說與現實一定是要有距離的,不管是怎樣的想象和虛構,不過是以不同的形式抵達現實,于是,如何讓小說與現實保持恰如其分的距離就成為擺在作家面前的難題。
優秀的作家常常處于和現實的緊張關系中。當小說距離現實較遠時,作家就有了廣闊的施展空間,可以盡情發揮自己的經驗、想象、智慧、激情來創造故事,但同時也容喪失批判性,在與現實的隔閡中淪為自我陶醉的個人狂歡式寫作,比如二十世紀備受追捧的現代主義文學,就因與現實的脫節越來越難以引起讀者的共鳴。可是,一旦小說與現實的距離被無限拉近,甚至“零距離”時,小說的“文學性”又常常是大打折扣的。必須承認,“當代性”寫作中很難看到成熟理想的作品,一般來說,“文學性”較強的小說,往往是那些書寫過去“現實”的歷史小說,而那些直面當下“現實”的小說,又因與現實太近造成審美藝術的沉淪,而且由于“當局者”的身份,很難表現出超越現實的藝術思想。所以,處理好小說“當代性”和“文學性”之間的平衡問題是作家們共同面臨的一大挑戰。
中國作家一直有很強的歷史意識,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出現了如陳忠實的《白鹿原》、路遙的《平凡的世界》、王安憶的《長恨歌》、莫言的《生死疲勞》等史詩級巨著,尤其是80年代成長起來的這批作家,其成長經歷和文學經歷使得他們對民族史和時代變遷有著深切的體會,歷史寫作對他們很多人來說更得心應手,也更容易寫出大格局的作品。
二、小說與新聞的較量
格非坦言,“今天小說寫作面臨兩個方面的壓力,首先是科學使得我們的生活充分暴露,所有的事情都可量化、可分析。另外,新聞和小說一直在較量。”小說本是一種虛構的藝術,作家以非凡的想象力為讀者提供身臨另一個時空的體驗,但我們在贊嘆作家卓越想象力的時候卻往往忽略了一個事實——任何奇特想象力的背后其實都有作家獨特的個人經驗作為支撐。比如,加西亞﹒馬爾克斯的小說,那些在別人眼中的“魔幻”其實就是他的“現實”,與他的人生經歷密切相關。所以,優秀的小說固然離不開作家的想象力和虛構能力,但更離不開作家的個人經驗,更何況在當今這個鬼魅的時代,現實常常比小說更魔幻、更荒誕,很多時候,作者苦思冥想的故事甚至不及新聞報道來得精彩,虛構小說在大眾傳媒時代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機。既然當下的“現實”比小說更荒誕、復雜,那小說直接描摹現實豈不更有效?
現在很流行一種寫小說的方法,從新聞取材,然后作家再進行審美藝術處理,建立小說與現實世界的聯系。余華的《第七天》、劉震云《吃瓜時代的兒女們》也都如此,《第七天》對新聞事件的運用之廣令人瞠目,以致招來“新聞串串燒”的詬病;《吃瓜時代的兒女們》運用新聞的密度雖不及《第七天》,但“幾個素不相識的人”的故事,也幾乎都能從新聞事件中找到原型,小說名稱更是直接用“吃瓜”這一網絡語,體現出小說強烈的新媒體時代特征。80年代這批作家,他們年輕時經歷了文學變革,中年時又經歷了新媒體時代,在巨大的變革和跨越中,他們中很多人的轉型是自覺的,通過新聞素材搭建文學與現實溝通的橋梁,成為了一種自然而然的選擇。
但格非的《月落荒寺》對新聞的運用是很節制的,他更依賴的是個人經驗。格非曾在談加西亞﹒馬爾克斯的文學創作時強調過個人經驗的重要性,“作家的稟賦和想象力、形式的轉換固然可以彌補個人經驗的貧乏,但對于寫作來說,經驗或經歷毫無疑問依然是最為重要的資源”格非身為學院派作家,對高校知識分子再了解不過,他選擇從自己熟悉的群體寫起正是基于對這種可靠的經驗的信任。而這部小說不局限于知識分子群體,圍繞著主人公林宜生,小說生動刻畫了他朋友圈里來自商界、政界、藝術界的各色人物,查海立和趙蓉蓉、李紹基和曾靜、周德坤和陳渺兒三對夫婦,以及白薇、楊慶棠、小布爾喬亞等人,實則是現今中產階段的一個縮影,從這些人物身上可以窺見這個時代中產階級的基本生存狀態。
無論什么時代,作家的地位都是無可取代的。新聞再精彩,再荒誕,也難以實現文學的豐富性。雖然這個時代涌現了大量文筆優秀的新聞工作者、網絡段子手,他們可以寫出精彩紛呈的故事,但是,一個好作家絕不僅限于講好故事,作家需要對現實生活有高于普通寫手的認知,“不僅要講故事,還要創造故事。創造故事就是創造一種生活的可能,這是對作家更高的要求。”能帶給讀者比新聞、比現實本身更多的東西,這是作家的責任和使命。《月落荒寺》除了對知識分子、中產階級生存困境、精神狀態的反思,還可以從多個視角和層面去解讀,比如,林宜生和楚云的感情線中呈現出了現實生活中每個人“重建自我主體性的企圖”以及生活的另一種可能性;林宜生與兒子伯遠從一開始隔閡到最終體諒、和解的過程寄托了作者對年輕一代的關懷與理解。這篇小說既是批判的,也是反思的,格非的寫作不是一種簡單的“對抗式”寫作,而是一種“對話式”寫作,用小說與當下現實在對話和溝通中達成理解,使得這篇小說變得豐富、厚重,耐人咀嚼。
三、小說的陌生化和審美化
小說如何“高于生活”?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賦予小說“文學性”,從敘事方法上來說,要對小說進行陌生化和審美化處理。“荒誕”是作家進行小說陌生化處理常用的手法,現在很多“當下性”的小說寫作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以荒誕手法來反映當代中國社會現實,而這也是由當下現實的荒誕與神奇決定的。但是,這種透過新聞報道間接獲取的信息是“碎片化”的現實,這種不牢靠的經驗所滋生出來的“荒誕”在真實的現實面前是無力的。余華認為當下生活的復雜性很難用一兩個故事能講好,所以他的小說《第七天》里大量塞滿了社會生活各個角落的熱點新聞事件,雖然余華很先鋒地以亡靈視角展開敘事,極盡荒誕敘事之能對小說進行陌生化處理,但通過媒體獲知的新聞由于缺乏真實的生命體驗,使得小說在深度和厚重感上都是有所欠缺的,小說的“文學性”也因此受損。相比之下,格非的《月落荒寺》故事其實并不復雜,但融入了作家豐富的文學經驗、生命體驗和對現實的感知力,把林宜生這個人物刻畫得真實飽滿,對當下現實生活中洞幽燭微。小說里有一個人物與其他人物是不同的,那就是闖入林宜生生活里的神秘女子楚云。楚云和林宜生男女關系的確定是迅速和世俗的,但隨著情節的發展,楚云的性格、身世越來越與眾不同,她不僅懂日本駢句、白居易、帕斯卡爾,還知道德彪西、古爾德、席夫,這樣一個才華橫溢的女性不正是大多數男性知識分子夢寐以求的嗎?但人生的美好總是難以留住,楚云行蹤捉摸不定,最后神秘消失,她的存在無疑給小說營造了神秘的氤氳之氣,她不像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更像是一個美好的幻夢,如同她的名字一樣,“楚云易散,覆水難收”。格非的《月落荒寺》洞悉了現實生活鮮為人知的另一面,挖掘日常生活的詩性和神秘色彩,拉開現實生活更廣、更深的維度,有效增強了其小說的“文學性”。小說以德彪西的樂曲為名,“月落荒寺”,既有一種悲涼落寞之感,又有一抹東方神秘色彩,格非在這一基調下展開敘事,情節的推動、人物的命運與德彪西樂曲空寂的意境相得益彰,使小說藝術審美得到了進一步的升華。陌生化處理是寫小說的基本要素,但一個優秀的作家,還需要給予小說更為復雜的審美化處理。
近期,談起書寫當代知識分子的小說,不能不提到李洱的《應物兄》,李洱出手不凡,該小說一舉拿下第十屆茅盾文學獎。李洱淵博的知識和超高的文化素養在《應物兄》里體現得淋漓盡致,小說里儒學、詩文信手拈來,高深的學術問題的探討筆筆皆是,頗有錢鍾書《圍城》的風韻,其筆下形形色色的人物,知識分子、官員、商人,各階層、各群體,構成一幅浩瀚的當代社會圖景。李洱《應物兄》的大氣闊是有目共睹的,但對于普通讀者來說是有距離的,尤其是小說中大篇幅的學術探討容易令人望而生畏,如果沒有較高的知識儲備,《應物兄》讀起來是很吃力的。而格非的《月落荒寺》雖然也是描寫知識分子生活,但并未過多涉及學術問題,人物間有關文學、藝術的話題也是點到即止,其實,以格非的學識想要深寫下去又有何難,但他的關注點始終放在小說的敘事上、對現實的關照上,因而也更能激發大眾閱讀的激情。小說的語言是由內容決定的,為了拉近與現實的距離,作家用樸素的語言來進行敘事并不比用復雜的語言容易。“當代性”寫作須考慮讀者接受的問題,在增強小說批判性、提高小說文學性的同時也不該忽視讀者的閱讀參與。
參考文獻:
[1]王暢.以“庸常”作為一種方法——從《月落荒寺》看知識階層的價值失落與找尋[J].漢字文化,2019(S2):87-88+100.
[2]林培源.重返小說的神秘性——論格非長篇小說《月落荒寺》的敘事[J].當代作家評論,2020(01):116-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