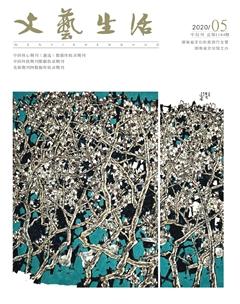紀實是虛構的一種方式
摘要:本文從20世紀50年代邊疆文學的代表作一鄧普《軍隊的女兒》出發,從寓紀實于虛構、化歷史為情節以及從現實到理想三個方面來探討小說中紀實與虛構的關系。
關鍵詞:紀實;虛構;王孟筠
中圖分類號:I207.4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20)14-0010-01
文學以藝術的方式對現實和歷史進行敘述。這種“藝術的方式,可以是虛構的,也可以是紀實的。小說通常被認為是一種虛構的文本,但也會受到紀實的深刻影響。
一、寓紀實于虛構一從王孟筠到劉海英
小海英,14歲從湖南自愿支邊來疆,來到了八一軍墾農場,在西北的荒原上奉獻青春。后來為了搶救國家財產,她跳進冰冷刺骨的老龍河,以至于耳聾、癱瘓,但她以超人的意志力戰勝困難,被譽為.中國的保爾”。
原型王孟筠,來到新疆后,被分配到剛建的八一鋼鐵廠煉鋼部選礦石。后來她為了搶救河里的小羊,導致風濕病加重,下肢癱瘓,又并發中耳炎等許多復雜的病。在小說中,作者選取了王孟筠跳進老龍河以及并發中耳炎、癱瘓的細節真實,但也虛構了小海英在搶救水庫的戰斗中,撈起一根根抗洪急需的木樁,最后,為了搶救對抗洪至關重要的梢捆導致耳聾以及冒著連綿的大雨不顧自己的關節炎,將“八一棉”棉田的泄洪閘打開,最后導致癱瘓這兩件事。
小海英的命運遭際像是雜糅了多個人物的故事、命運遭際于她一個人物身上。換言之,作者采用了如魯迅塑造小說人物的手法:“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過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角色。”如小海英跟隨母親在獄中就患上關節炎、成長于紅色革命家庭。后來搶救國家財產時患上耳聾,又因為將‘八一棉”棉田的泄洪閘打開導致癱瘓。小海英所經受的磨難仿佛是多個人的命運遭際全都集中發生于她一人身上。
二、化歷史為情節
海英參軍的年代是1952年,在昂揚奮發的時代精神感召和鼓舞下,小海英沖破重重阻力,終于如愿以償,從風景秀美的江南地區來到了大西北,投身邊疆建設中,成為軍隊中的一員。這是將人物置身于當時的時代大背景之下的。
此外,作家鄧普1951年被分配至新疆軍區后勤部,從事宣傳工作。《軍隊的女兒》是他在此期間創作。正是由于他在八一軍墾農場生活的經歷使得小說的描寫具有現實性意義。
作家對當時生活場景進行了細致描寫:如梧桐窩大草原的建設者們,都像鼴鼠那樣棲居在地洞里。老場長的辦公室也是一種挖進地里兩米深、上面用蘆葦和泥土蓋頂的地窩子。包括博格達峰山洪爆發使得大大小小的水流一下子匯集到河床低淺的老龍河里。為了攔腰截斷老龍河,修了“八一水庫”等一系列的描寫都可以看出當初軍墾農場的現實生活的影子。歷史數據資料呈現的只是歷史的結果,而非生命的過程。通過閱讀《軍隊的女兒》,透過情節更能了解軍墾開發的歷史。
三、從現實到理想——革命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相結合
《軍隊的女兒》誕生在一個理想主義的時代。劉海英的理想是當拖拉機手。當她來到了八一軍墾農場之后,拖拉機有限,她未能如愿以償。后來她賭氣去當“業余”拖拉機手,她的思想出現了徘徊。
小海英的新的世界觀是在老場長的啟發教育下建立的,老場長對于小海英來說更像人生導師。后來小海英逐漸認識到無論干什么工作,只要工作就是美麗的。這種對自己童年理想一當拖拉機手的放棄,實際上是在個人與集體之間,無條件服從集體,無私無我,這才是黨的好女兒。
未當上拖拉機手的小海英像保爾那樣活著,在平凡的工作中實現自己人生的價值。搶救國家財產使得這位女孩子變成了一個聾子,但她卻說:“我不過是聾了,手還是好好的,我要做一個快快樂樂的聾子。”她尋找了很多克服耳聾的辦法,通過鏡子練口型去猜別人說的話。她不能容忍自己過“光拿錢不干活”的日子,也沒有去領周玉珍為她留的供養費。因為保衛“八一棉”讓小海英再次住院,她變得又聾又癱。她宣稱:“我要活著,不要安慰。”后來,她重新振作起來,這種精神鼓舞了同病房的人同病魔作斗爭,小海英的生命的火花充實了很多病人的生命力量。
作者對自己筆下的英雄人物及其典型環境是熟悉的,他將真實的人物事件以及時代背景融入到這篇小說中,使這部作品洋溢著革命激情,以其自身的真實性獲得藝術生命力與獨特價值。并通過一定的虛構突出了革命青年熱情高漲,投身于邊疆建設的形象,影響了一批批青年對自己人生的選擇。
參考文獻:
[1]張呂.從《軍隊的女兒》看邊疆文學創作的審美追求[J].石河子大學學報,2004(04).
[2]郭澄.生命的火花分外燦爛—重評已故著名作家鄧普的小說《軍隊的女兒》[J].新疆石油教育學院學報,2001(01).
[3]謝剛.“紀實與虛構:新時代中國文學的走向”學術研討會綜述[J].當代作家評論,2018.
作者簡介:王娟娟(2000-),女,河南南陽人,夭學本科在讀,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