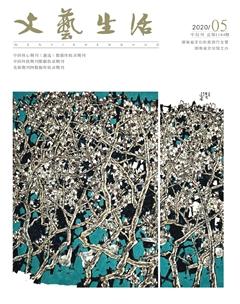瑪格麗特·尤瑟納爾中國神筆故事變異研究
摘要:曹順慶先生提出的變異學(xué)理論不僅彌補了法國學(xué)派影響研究和美國學(xué)派平行研究的缺憾,開啟了注重異質(zhì)性的比較文學(xué)學(xué)科理論新階段,而且也為異國形象的研究提供了新視野。筆者在對《王福脫險記》和神筆馬良分別進(jìn)行文本細(xì)讀的基礎(chǔ)上,再利用變異學(xué)的相關(guān)理論知識,找出這兩個文本在人物形象、情節(jié)塑造和思想傾向等方面各自的異質(zhì)性,以及前者對后者所進(jìn)行的改造和變異,即以“求異”的思維方式來研究兩個文本并努力探尋其變異的原因。
關(guān)鍵詞:變異學(xué);《王福脫險記》;神筆馬良;瑪格麗特·尤瑟納爾
中圖分類號:I565.074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20)14-0053-02
一、前言
法國作家瑪格麗特·尤瑟納爾結(jié)合了自己法蘭西民族文化背景、個人文化心理,又充分吸收了帶有東方氣息的中國思想文化,完成了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內(nèi)核元素的接受的同時,又對其進(jìn)行歸并和整合,并通過一系列的變異、改造、過濾和選擇,進(jìn)行“文化過濾”,造就了一個新的中國形象、新的神筆故事,一個帶有法國情調(diào)的中國故事,從而完成了對異國形象的塑造。也正因為如此,尤瑟納爾筆下的《王福脫險記》呈現(xiàn)出東西方文明結(jié)合共生的變異色彩。
二、人物形象塑造上的變異性
《王福脫險記》將古今和東西縫合的天衣無縫,猶如渾然天成。與中國神筆馬良的故事相比,二者都屬于寓言故事的范疇,在情節(jié)的安排上二者也頗為相似,甚至二者文末都是以一片汪洋大海作結(jié)。但是,在主題意蘊和人物形象塑造上卻大有不同。其中,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異質(zhì)性更為醒目和明顯。
在神筆馬良的故事中,洪汛濤先生集中刻畫的人物形象主要有三類:馬良、縣令與皇帝、窮苦百姓,但是這三種人物除了主人公馬良之外,其他人物都可以統(tǒng)一歸并在一個“官——民”、“好——壞”、強——弱”、“富——窮”、“統(tǒng)治——被統(tǒng)治”這樣一個矛盾強烈的絕對二元對立結(jié)構(gòu)之中,而且這個結(jié)構(gòu)是完全封閉的。而它越封閉,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就更加單純和單一,人物性格基本不存在顯著的發(fā)展變化。比如,故事中的皇帝和縣令都是物質(zhì)上的貪得無厭者,皇帝在得到了神筆后,他畫了一座又一座的金山,一塊又一塊的金磚,后也是由于貪心要去大海中尋找搖錢樹而死于其中。而故事中的窮苦百姓則是中國傳統(tǒng)農(nóng)耕文化中善良、勤勞的下層階級。在神筆馬良的故事框架里,無論是統(tǒng)治階層,還是被統(tǒng)治階層,他們都自然而然地統(tǒng)治著別人或被人統(tǒng)治著,貪婪的人從頭到尾都貪婪,善良的人一直都善良,好人與壞人徑渭分明。
與之相反,尤納瑟爾在對中國神筆故事進(jìn)行變異和改造的過程之中,人物形象被塑造得更加飽滿和善于變化。首先,小說中的那個年僅20歲的皇帝,其行為模式符合西方世界對東方中國封建王朝的一次想象,他怎么看都是尤瑟納爾筆下想象出來的“中國天子”,這個天子從一出生起就圈養(yǎng)在翻美”的空間里,他所看到的,所聽到的,所呼吸到的完全都是藝術(shù)中的精華、人間的所有美好。因此,在他16歲之前,他甚至認(rèn)為這就是生活的模樣,可是,當(dāng)他接觸到了現(xiàn)實生活丑陋的一面時,他頓時覺得以前他生活的那個世界只不過是“一個失去了理智的畫家憑空涂抹的一堆亂糟糟的墨跡”。因此,他認(rèn)為是畫家王福欺騙了自己,他決定要剁掉王福的手,挖掉王福的眼球,讓他無法再創(chuàng)作。看到這里,有些讀者也許會認(rèn)為這個皇帝是無比殘酷的,但其實不然,相反,更加表現(xiàn)了他是著實向往王福所創(chuàng)作的那個世界,那個世界不為物質(zhì)不為權(quán)利只為純粹的美。權(quán)利無法讓這個皇帝真正快樂,相反讓他孤獨,令他厭惡。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個天子他多了些溫情,也令讀者充滿了同情,他與神筆馬良故事里的那個壓榨百姓的封建皇帝是截然不同的。我們甚至可以說,《王福脫險記》中的那個皇帝與小說中那個放棄錦衣玉食、榮華富貴虛心跟隨王福的弟子林一樣,都是不夾一絲雜質(zhì)在追求在追求藝術(shù)的美。他們二者所不同的是,弟子林由于在師父王福的引導(dǎo)下,重新審視了自己的生活,走向了藝術(shù)的道路。而這個不一樣的“中國天子”,卻迷失在了藝術(shù)中而無法自拔。同時,他還心有不甘,所以當(dāng)他見到王福時,他才會滔滔不絕地一句又一句地質(zhì)問王福:老王福,你想知道做過什么觸犯了聯(lián)的事嗎?”他質(zhì)問王福,其實也是質(zhì)問自己,否定了自己的過去。
其次,弟子林這一人物形象的建構(gòu)是《王福脫險記》較之神筆馬良而言所實現(xiàn)的一次重大變異和改造。我們甚至可以說,如果尤瑟納爾的這篇小說中沒有設(shè)置弟子林這一人物形象,那么整部小說的文學(xué)魅力和思想內(nèi)涵都會大打折扣。從文本我們可以知道,弟子林的思想認(rèn)知在前后發(fā)生了重大的轉(zhuǎn)變。本可以錦衣玉食度過這一生的他卻毅然地放棄了自己原來的生活,因為在他看來,裝滿畫稿的口袋裝的并不是畫稿,而是“白雪皚皚的大山”、春水浩蕩的河流”和“夏夜月亮的玉盤”。而且,他將王福視為自己最愛最珍貴的人,這種情感甚至超越了他那個如花似玉而又心地純凈的妻子。所以,當(dāng)皇帝抓拿王福時,他竭力保護(hù)自己的師父甚至最后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最后,弟子林死而復(fù)生,王福脫險而去,兩人一起消失在汪洋大海里,只見“林的紅圍巾”和“王福的胡子”仍在空中飄動著。這是小說結(jié)尾的處理,是浪漫主義的筆調(diào),是作者尤瑟納爾個人情感在人物命運安排上的一個恰到好處的投射。
最后,關(guān)于小說的主人公王福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作者也是在神筆馬良故事里的馬良的基礎(chǔ)上,做了“陌生化”的處理。總的來說,王福這個人物形象較之馬良而言,更加立體更加鮮明。王福,這個名字一聽就是一個很中國的名字,但由于時間、身份和見解等因素,這個中國畫家并不是那么中國。在神筆馬良的故事里,主人公馬良的神筆來源于一個白胡子的老人,即來自于外界客觀世界。在沒有畫筆之前,馬良白天用樹枝在沙地上學(xué)描飛鳥,用草根蘸河水描游魚,晚上又用木炭描白天描過的東西,從這其中我們得知馬良是一個勤奮的繪畫藝術(shù)愛好者。但是相對于馬良而言,王福更多的是一個具有藝術(shù)天賦的畫家。所以當(dāng)?shù)茏恿志退涝谧约旱拿媲皶r,他雖然也會悲痛欲絕,但瞬間他的目光便投向了那一灘艷麗的紅色血跡上,因為在王福的眼里,這紅色的血跡就像筆墨一樣又將他拉回了藝術(shù)的王國。這種對藝術(shù)的癡迷幾乎讓王福忘記了失去徒弟的悲傷。
除此之外,小說中還有一處極為精彩的描寫:“林的腦袋從他的脖子上掉了下來,猶如一朵掐斷莖的鮮花。寫之當(dāng)然是王福的目光,是他作為藝術(shù)家所看到的別人無法理解的美,正如小說開頭中所說的:“王福所喜歡的是物體的形貌,而非物體的本身廠寫之不得不讓我們佩服尤納瑟爾的藝術(shù)想象力。與此同時,更令我們驚嘆的是作者在與人物融為一體的同時,又能夠做到與之保持著適當(dāng)?shù)木嚯x,用唯美的筆觸對自己筆下心愛的人物進(jìn)行如此冷靜的殘酷描繪。
三、思想傾向上的異質(zhì)性
《王福脫險記》和神筆馬良表現(xiàn)了不一樣的思想內(nèi)涵和思想傾向。這表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神筆馬良這個故事發(fā)生的環(huán)境是典型的封建社會,但《王福脫險記》中,雖然故事一開始就告訴了我們故事的發(fā)生地點:漢王國。但是它究竟是不是歷史上的漢朝,我們不得而知。這種時間上的模糊安排也更有利于尤瑟納爾來營造一個背景虛幻的異國形象。同時也更容易讓我們進(jìn)入作者所營造的這個世界中去,產(chǎn)生了一定的間離效果。
除了在時間上模糊外,尤瑟納爾還有意打破了性別上的對立,這不僅是作者的一種主觀投射,同時也是老畫家王福的獨特之處。這種獨特的處理讓《王福脫險記》得以實現(xiàn)改造和變異。《王福脫險記》中,寄寓了尤瑟納爾對于中國道家思想內(nèi)核的選擇性吸收。因此,在《王福脫險記》之中,父與子(林的外祖父與林的母親、林與林的父親)、君與臣(皇帝一大臣)、君與民(皇帝與王福、弟子林)、夫與妻(林與林之妻)之間的關(guān)系并不是像真正的中國封建社會所要求的那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說人與人之間、統(tǒng)治階級與被統(tǒng)治階級的矛盾不再是作者著力要去塑造的中心。
與之相反,在《王福脫險記》這里,中國傳統(tǒng)的人際倫理關(guān)系中多了一絲溫情。如:皇帝雖然擁有權(quán)卻并不殘暴也沒有熱衷權(quán)利。林與其妻子的確是父母之命的婚姻,但其中同樣有互幕的愛情。而林的妻子很顯然是作品中的一個悲劇人物,但作品中的皇帝也同樣是一個可憐的人物。
四、結(jié)語
總之,尤納瑟爾的《王福脫險記》很明顯受到了中國道家思想的影響,作者正是借以表達(dá)自己對于道家文化的欣賞和認(rèn)同。同時,她又一個“他者”的身份審視和反思了當(dāng)時西方國家的那種物質(zhì)至上、欲望澎湃的社會現(xiàn)實。
參考文獻(xiàn):
[1]曹順慶,張莉莉.從變異學(xué)的角度重新審視異國形象研究[J].湘潭大學(xué)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4(03).
[2]曹順慶.比較文學(xué)概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5.
[3]許凡之.想象的東方敘事——讀尤瑟納爾小說《王福脫險記》[J].書城,2018(06).
作者簡介:康雯(1999-),女,湖南姿底人,吉首大學(xué)2017級漢語言文學(xué)專業(yè)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