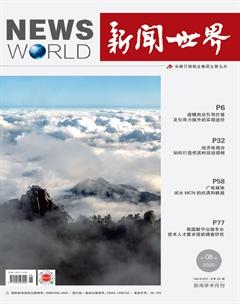“歷史街區”的媒介鏡像與空間再造
謝雅茜
【摘? ? 要】紀錄片作為一種具象化的傳播方式,在城市形象塑造、文化傳承和集體記憶傳播上具有重要作用。紀實性影像是記錄街區變遷的一個重要載體,歷史街區紀錄片折射出街區的現代化和再生過程,承載了人們對于街區“過去”“現在”和 “未來”的時空想象,并促使受眾去追尋影像中的城市街區。本文從《記住鄉愁》的內容表現加以分析,闡述其如何在媒介視域下進行空間敘事,用視覺語言講好歷史街區故事,塑造街區形象。
【關鍵詞】記住鄉愁;歷史街區;空間;媒介
近年來,隨著城市的發展和建設,街巷原有的生態環境和文化生活氛圍逐漸淡出,開始走向“集體失憶”和“千城一面”的時代。歷史街區不是一個古老的遺跡,它的歷史氛圍濃厚,多年形成的記憶場所具有很大的文化再生能力。街區記憶作為一個城市不可分割的文化表征,具有不可回避的價值。今天,在城市化進程中保留下來的傳統街區正面臨著轉型和發展。只有把握時空演變和新舊耦合的特點,才能最大程度度地延伸城市的情感記憶,實現街區的再造。在紀錄片中,街區景觀通過影像達成意義共享的過程是地理空間實體、共同的歷史文化背景和街區個體生活體驗相互作用的過程,紀實影像成為閱讀街區的一種媒介路徑。“真實虛擬”,藝術的再創造,生成了一個“媒介化”場景,讓我們感受自己習焉不察的街區鏡像。
2019年央視播出了大型人文紀錄片《記住鄉愁》第五季,它以歷史文化街區為拍攝主題,通過一集一個街區的方式,講述一個地方的精神傳承,其創作的方向是展現歷史文化街區風貌,喚醒逐漸消失的家鄉記憶,梳理老街區的歷史脈絡,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本文選取第五季中的60個街區作為研究對象,通過分析其對歷史街區的故事化表現,多層次挖掘老街的媒介表達和空間內涵。
一、街區場景的再場景化
(一)街區可見性的建構
歷史街區作為一個建筑媒介,包涵著自身獨特的文化意涵,在不同的情況下被征用。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有“地方(place)可見度”的說法,他認為,作為地理或空間的“場所”,把握人類視覺和心理的能力,與其它地方的敵視或與其他場所相沖突,具有突出的視覺和藝術、建筑、紀念儀式、召喚的力量。通過戲劇化的建構,使人文場所生動真實。[1]歷史街區通過紀實影像的方式向民眾展示了街區不為人知的歷史“秘境”,當空間可以被視覺透視,街區景觀也由想象變為可見的地方。
該片每一集都將當地古城老街的全貌加以視覺呈現,對有代表性的建筑特色悉數道來。在閩南地區,福建晉江五店市街區遍布的130多座獨具閩南特色的傳統建筑群,雕梁畫棟的紅磚大厝足見閩南風情。泉州西街是泉州保存最完整、最有意義的老街。街上的建筑表現出閩南風格,以及現代主義、巴洛克式的特色;在華南地區,騎樓這種建筑形式并不少見,梧州騎樓街區以面積之大、范圍之集中、保存之完整而被譽為“騎樓博物館”,藝術雕花、巴洛克欄桿、圓形屋頂,這些極具異域風情的建筑符號和中式傳統的牌坊、花窗和灰雕結合在一起。透過紀錄片,帶觀眾了解歷史街區的繁華,領略街區風貌,在街區意象的組合之中拼貼出鄉愁的主題。紀錄片中的街區意象符號以紀實性影像為媒介,使隱喻在街區下的建筑意涵得以顯現。
(二)媒介化的街區文本
歷史街區是以場域作為媒介,正如夏瓦所言,媒體的曝光是宣傳與名聲的關鍵,它有可能在市場或者文化政策語境下轉換成其他價值形式。[2]媒介深刻影響了人們對于城市空間的理解和體驗,人們對歷史街區的“懷舊”激發了“鄉愁”思緒。在網絡空間中,用文本的衍生而構筑的符號化街區,讓故鄉與媒體交織在一起,形成了多重變奏與懷舊之流。“懷舊”涉及空間和場所,與人的情感密切相關,體現了人們對家鄉生活體驗的追憶。媒介搜集到更多關于歷史街區的信息,這些帶有地理標簽的數據,將地方景觀與其文化標簽連結起來,讓人們重新認識了城市的文脈氣息和人文歷史。
現代城市是媒介和建筑的復合體。空間則通過可見物的不同框架、再現的不同觀點和不同技術而成為眾多空間性的媒介。[3]之所以用街區文本制作城市紀錄片,也是因為這些文本來自城市,同時是城市的中介,媒介與街區間的耦合,意味著二者不僅僅是表征與被表征的關系,也不是線上與線下、虛擬與實在的二分關系,而是一種融合、互嵌的關系。
(三)街區場景的互文性
揚·阿斯曼指出,“文本的一致性”是為了搭建一座橋梁,旨在克服作品轉化為文本形式可能造成的斷裂。有了這樣的連接,文本即使歷經滄桑也不會消失,并保持其有效性和與當前形式的無縫對接。這種對接即為“互文性”,[4]一方面,在紀錄片中,視覺影像和歷史街區形成一種互文作用,把街區的風情風貌向世人展示;另一方面,影片的觀眾被影片所吸引,走在影片出現的場景中,幻想與現實可以相互印證。
街區影像傳播通過將鏡頭對街區故事文本的刻畫并以影像技術的形式進行二次創作,讓街區的故事以全新形式回到觀眾的視野中。這部紀錄片也表達了一種強烈的對話感。例如,鏡頭對準800多年前,南宋詞人辛棄疾看著滔滔三江水遙望著故都汴梁的郁孤臺,“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郁孤臺聞名于世,這要歸功于一首名為《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的古詩。建筑與詩篇的互文,賴以既有經驗和情境營造,激發了受眾對街區意象的解讀和聯想。又如,位于浙江紹興的書圣故里歷史文化街區,因是書法大家王羲之的故鄉而得名。老街北端的戒珠講寺有一千多年的歷史。相傳,這座寺廟名字的來歷,因王羲之誤會老方丈偷竊寶珠致其郁郁而終,王羲之把自家宅院捐給佛門,從此一心鉆研書法,終成一代“書圣”,也留下了“心正,字正,人正”的訓誡。歷史上,紹興共走出了27位狀元,2000多位進士,讓這里有了“名士之鄉”的美譽。如今的老街,依舊延續著歷史的繁華。在這里,傳承下的一脈文風,不僅滋養了文人大家,也浸潤了尋常百姓的心田。
家族世代成長于街區的地理歷史融于紀錄片中,街區的真實面貌與紀實影像的情境交疊,前者提供素材,后者造就想象的懷舊空間。
二、懷舊空間:空間再造的意義生產
(一)地方感的營造
人文地理學家段義孚認為,當我們賦予空間意義時,空間便變成了地方。[5]城市傳播中的紀錄片借助自身傳播優勢,從選取承載“地方意象”的城市“空間”到呈現“空間”中日常生活實踐,以及展現代表地方認同內化的獨特人物故事,完成從“空間”到“地方”的轉變,重新連接起城與人的深度關系。當鏡頭切入一簞食一豆羹的日常,是嵌入居民生活的日常場景。街區百年的傳承,離家遠去的游子見到自己的家鄉以影像形式呈現的時候,內心會產生獨特的情感連結,鄉愁就化為街巷之間濃濃的市井人情味。在紀錄片中,重慶黃桷坪老街上隨處可見的是一棵棵黃桷樹,跟隨街頭的手繪地圖去四川美院的校園里看看雕塑、逛逛展覽,去交通茶館里喝一碗蓋碗茶,擺擺龍門陣,去豆花店吃一碗豆花、喝一口蹄花湯,與老街人一起聊聊這里的故事,跟隨鏡頭的腳步帶你一起感受老街人“志于道,游于藝”的情懷。在北京大柵欄爆肚馮、老門框鹵煮、張一元茶葉、兩分錢一碗的老舍茶館大碗茶,里面每天晚上能聽戲和相聲,都是老北京街區胡同里的京味符號,也是當地最具有日常氣息的地方。
城市不僅是物質城市,它也是承載人們日常生活的空間城市。這是一個有意義的空間,銘刻著人們的情感記憶和歷史想象,在城市敘事中,通過對城市文化心理的描寫和對日常生活的呈現,找回遺失的文化記憶和獨特的地域意識,實現集體記憶的懷舊構建。
(二)集體記憶的懷舊營造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和同質化危機的出現,集體記憶作為一種具有歸屬感和認同感的無形力量,與城市歷史文化的積淀和特征的生成有關。城市記憶不僅是空間記憶,也是社會記憶或文化記憶。老街沿革的舊城記憶成為城市地標,建構集體記憶。作為媒介的空間,也成為“記憶的場域”和“記憶之所”。街區鄰里的傳統文化和歷史往往與當地居民的身份和文化歸屬感聯系在一起。由于都市人的集體挫折感和他們在現代城市文化中對現實的逃避,巷弄、街道、老屋、洋房隨著時間一步一步改變,慢慢地翻新,那熟悉的古老街區,漸漸地成為老街區人心中的逐漸模糊的記憶。集體記憶的傳承也成為意象中的一種情感傾向,延伸了意象中日益濃厚的懷舊情結。
始建于明代的“布政衙”是五店市現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這里收集了晉江各個姓氏的家風家訓。在五店市,走進老街的任何一間院落,都能看到各個家族的家規家訓,就是在這種崇善向德的氛圍下,一代代老街人書寫記錄著家族的集體記憶。在梧州,騎樓式建筑連在一起,從自己家中探身出去就能與鄰居握個手,這樣的老街,更像是一個溫暖的大家庭。惠山老街大大小小的街巷中分布著108座祠堂,80個姓氏的祖先都供奉在這里。這里一座又一座的古祠堂,保留了自身的姓氏,記錄了家族的繁衍,也記錄了人們的生活。
城市在拼貼歷史與記憶的張力敘述中,以一種想象力的延伸方式確立人類集體記憶的延續性。景觀也充當著一種社會角色,人人都熟悉的有名有姓的環境,成為大家共同的記憶和符號的源泉,人們因此被聯合起來,并得以相互交流。為了保存群體的歷史和思想,景觀充當著一個巨大的記憶系統。[6]在昆明老街那期節目的尾聲,主持人走在甬道街上說,回望昆明老街,這里收藏著人們世世代代的集體回憶,無論世事如何變遷,老街人始終熱愛著它。因為這里的每一條街道和小巷,不僅記錄下了這座城市的歷史,更承載著所有人的夢想。人們沐浴著云貴高原的陽光,更享受著屬于那個時代的精彩。
(三)從影像里管窺街區的創生
這些具有百年歷史的古老街區,隨著現代化與都市發展,面臨巨大的轉變,在現代化的洪流之下,它將如何保存古老的歷史與文化,對于歷史街區來說是一個重大的考驗。老街是一座城的起點,從老街出發,一座座現代化城市拔地而起。在日益進步的都市計劃與街區再生中,老街逐漸煥發新生。紀錄片以歷史性城市地景視野的呈現提供了探討歷史街區保存的可能。百年歷史街區也是一部城市的發展史,源于歷史文化的深度,通過確立街區特色,城市可以利用其經年累月的古色古香保留文脈的傳承。
老街巷里沉淀著千百年的歷史故事,即便是每天都經過的街巷、看得見的景觀也未必就了解其背后的人文意涵,影像通過旁白敘事和街巷的視覺呈現,向人們娓娓道來老街的前世今生,以此實現城市記憶的再現和建構,實現街區文脈的傳承。
三、超真實的街區意象
以空間敘事美學取代傳統敘事美學去刻畫街區空間,一方面視覺在建構街區的文化空間,其中包括街區名片的打造、現代性的塑造以及街區身份的分層等;另一方面以紀實為方式的紀錄展示,作為一種特殊的視覺文本,影像在現實生活造成的歷史平面化或超真實等現象改變了人們的空間經驗。媒介與城市空間之間出現了一種“結構性耦合”,呈現的是城市作為視覺交織文本的圖景,同時也表現了視覺在歷史的創造與消失、現實與虛擬的辯證可能性。在光影交錯的虛擬與現實影像世界中,我們看到了城市、人與社會的另一個參照世界,對反思當前的城市發展和人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凱文林奇在《城市意象》中,說明了都市意象需要深入探討景觀結構于當地人與外地人的意義。作為傳播城市形象的手段,紀錄片已經成為新世紀不可或缺的營銷方式。良好的城市建設為其提供了一個審美化的空間,同時紀錄片中也展示了經過加工和放大后的城市空間之美。影視記錄了充滿人性和現代化的歷史街區,同時向觀眾展示了其背后的社會文化、價值取向和觀光吸引力。同時凱文林奇也認為,“物體不只是被看見,而且是清晰的、強烈地被感知。”[7]影像化的歷史街區掩蓋了商業的氣息,不是對街區真實的再現,被選取的可見的地點造成遠程的繭房,不是街區立面的完整呈現,影像街區不能代替真實的空間感知。
結語
“游子在外,最憶家鄉。”歷史街區是一座城的起點,在都市現代性的沖擊下,借由情感記憶與文化建構得以呈現,地方性影像、文化景觀以及公共展示等都成為釋放“鄉愁”的媒介形態。現代化固然是不可抗的進程,各地都在努力打造霓虹璀璨的大都市,但是真正給人以歸屬感的,還是街頭巷尾的小人物、小情懷。
注釋:
[1]段義孚.經驗透視中的空間和地方[M].潘桂成譯.臺北:臺灣國立編譯館,1998:72.
[2]施蒂格·夏瓦,文化與社會的媒介化[M].劉君,李鑫,漆俊邑 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8:148-149.
[3]汪民安,陳永國,馬海良主編.城市文化讀本[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63.
[4]揚·阿斯曼.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會議和政治身份[M].金壽福,黃曉晨 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
[5]Yi-Fu T.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7,p6.
[6][7]凱文·林奇.城市意象[M].方益萍,何曉軍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95.
(作者: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2018級傳播學碩士)
責編:姚少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