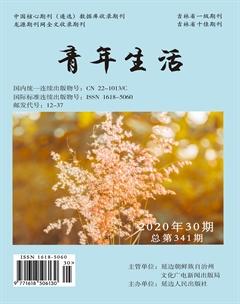德里達《友誼政治學》的思想探析
賀馳
摘要:政治學對于早期解構主義者而言一直是諱莫如深的議題。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它卻成為解構主義者德里達談論“政治”的話題之一。從《友誼政治學》一書的出版到德里達實現“政治學”思想轉向的整個過程中,他通過對形而上學的政治觀點進行解構與重建,將友愛、朋友、民主等概念作為解構主義策略中的對象,試圖打破一個傳統政治意義上無敵友的人類時代,正是德里達解構思想的時代特征和理論價值,而這一點也在以往的研究中被忽略。
關鍵詞:德里達;政治學;解構策略
作為法國最具影響力的解構主義者雅克·德里達,他的思想在當時政治背景的影響下經歷了早期和晚期的演變之路。20世紀80年代,學術界就關于德里達思想中是否存在政治學或倫理學這一隱喻表述為基本線索展開討論,同樣德里達解構主義立場是否隱含政治性也成為人們廣泛議論的話題。對此,學者楊耕的觀點獨具創意,他指出德里達從結構主義轉向了馬克思主義,并且“這是由解構主義的內在邏輯、馬克思主義的解構功能以及二者之間存在著相似的政治學維度決定。”[8]學者張旭在《德里達晚年思想的政治哲學轉向》文章中表明,德里達借助于列維納斯模式實現了“他晚年政治哲學的轉向,提出了一套以友愛、好客、新國際等概念為核心范疇的新政治哲學,對全球化時代的新國際政治秩序和人權政治給出了深刻而負責任的反思。”[9]學者李永毅先生認為,德里達思想中存有“政治學”轉向和早期解構主義思想是一脈相承,解構主義的立場本身就隱含著政治性。上述觀點從本質上強調,德里達思想的轉變是其政治邏輯與環境發展演變下的時代產物,如他本人所說那些政治問題并非像從某個彎道貿然出現,而是通過借助馬克思主義,實現對當前形勢規則的反抗。那么,如此以來,關于德里達思想中“政治學與倫理學”的轉向之爭,以及解構主義觀點中所指涉的政治含義,由此將解構策略運用于政治領域去重新思考政治問題,這是本文得以開展的前提。
一、德里達“政治學”思想轉向之路
20世紀60年代,“解構”或“解構主義”思潮在法國學界開始蔓延,這一思潮的傳播之勢可謂是蔚然成風,很快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激起反響,進而席卷歐美,涉及包括哲學、文學、藝術、神學等在內的文化研究的每一領域。”[2]20世紀90年代,德里達相繼出版了《馬克思的幽靈》《法律的力量》《友誼政治學》等涉及政治問題的著作,引起當時思想界的強烈反響,這一反響的背后是德里達晚期思想轉向“政治學”的重要發端,也有少數人認為這是他晚期“政治一倫理觀”的轉向之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關于討論德里達的聲音越來越廣泛,是否意味著他真正實現了政治學思想轉向呢?基于上述觀點,我們要從《友誼政治學》著作中去尋找在實現轉向過程中隱含的理論線索,要理解其中的政治立場,德里達對解構主義的批判就是一把鑰匙。
事實上,德里達在1967年出版《論文字學》一書就涉及對政治問題的討論,隨后在1968年法美哲學家學術研討會上,他指出“任何哲學性學術研討會,都存在著必然的政治意義,”[10]此言滲透了他對“政治”一詞的見解,也奠定了《友誼政治學》一書的思想基調。同時,此書的寫作思路與他前期作品風格略有不同,似乎暗示“解構主義向來訴說的是意義和判斷之叢確證和自相矛盾的悲傷,”[2]它充其量不過是德里達‘政治學轉向的一種方式而已。但有所不同的是,在《友誼政治學》書中他并沒有直接討論政治問題,而是指出解構和政治并不是直接的關系,德里達在分析表面與政治不相關的問題時,他的文本也充滿了政治的“潛臺詞”,因此,文本中的文字僅僅是解構主義分析的切入點,也說明德里達并沒有失去政治立場而是針砭時弊地對分析社會現實問題。所以,他認為解構思想中隱含著政治維度,試圖通過文字來闡述對政治的看法,以此獲得更明晰的理解。
關于‘政治一詞的概念,它最早出現在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以及施密特的《政治的概念》書中,起源于古希臘的城邦制并延續至近代西方國家。然而,‘政治在德里達解構思想中呈現出不同的方式,其一,他認為政治領域中存在著私人和公共對立的局面;其二,他指出傳統意義上政治體制的問題,是“公民主體與計算、政治犯罪、男性中心主義的政治思維、友愛的政治含義、政治欲望與政治決斷的關系、作為允諾的民主、主權、政治共同體等等微觀問題。”[6]基于上述兩點,德里達在對政治概念的解構過程中進行去政治化的闡述,這表明他對政治進行另一種可能的思考,希望“盡可能擴大政治討論的空間,同時又防止將一切東西簡單地歸結為單一意義上的政治。”[6]可見,德里達解構主義思想與‘政治有著復雜的關系,解構主義的建構意義和人文關懷,也能夠得到具體的呈現,正是他“政治學”思想轉向的重要過程。
所以,在德里達看來,“解構”它不是所謂的“摧毀和瓦解”,而是一種對美好社會的“肯定”追求,在也恰恰預示了他后期經歷“政治學”轉向并不是偶然,而是一種思想在新的歷史語境下的進一步發展。同時,它也并未背離早期解構主義所設的思想框架,相反,在很大程度上,解構主義的立場是具有政治性質的。另外,它從根本上消解了西方文化的優越意識和歐洲中心主義觀念,呼吁建立新型國際組織抵御全球性的危機,從而也宣告了一種世界主義哲學家的愿望和遠矚。
二、《友誼政治學》中的解構策略分析
20世紀60年代后期,解構主義和德里達的名字似乎毫無聯系,為何在20世紀90年代德里達的名字卻在歐洲大陸變得家喻戶曉呢?此前,《友誼政治學》一書的出版,引起了學術界、思想界的關注,也由此帶來兩個不同觀點的爭論:“友誼”中有政治學?友誼的“政治”還是政治的“友誼”呢?鑒于此,學者尚杰先生對“友誼”的內涵作了分析,他指出:“友誼政治學的提法本身就是模糊學科界限的,其實德里達談論的絕不僅僅是政治學,這個術語本身就具有超越性質。”[11]這一論斷表明德里達對‘友誼概念的表述在當時還顯得不成熟,此書中雖涉及朋友、敵人、友愛、民主……這些熟知的哲學概念,但他并沒有將這些哲學概念直接運用在政治領域,而是認為哲學在生活中是具有政治意義的東西,如此說來,哲學概念與政治表述成為《友誼政治學》書中一條重要的理論線索。
那么,關于另一個觀點的爭論,德里達為什么要闡述“友誼”政治學呢?因為在他看來友誼是身邊的事,友誼(友愛)在傳統的啟蒙術語中,即以博愛稱之。所以,‘友誼與‘朋友這兩個概念,在西方政治術語中具有特殊的含義,“如果要產生一種友愛的政治學而不是戰爭的政治學,那么就必須對朋友的意義產生一種共識,只有從朋友(敵人)之間對立內部才能決定‘朋友的含義。”[12]此言可以看出,德里達的政治觀點是要消解這種非友即敵或非敵即友的對立狀態,從而進一步解構施密特所持以戰爭作為敵友之分的形而上學政治邏輯觀點。基于此,德里達把對戰爭的解構轉向以朋友、友愛為對象,因為“朋友與敵人”往往被人們認為是一對日常生活的概念,如果這個世界上沒有朋友或敵人,我們就不能稱對方為朋友或敵人了。
在此,德里達首先討論了如何解構友愛以及從友愛的概念中衍生出博愛,他認為“真正的博愛,字面意義上的博愛,可能就是普世的、精神的、象征的以及無限的博愛,即誓約的博愛(兄弟關系),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博愛,不是‘自然兄弟之間的博愛,不是對立于姐妹的男性兄弟之間的博愛,不是家族之內、民族之中以及特殊語言之內被確定的兄弟之間的博愛。”[12]如此以來,家庭、民主等概念便成為他著作中不可缺少的語言。其中,在《友誼政治學》書中反復出現這樣一句話:“哦,我的朋友,沒有朋友。第一個‘朋友是復數,第二個‘朋友則是單數。”[2]此話是德里達引用亞里士多德的觀點,第一個‘朋友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朋友;而第二個‘朋友指少數人之間的友誼,具體地講即是志同道合的兄弟情誼。
那么,什么是友愛呢?在亞里士多德傳統倫理學中,關于友愛的闡述,換句話說“人可以喜歡被愛,但是愛永遠比被愛更為重要,兩者之間的差別就像行動之于痛苦、主動之于被動、本質之于偶然、知識之于無知。”[2]這是因為我們依存的社會,從來只是少數人的平等,友愛也是指向少數人,反過來體現人們之間平等關系。如果沒有朋友或敵人將意味著什么?一個沒有朋友與敵人的世界里,猶如人丟失了朋友或敵人,只有在記憶中恍恍惚惚出現了一個幽靈,可是依舊沒有找到友誼或朋友。另外,如果我們處在一個非敵非友抑或無友無敵的世界里,那么戰爭也不復存在,也恰恰印證了施密特所指的后冷戰世界的政治格局及其走向。
同樣,德里達在《友誼政治學》書中對“民主”一詞談論較多,“民主”來源于西方政治制度,它的產生必然帶有一定的歷史性。德里達所討論的民主并不是民主制度,他認為:“民主的生命就像生命本身,在其分化的德性的核心保持著它自身的不充分性。”[6]因而,解構和民主成為了以民主的方式對待民主的一種策略,這樣“民主”就不斷完善“自身免疫”機制,正因為如此,它就有無限地可完善性,不斷解除自身界限地可能性。
總之,德里達在《友誼政治學》書中以其深邃的思想對‘政治進行傳統意義上的解構,它肯定了一個沒有傳統政治意義上的敵人與朋友的人類新政治時代,從而也宣告了一種世界主義者的強烈愿望。在這樣的觀點基礎上,后現代的政治模式漸漸消解了傳統政治,將友愛、朋友、民主等概念作為解構主義策略中的對象,表明德里達解構思想的現代特征。
參考文獻:
[1](法)伯努瓦﹒皮特斯著.德里達傳[M].魏柯玲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
[2]陸揚.德里達的幽靈[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8.
[3]俞吾金,陳學明.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流派新編(下)[M].復旦大學出版社,1989.
[4](法)德里達著.友愛的政治學及其他[M].胡繼華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
[5]岳梁.幽靈學方法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6]汪堂家.汪堂家講德里達[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7]尚杰.悖謬與后冷戰時代的政治哲學—讀德里達<友誼政治學>[J].社會科學輯刊,2007(03).
[8]復且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編:《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評論》第二輯,復且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210頁.
[9]劉婷:《讀德里達傳的幾點思考》,選自《中國美學研究》( 第四輯),第316頁.
[10]轉引自高橋哲哉:德里達,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頁.
[11]選自《悖謬與后冷戰時代的政治哲學—讀德里達<友誼政治學>》,尚杰,社會科學輯刊,2007年第3期,第15頁.
[12]胡繼華:《友愛的政治學》及其他,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