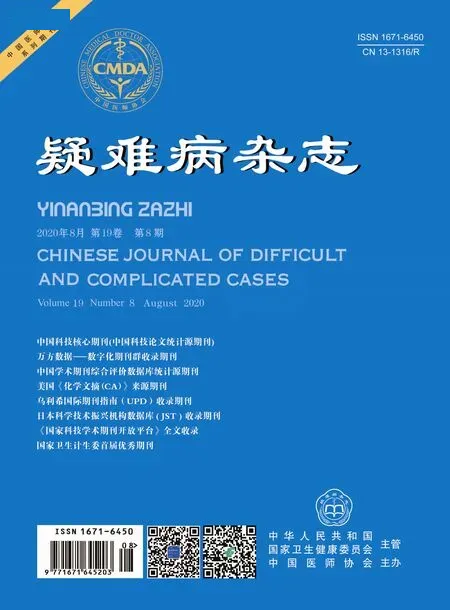家族遺傳性STING相關的嬰兒期發病血管病1例
張蕾,田利遠
STING是干擾素基因刺激蛋白,STING相關的嬰兒期發病血管病(STING-associated vasculopathy with onsetininfancy,SAVI)是由編碼STING的TMEM173基因突變引發的一系列臨床癥狀,其中包括間質性肺疾病、皮疹、關節炎等。國內對該病報道罕見,且無家族遺傳性病例報告。現報道筆者醫院收治的1例經基因檢查診斷明確的家族遺傳性SAVI病例。
1 臨床資料
先證者,男,9歲,主因“活動后氣促、咳嗽8年余,關節疼痛4個月,加重3 d”于2016年5月19日入院。患兒于1歲開始走路后,家屬發現患兒與同齡兒相比,活動耐力差,于活動后容易出現氣促、咳嗽,干咳為主,痰不多,無喘息,無咯血,營養狀態中等,曾就診于當地醫院,查X線胸片示支氣管肺炎,給予對癥治療(具體用藥家屬不能詳述)共40余天。患兒病情無明顯改善。家屬未再進一步診治。8年內患兒仍有活動后氣促,活動耐力差,間斷咳嗽,偶訴有胸悶癥狀,全身間斷出現散在淡紅色皮疹,無長期發熱。入院前4個月患兒無明顯誘因出現關節疼痛,為游走性,累及雙側膝關節、腕關節、指(趾)間關節,雙手中指近端關節腫脹,曾就診當地診所,給予“口服麝香風濕膠囊、貞芪扶正顆粒、風痛片、潑尼松片”治療,疼痛稍緩解。入院前3 d患兒關節疼痛加重,伴跛行,咳嗽次數較平時增多,伴胸悶、氣短,就診當地縣醫院查類風濕因子 47.9 IU/ml,ESR 75 mm/h;X線胸片示間質性肺炎、右側胸膜炎。為進一步治療轉診我院。患兒系第1胎第1產,足月順產,出生體質量4.6 kg,母孕期無異常,出生時無缺氧、窒息史。其父親自10余歲時即有氣短、胸悶、咳嗽癥狀,無長期低熱、盜汗,不能從事重體力勞動,曾間斷治療,癥狀無明顯好轉(入院后其父親測經皮血液氧飽和度93%)。母親身體健康。
查體:T 36.9℃,R 34次/min,P 80次/min,BP 106/60 mmHg。裸氧狀態下測經皮血氧飽和度95%,神清,精神反應可,全身可見散在淡紅色斑丘疹,有卡瘢,鼻翼兩側面頰部可見暗褐色斑疹,呼吸稍促,無鼻扇,三凹征陰性。雙肺呼吸音粗,未聞及干濕性啰音,心臟未聞及雜音,肝脾不太。四肢末梢發紺,呈杵狀指(趾),雙手中指近端關節腫脹,活動時疼痛;右足第1、2跖骨處有壓痛,活動障礙,足背動脈搏動好。
實驗室檢查:血WBC 8.7×109/L,L 46.1%,N 49.1%,Hb 124 g/L,PLT 400×109/L,CRP 13.1 mg/L。類風濕因子、ASO正常;ESR 41mm/h;補體C3正常,補體C4 0.62 g/L;自身抗體、抗核抗體、抗角蛋白抗體、抗平滑肌基底膜抗體均陰性。血管炎四項:抗中性粒細胞胞漿抗體(pANCA)陽性,余陰性。總淋巴細胞分析大致正常。肺功能:肺活量占預計值47%,用力肺活量(FVC)占預計值44.7%,第一秒用力呼氣容積(FEV1)占預計值50%,FEV1/FVC 94%,提示限制性通氣功能障礙。呼出氣一氧化氮測定 14.4 ppb。胸部CT:雙肺間質性改變,雙肺多發囊性變,小葉中心型肺氣腫改變,縱隔及腋下小淋巴結影,雙側胸膜增厚,右側為著,少量胸腔積液不除外。支氣管鏡檢查:左右主支氣管及其分支開口通暢,位置形態正常,雙側支氣管黏膜稍充血,左舌、左下葉前段支氣管灌洗時見黏膜粗糙、蒼白,有少量白色絮狀分泌物吸出,通氣尚可,未見異物。腕關節超聲:雙側腕關節結構及血流未見明顯異常。
留取患兒及其父母血液標本進行基因檢測,檢測結果提示患兒攜帶的TMEM173基因c.824C>T(p.R281Q)雜合突變,突變來源于患兒父親,為常染色體顯性遺傳(圖1)。確診為STING相關嬰兒期起病血管病,伴有間質性肺疾病及關節癥狀、皮疹。患兒口服托法替尼治療6個月,但臨床癥狀無明顯好轉,自行停藥。隨訪至今,患兒仍有間斷咳嗽、關節疼痛癥狀,活動耐力減低。患兒父親已因該病去世。患兒弟弟亦行相關基因檢查,結果提示存在同位點基因突變,胸部CT亦提示間質性肺病改變,但目前尚無特殊臨床癥狀,仍在隨訪中。家系圖見圖2。
2 討 論
嬰兒期起病的STING相關血管病是2014年新報道的一種血管病/炎綜合征,屬于自身炎性疾病,是由編碼STING的TMEM173基因發生突變,導致STING基因功能增強性突變,使得STING持續活化,促進炎性因子的持續釋放,IFN產生不斷增多,最終導致自身炎性綜合征[1]。
cGAS—cGAMP—STING信號轉導通路是SAVI發生的關鍵,也是近年自身免疫性疾病或自身炎性疾病研究的熱點。干擾素基因刺激蛋白STING,是胞漿DNA激活免疫反應的關鍵蛋白,但它本身并不能識別DNA,需經過環狀核酸分子激活[2]。環鳥苷酸—腺苷酸合成酶(cGAS)是2013年新發現的一種細胞內DNA 感受器[3],cGAS激活后催化三磷酸腺苷(ATP)和三磷酸鳥苷(GTP),合成環鳥苷酸—腺苷酸(cGAMP)。STING受到cGAMP刺激后被激活,誘導Ⅰ型干擾素和炎性因子的表達[4-5]。
SAVI臨床癥狀可出現皮疹、壞疽、毛細血管擴張、反復發熱、間質性肺病、關節炎、T細胞減少等[1],其中肺部癥狀起病隱匿,容易被忽視,主要表現為呼吸急促、活動受限。胸部CT檢查多見間質性肺炎改變。鑒于SAVI的發病機制,目前認為SAVI屬于Ⅰ型干擾素病[6],目前已知多種基因突變可導致Ⅰ型干擾素病,典型病例如Aicardi-Goutieres(AGS)綜合征,主要表現為嚴重智力與運動發育遲緩、肌張力障礙、獲得性小頭畸形、凍瘡等,頭顱影像學提示顱內多發鈣化、腦白質發育不良及腦萎縮[7]。SAVI與其他Ⅰ型干擾素病不同的是,它是目前惟一已知的以肺部受累為主要表現的Ⅰ型干擾素病[8],研究者發現STING廣泛表達于血管內皮細胞、Ⅱ型肺泡細胞和支氣管上皮和肺泡巨噬細胞,STING引起的功能障礙導致血管閉塞同時激活局部巨噬細胞和肺泡上皮細胞[9],肺活檢的典型特征是Ⅱ型肺泡上皮細胞增生、淋巴細胞浸潤和間質纖維化[10]。
檢索文獻,目前國內已報道該病5例[11-13],主要表現為反復咳嗽伴活動耐力下降,伴有杵狀指。肺功能提示限制性通氣功能障礙伴彌散功能減低;肺部高分辨CT提示符合間質性肺炎,并局限性肺氣腫、肺大泡形成。其中有3例患兒間質性肺疾病并發彌漫性肺泡出血。肺活檢病理:肺泡腔擴張,其內見大量泡沫狀組織細胞聚集,伴Ⅱ型上皮細胞增生,與Jeremiah等[10]報道一致。以上5例患兒基因檢查結果均提示TMEM173基因雜合新生突變(c.463G>A,p.V155M)。本例患兒主要表現與國內外多數病例報道表現一致。總結國內病例,發現所有病例均以間質性肺炎為首發并且是最主要的癥狀。目前已知常見引起間質性肺疾病的基因突變包括表面活性蛋白B基因(SFTPB)、表面活性蛋白C基因(SFTPC)、三磷酸腺苷結合盒轉運子A3(ABCA3)和甲狀腺轉錄因子1的基因突變等[14]。但對于TMEM173基因突變報道較少。目前國內報道的SAVI均為新發突變(c.463G>A,p.V155M)。本研究為國內首例報道家族遺傳性突變,致病基因TMEM173基因c.824C>T(p.R281Q)雜合突變,突變來源于父親。
張巖等[11]總結國內外文獻報道,發現糖皮質激素治療SAVI療效欠佳,可用于鑒別自身免疫性疾病。鑒于SAVI發病機制,Janus激酶抑制劑可能有利于阻斷Ⅰ型IFN信號傳導。魯昔洛替尼(ruxolitinib)和巴里替尼(baricitinib)都是JAK1和JAK2抑制劑,而托法替尼(tofacitinib)是JAK3抑制劑,在較小程度上是JAK2抑制劑。因此魯昔洛替尼和巴里替尼治療SAVI的療效優于托法替尼[8]。但該類藥物尚處于臨床研究階段,有待于更多的臨床數據證實其療效。
總之,SAVI以間質性肺炎為主要表現,可伴有皮疹、關節疼痛等癥狀,肺部影像學以多發囊性病變為特點,基因檢查可最終確診,可有家族遺傳性。目前尚無特效藥物治療,需進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