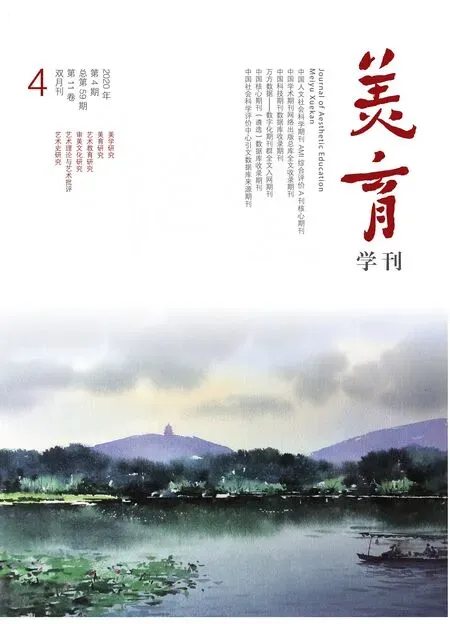跨藝術比較:“伊卡洛斯”在文學與繪畫之間的轉換
趙建國
(河西學院 文學院,甘肅 張掖 734000)
16世紀尼德蘭畫家彼得·勃魯蓋爾的油畫《風景與伊卡洛斯墜落》取材于古羅馬詩人奧維德的《變形記》中伊卡洛斯墜海而亡的神話。20世紀英裔美國詩人奧登依據勃魯蓋爾的四幅油畫《冬日時光的溜冰者和捕鳥器》《伯利恒的戶口調查》《伯利恒的嬰兒屠殺》以及《風景與伊卡洛斯的墜落》寫成了“讀畫詩”——《美術館》。《冬日時光的溜冰者和捕鳥器》是一幅風景畫,《伯利恒的戶口調查》和《伯利恒的嬰兒屠殺》題材來自《圣經·新約·馬太福音》。本文擬以上述作品為例進行跨藝術比較,分析以伊卡洛斯墜海為主要題材的作品如何從詩歌轉換為繪畫,又如何從繪畫轉換為詩歌。
伊卡洛斯墜海而亡的神話最早記載于古希臘典籍《希吉諾斯文集》,希吉諾斯是希臘神話家,生活在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1世紀,他的著作中有關希臘神話成為奧維德《變形記》的來源。《變形記》關于伊卡洛斯的墜落是這樣記述的:
下面垂竿釣魚的漁翁,扶著拐杖的牧羊人,手把耕犁的農夫,抬頭望見他們都驚訝得屹立不動,以為他們是天上的過路神仙。在左面,他們早飛過了朱諾的薩摩斯島、提洛島和帕洛斯島;在右面,他們飛過了勒賓托斯島和盛產蜜蜂的卡呂姆涅島。伊卡洛斯愈飛愈膽大,愈飛愈高興,面前是廣闊的天空,心里躍躍欲試,于是拋棄了引路人,直向高空飛去。離太陽近了,太陽煅熱的光芒把粘住羽毛的芬芳的黃蠟烤軟烤化,伊卡洛斯兩臂空空,還不住上下拍打,但是沒有了長槳一般的翅膀,也就撲不著空氣了。他淹死在深藍色的大海里,直到最后他口里還喊叫父親的名字。后人就給這片海取了少年的名字。[1]
《變形記》中伊卡洛斯墜落神話解釋了地名的由來,即伊卡洛斯墜亡的海域命名為伊卡洛斯海,埋葬伊卡洛斯的海島叫伊卡利亞。表面上看,伊卡洛斯的神話是因其自負不聽父親代達羅斯的勸告而引發的悲劇,深層意義為“父債子償”式命定論。代達羅斯曾因嫉妒殺害了他的學生斯塔洛斯,父親犯下的罪行,由兒子償還。《變形記》中還有一則太陽神之子法厄同駕日車墜亡的神話,相比而言,法厄同駕日車墜亡的神話顯得更為古老,伊卡洛斯墜落的神話或許是這則神話的翻版或改寫。
勃魯蓋爾的油畫《風景與伊卡洛斯墜落》,主要以場景和細節來再現伊卡洛斯的墜落。在油畫的右下角,伊卡洛斯的腿在水面上絕望地掙扎,他被散落的羽毛環繞著,畫面中牧羊人、漁夫和農夫均專注于自己的工作無視這一災難性場景。勃魯蓋爾并沒有表現伊卡洛斯如何飛向太陽,也沒有表現蠟翅如何融化。畫家只是畫了他的兩條腿在海上濺出水花的瞬間,而且,伊卡洛斯墜海而亡被放置于一個細小的不引人注意的方位,油畫似乎在刻意掩蓋或者淡化這個事件。相反,勃魯蓋爾重點描繪農夫犁田,牧羊人放羊以及漁夫專注釣魚。油畫對《變形記》敘述情節的處理使得繪畫的主題發生陡轉,更像是一幅安靜祥和的風景畫,伊卡洛斯墜落變成了不仔細看幾乎難以發現的細節。
法國學者喬治·迪迪-于貝爾曼的《在圖像面前》一書分析了彼得·勃魯蓋爾的油畫《風景與伊卡洛斯墜落》,但主要不是對整幅畫的解讀,而是重點闡釋伊卡洛斯墜海瞬間飛舞的羽毛和水中泛起的泡沫的細節。這個細節不是《變形記》中描述的細節,而是勃魯蓋爾想象性的添加。于貝爾曼分析道:“……布魯日爾(即勃魯蓋爾)這幅畫中的羽毛也是一個,甚至是唯一的一個故事、一個敘述說明:這是一個正在沉入海里的人體(一個‘落海的’隨便什么人),它和這些在畫中的不起眼的但卻獨自將‘伊卡洛斯’的含義表達出來的羽毛同時發生。在這種意義上,羽毛是為表現神話場景所必需的肖像學的特性。”[2]340-342羽毛飛舞的細節不可或缺,在一定程度上,這一細節濃縮指涉了整個神話,類似文學修辭——借代。著名的圖像學家潘諾夫斯基指出:“肖像學這個詞的后綴是從希臘文的動詞(‘寫作’)發展而來的,他暗示了一種對過程的純粹描述性方法——有時甚至是敘述性的方法。”[3]34-36肖像學是圖像學的術語,“是藝術史中研究與藝術形式相對的藝術題材或含義的一個分支”[3]31。油畫《風景與伊卡洛斯墜落》的題材是古希臘的神話傳說,一個與古典有關的題材,也是古典神話傳播的載體。潘諾夫斯基認為,題材和含義主要有三類:“1.基本的或自然的題材,又分為事實性或表現性題材;2.從屬的或約定俗成的題材;3.內在含義或內容。”[3]37依此分類,油畫《風景與伊卡洛斯墜落》屬于從屬的或約定俗成的題材。肖像學的特性意指描述性和敘述性的過程,繪畫因媒介限制,描述性和敘述性的過程被省略或用局部代替整體,因為伊卡洛斯的神話在西方人所皆知,無須整體性呈現。
回到跨藝術比較的視角,跨藝術比較主要關注的是藝術之間的互動轉換。從奧維德詩歌《變形記》到勃魯蓋爾油畫《風景與伊卡洛斯墜落》,不同藝術之間的互動轉換是怎樣實現的呢?
首先,詩歌的動態敘述轉化為繪畫的靜態呈現。由于文學與繪畫分屬不同藝術門類,《變形記》中對伊卡洛斯神話是一種過程性的敘述,而油畫僅是對瞬間的再現。誠如法國學者喬治·迪迪-于貝爾曼所言:“布魯日爾的整幅畫的畫面從其精確度本身來講就像一個被過度壓縮的空間。簡而言之,細節的特征在此將只與功能的多重性相適合,它不接受一切單一的說明。”[2]342勃魯蓋爾的油畫《風景與伊卡洛斯墜落》中人物、景物與物體并置集中,形成一個壓縮性的空間,動態敘述就轉化為靜態再現。
其次,詩歌場景的遷移轉化為繪畫場景的組合疊加。《變形記》中伊卡洛斯飛行是時間性的,他飛越了薩摩斯島、提洛島、帕羅斯島、勒賓托斯島以及卡呂姆涅島。詩歌中這種大跨度的距離和不斷轉換的空間在繪畫中難以表現,處理的方式只能是對不同時空的場景進行組合疊加。
再次,詩歌中人物的驚訝表情、伊卡洛斯的飛行過程和心理活動不是繪畫表現的焦點,因而被繪畫刻意省略或不予呈現。萊辛在《拉奧孔》中曾指出:“繪畫由于所用的符號或摹仿媒介只能在空間中配合,就必然要完全拋開時間,所以持續的動作,正因為它是持續的,就不能成為繪畫的題材。繪畫只能滿足于在空間中并列的動作或是單純的物體,這些物體可以用姿態去暗示某一種動作。”[4]勃魯蓋爾的油畫《風景與伊卡洛斯墜落》(圖1)中,時間性的過程毫無痕跡,而用伸出的雙腿、飛舞的羽毛以及泛起的泡沫來暗示伊卡洛斯墜落的動作。

圖1 勃魯蓋爾的油畫《風景與伊卡洛斯墜落》,圖片來源網絡
除保留伊卡洛斯這個人物外,繪畫通過簡化、聚合、疊加、省略、模糊等手段重新構筑畫面,呈現與詩歌不一樣的主題,即人情冷漠。勃魯蓋爾油畫場景中人們并沒有注意到海上所發生的奇怪而恐怖的死亡事件,慘劇已經發生,然而真正的情節敘述在于漁夫、農夫和牧羊人依然故我地各行其是,他人的苦難與己無關。
如果說,勃魯蓋爾的油畫《風景與伊卡洛斯墜落》是一次從文學到繪畫的跨藝術轉換,那么,詩人奧登的“讀畫詩”《美術館》則是從繪畫到詩歌的第二次跨藝術轉換或輪回再現。奧登的詩作《美術館》這樣再現勃魯蓋爾的油畫:
關于苦難,這些古典大師
他們從來不會出錯:他們多么深知
其中的人性處境;它如何會發生,
當其他人在吃飯,正推開一扇窗,或剛好在悶頭散步,
而當虔敬的老年人滿懷熱情地期待著
神跡降世,總會有一些孩子
并不特別在意它的到來,正在
樹林邊的一個池塘上溜著冰。
他們從不會忘記:
即便是可怕的殉道者也必會自生自滅,
在隨便哪個角落,在某個邋遢地方,
狗還會繼續過著狗的營生,而施暴者的馬
會在樹干上磨蹭它無辜的后臀。
譬如在勃魯蓋爾的《伊卡洛斯》中:一切
是那么悠然地在災難面前轉過身去;那個農夫
或已聽到了落水聲和無助的叫喊,
但對于他,這是個無關緊要的失敗;太陽
仍自閃耀,聽任那雙白晃晃的腿消失于
碧綠水面;那艘豪華精巧的船定已目睹了
某件怪異之事,一個少年正從空中跌落,
但它有既定的行程,平靜地繼續航行。[5]
奧登的這首詩是伊卡洛斯墜海而亡神話的又一次藝術表現,奧維德的《變形記》是詩體,《美術館》也是詩體,從詩歌開始,經過繪畫,又重新回到詩歌,經過兩次藝術轉換,從詩歌開始又回到詩歌,恰似一種輪回。那么,從油畫《風景與伊卡洛斯墜落》到詩歌《美術館》,藝術之間的互動轉換又是怎樣實現的呢?
第一,奧登的詩作《美術館》雜糅了勃魯蓋爾的四幅油畫,抽象概括統一主題,根據主題的需要,抽取繪畫中的場景。《美術館》整首詩分為兩節,前一節糅合了勃魯蓋爾的三幅畫,即《冬日時光的溜冰者和捕鳥器》《伯利恒的戶口調查》和《伯利恒的嬰兒屠殺》。風景畫與宗教畫合二為一,凸顯了寧靜與暴虐、祥和與死亡之間的張力。后一節才是對伊卡魯斯墜海而亡的神話的敘寫。毋庸置疑,奧登《美術館》的主題即是苦難,這在詩歌的第一句表述得很明晰。像耶穌和伊卡洛斯這樣的神話英雄,他們造福人類或征服自然的壯舉,成為人類長久以來的記憶,即使蒙難殉道或獻身也與他人無關,神話英雄的崇高感油然而生。從繪畫文本到詩歌文本的轉換方式,如法國學者薩莫瓦約所言:“文本之間求同存異的效果可以按照四種方式產生:組合(configurationg)、再現(refigurationg)、歪曲(defigurationg)、改頭換面(transfigurationg)。”[6]140可以說,奧登的詩作《美術館》綜合運用了如上組合、再現、歪曲及改頭換面的方式,在此前作品的基礎上進行了跨媒介再次加工。
第二,奧登的詩作《美術館》從看與聽兩個方面形成較為明顯的對比,它還原了人物動作及心理狀態。第一節詩中普通人吃飯、散步、溜冰,“狗還會繼續過著狗的營生,而施暴者的馬會在樹干上磨蹭它無辜的后臀”,大部分人對于耶穌的降生漠不關心。第二節詩中人們面對災難,“一切是那么悠然地在災難面前轉過身去”,正視變成了背對;“那個農夫或已聽到了落水聲和無助的叫喊”,叫喊聲、水聲無人回應。繪畫與詩歌從色彩畫面或語言上說,它們都可以說是視覺藝術或者具有視覺的要素,但詩歌既可看也可聽。根據繪畫表現主題的需要,奧登的詩作《美術館》敘寫了伊卡洛斯與農夫、伊卡洛斯與船之間的不同表現,對比凸顯無視苦難的主題。
第三,奧登的詩作《美術館》與勃魯蓋爾的油畫《風景與伊卡洛斯墜落》的手法相似,即把奧維德《變形記》的故事情節縮略萃取為場景與細節。詩歌中“太陽仍自閃耀,聽任那雙白晃晃的腿消失于碧綠水面”與油畫里伊卡羅斯墜海瞬間飛舞的羽毛和水中泛起的泡沫的細節以及雙腿水中掙扎的動作極為相似。
西方文藝史上以伊卡洛斯神話為題材的作品為數眾多,形成以伊卡洛斯神話為中心的題材史。有研究總結,“在《伊卡洛斯神話:從奧維德到W.畢爾曼》這部文本匯編中,編者匯總了從古到今的作家詩人如奧維德、賀拉斯、J.桑那扎羅(Jacopo Sannazaro)、歌德、波德萊爾、格奧爾格、奧登、E.揚德爾(Ernst Jandl)、W.畢爾曼(Wolf Biermann)等創作的伊卡洛斯形象,分為五大類:1.父與子:古希臘羅馬時期的代達洛斯與伊卡洛斯;2.罪人、英雄、愛人:文藝復興與巴洛克時期的伊卡洛斯;3.藝術家與殉難者:古典到古典現代的伊卡洛斯;4.反叛者與革新者:從表現主義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伊卡洛斯們;5.烏托邦主義者:當代德語文學創作中的伊卡洛斯”。[7]該研究采用分類的方法,對伊卡洛斯的主題史進行了梳理,但僅限于文學。美國詩人W.C.威廉斯(1883—1963)也寫過類似的題材,名為《有伊卡洛斯墜落的風景》。美國自白派女詩人安妮·塞克斯頓也以伊卡洛斯為題材寫作詩歌《寫給一位成功在即的朋友》。日本小說家三島由紀夫也創作過名為《伊卡洛斯》的詩,據說還是在飛機上創作的。伊卡洛斯在西方不同時期的文學中以不同形象出現,這說明神話本身蘊含著多義性,文學藝術家根據自己的解讀,賦予神話新的意義,伊卡洛斯也以新的形象不斷呈現。如果將伊卡洛斯的主題史擴展到整個藝術領域,那么,僅有類型學的研究是不夠的,尤其是伊卡洛斯的神話如何從一種藝術轉換為另一種藝術,就成為跨藝術比較研究的課題。
概括說來,伊卡洛斯墜海而亡的神話從奧維德的詩體《變形記》被勃魯蓋爾以油畫的形式再現,經過大約4個世紀以后,詩人奧登觀看勃魯蓋爾油畫寫作了詩歌《美術館》,又以詩歌的形式再現。藝術史上同一主題的文藝作品之間的疊加交織形成多重的互文性關系。互文性理論的創立者朱麗婭·克里斯蒂娃提出:“任何文本都是對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轉化。”[8]法國學者吉拉爾·熱奈特用“超文性”的概念來說明文本之間因互文性形成的派生關系。他說:“我用超文性來指所有把一篇乙文(我稱之為超文hypertexte)和一篇已有的甲文(當然,我稱之為底文hypotexte)聯系起來的關系,并且這種移植不是通過評論的方式來實現。”[6]40以這一理論來分析,勃魯蓋爾的油畫《風景與伊卡洛斯墜落》(超文)吸收利用了奧維德《變形記》(底文)的題材,而詩人奧登《美術館》(超文)則是對油畫《風景與伊卡洛斯墜落》(底文)的轉換再現。在西方藝術史上同一個主題被不同的藝術反復書寫改寫的現象,也屢見不鮮。荷蘭學者米克·巴爾指出:“通過重復使用早先作品中的形式,藝術家領會了文本,其中借用的典故得以解脫出來,同時用碎片建構新的文本。”[9]用碎片建構新的文本,這大概是從一種藝術轉換為另一種藝術的通則。由此可見,不同藝術之間的轉換或者改寫,絕對不是襲用或照搬原有題材,而是將其打碎選取重新組合加以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