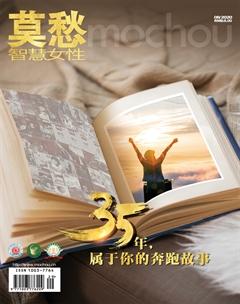鄭法娣:辦學20年,只因那匆匆一眼
曹宏萍

鄭法娣
早晨8點,江蘇宜興市景舟路兩邊大大小小的紫砂鋪子里,早起的手藝人靜靜地勞作。整條街朦朦朧朧地睡著,唯一靜中取鬧處,便是坐落于12號的宜興市紫砂小學。幾輛黃色的校車停在門口,教室里傳來孩子們清亮的讀書聲,和門口那抹黃一樣明晃晃的。聽得癡了,仿佛看見一顆顆種子正吮吸著養分拼命生長,在鄭法娣俯身耕耘了20年的土地上。
在門衛處辦公的校長
在當地婦聯工作人員的引導下走進宜興紫砂小學,卻發現校長鄭法娣的辦公室就在大門口的門衛處:一張舊桌,一臺老式電腦。一位埋頭批改作業的女性,戴著眼鏡,皮膚有些黑,笑容樸實而燦爛,讓人心生暖意。同行的宜興市婦聯宣傳部部長王亮介紹,她就是鄭法娣。“在門衛處辦公是為了讓孩子和家長更方便找到我。”從辦學之初,鄭法娣就把自己的辦公室設在了門衛處,猶如一位擺渡人,迎來送往。
四年級時跟隨父母從安徽省霍邱縣轉學到宜興的涂祎薇,兩次轉學考試都因其英語成績不合格而無法入學。“不能讓孩子沒有書念。”無奈之下,父母領著她敲開了紫砂小學門衛處的門。看到這三雙乞求的眼睛,鄭法娣二話沒說收留了涂祎薇。知道涂祎薇英語成績不好,鄭法娣還和英語老師一起每天放學后用半個小時給她“開小灶”。
小升初時,涂祎薇以丁蜀片區語數英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被畫溪中學錄取,但因家庭條件拮據,她無法繼續讀書。鄭法娣得知后連夜跑到涂家,做她父母的思想工作。第二天一早又趕到畫溪中學朱耀華校長家中,說明涂家的困難。朱耀華當即就說:“這么好的苗子怎么能輟學呢,全免!不但全免,還可以資助,實在不行我來資助。”
時間過得飛快,紫砂小學的孩子越來越多,一茬一茬地長大。誰能想到當初因為英語成績不合格無法入學的涂祎薇最終順利考入了北京外國語大學西班牙語系。拿著涂祎薇寫來的信,鄭法娣眼里滿是欣喜。
“家就是學校,學校也是家。”說起鄭法娣一家,家長和老師都說出了同樣的話。從辦學那天起,鄭法娣全家就住進了學校,全心全力撲在學生身上。每天早晨5∶40時她第一個爬上校車去接孩子們上學;每天放學之后,她坐在校門口的板凳上直到最后一個孩子被家長接走。
為了那一雙雙眼睛
談及當初創辦紫砂小學的初衷,鄭法娣的回答讓人動容。1998年的冬天,在丁蜀鎮査林小學做代課老師的鄭法娣和閨密周荷仙逛江南市場,偶然看到一個20多平方米既沒有窗口也沒有大門的昏暗車庫里,有位操著外地口音的中年男人正在給20多個凍得瑟瑟發抖的民工子女上課,課程內容很簡單,認認字念念詩。
那一雙雙渴求的眼睛,深深刻進了她的腦海。從那以后,在鄭法娣心里,讓民工子女也獲得基礎教育的想法,無比清晰且堅定,她萌生了辦學的念頭。恰逢上袁小學在撤并閑置進入公開拍賣階段,鄭法娣痛下決心辭掉了工作,停掉了已經開始搭建的新房,用夫妻倆省吃儉用積攢下的全部積蓄15萬元,和從朋友處借來的5萬元買下了當時破破爛爛的上袁小學,20萬元在當時并不是一個小數字。
學校有了,但辦學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第一學期,紫砂小學只有7個學生,1位老師——她的閨密周荷仙。鄭法娣和周荷仙一點也不敢松懈,和公辦小學一樣規范教學,但只收一半伙食費、學雜費,不收借讀費。紫砂小學接收外來民工子女讀書的消息口口相傳,第二學期,就迎來了300多名新入學的孩子,如今全校已經有1200多名學生在讀。
隨著辦學規模不斷擴大,教師人員不足成了問題,為了保證教學質量,鄭法娣四處奔走、求賢若渴。丈夫趙順根是一位中學老師,他20年如一日,每天早上天不亮出發,來回近兩個小時為孩子們采購最新鮮的午餐食材。后來,他索性離開任教的中學來到妻子的學校,“降級”為小學老師。如今,鄭法娣的兒子和兒媳也投身到教育事業之中。去年,經各級婦聯層層推薦,鄭法娣家庭獲評全國“最美家庭”。
不放棄任何一個孩子

鄭法娣給學生上課
學校步入正軌之后,漸漸地,鄭法娣發現了一個問題,班級里男生多女生少,一個班級可能有十個男孩,卻只有三個女孩。這成了她的一樁心事。她開始挨個做家訪,發現不少女孩輟學在家,楊海婷就是其中一個。由于家庭條件有限,父母讓兩個男孩優先讀書,楊海婷只能輟學在家。“如果您送孩子來我們學校的話,我們給您‘三免一。”鄭法娣當即免去了楊海婷的學雜費收她入學。從此以后,但凡家里有孩子未能入學的,鄭法娣都給予“三個孩子上學免除一個孩子學雜費”的優惠。“如果家里有五個孩子上學,那我們就免去兩個孩子的費用。到目前我們家訪到的所有家庭,戶口本上的孩子都已經入學了!”正因如此,宜興市婦聯將“性別平等進校園”項目落地紫砂小學,項目實施以來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效。

鄭法娣(右三)與學生家長交流
鄭法娣給予每個孩子最大限度的愛,對于那些身處困境的孩子她甚至是“偏愛”。學校成立后不久,一位家長找到了鄭法娣,孩子因殘疾行動不便,入學的事碰了不少壁,不忍心將孩子送到特殊教育學校的他們只能到鄭法娣這里“碰碰運氣”。“我們想讓孩子和普通孩子一樣接受教育,不求他有多大成就,只希望他將來不給社會添麻煩。”樸實的話語讓鄭法娣十分感動,她當即決定收下這個孩子,還專門為他定制了特殊的課桌椅,學習和生活都給予了更多的照顧。
孩子給了她更多驚喜
“其實開始的時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會產生怎樣的影響,直到一個個孩子長大了回到我的面前、一條條錄取的消息傳到我的手機里。辦學這些年雖然日子過得艱苦,但心里總是甜的。”20多年來,鄭法娣守著學校,送走了3000多名學生,播種著也收獲著。來自陜西的學生小羅,大學畢業后原本可以留在城里工作,但卻選擇到偏遠的學校任教。她說:“就像歌里唱的,‘長大后我就成了你,是鄭校長影響了我,讓我選擇了教育事業。”從學生到家長,這樣的事情還有很多。一次,一位中年男人找到學校提出要給教室粉刷墻壁。經過了解才知道,他是一位家長,見教室太老舊,想著用自己的一技之長為學校做點事,回饋老師們的辛勤付出。
“辦學第一年,我們的教職工沒有拿工資。后來辦學的事情傳開了,政府和婦聯組織給了我們很多幫助,鏈接了更多資源,越來越多的人加入到我們的隊伍中來,路也就好走了。”說起這些年的經歷,鄭法娣總是充滿感恩。
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從車庫那一瞥到辦起一所小學,從7名學生到3000多名,從迎接第一個學生踏上校車到目送最后一個孩子被家長接走,20年,鄭法娣把自己的全部獻給了孩子們。
圖片由本文主人公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