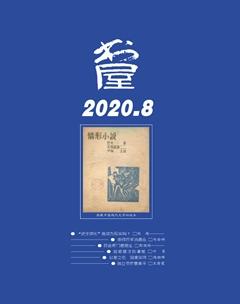醰醰多古情
朱航滿
谷林原名勞祖德,大半生從事會計工作,晚年寫作自娛,著述不多,但頗為識者所賞。有論者由谷林想到了曾做過會計的英國散文作家查爾斯·蘭姆,對此,谷林倒是有一番特別的自嘲:“蘭姆當了三十六年的小職員,他牢騷滿腹地說,他生平的偉大著作,都已被鎖藏進東印度公司的賬桌抽屜里。世上以會計工作終其身,直至退休的男男女女,只恐怕不止成千上萬,但像查爾斯那般發牢騷動人聽聞的有幾個呢?”谷林自認為“不敢去盲目與之攀比”,但諸如蘭姆這樣的會計人員,又能寫一手好文章者,世上又有幾人呢。谷林與一般的會計不同的是,他愛讀書,是個真正的書迷,而他曾供職多年的新華書店總管理處和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也都還算是個與文化打交道的地方。后來,他又調至國家歷史博物館,以十多年的時間,校訂一部二百余萬字的《鄭孝胥日記》,算是成為一個文化界的邊緣人物。也正是因為這段經歷,使得他因緣際會地與剛剛創刊的《讀書》雜志結緣,有幸成為這份雜志的編外校對和作者,也是讀書圈的一個小小佳話。
起初,谷林在《讀書》雜志所寫均為短章,借女兒之名作筆名,乃是有意于隱的。他給當時尚在《讀書》雜志任職的編輯揚之水的信中這樣寫道:“我只是想看看閑書消日,并非求學做學問,偶有會意,記以小文,自鳴其幸遇和歡悅,故讀寫皆屬‘計劃外項目,而讀更先于寫也。”這種無意為之的行為,卻使他很快收獲了一冊小書《情趣·知識·襟懷》,收錄于三聯書店的“讀書文叢”之中,與已頗有影響的王佐良、董鼎山、董樂山、流沙河等作家學人的作品同為一輯。數年后,他的另一冊讀書隨筆集《書邊雜寫》,列入遼寧教育出版社的“書趣文叢”第一輯,且得以與施蟄存、金克木、唐振常、辛豐年等名流的作品同列。這兩冊小書,令谷林在愛書人中聲名鵲起。《淡墨痕》是谷林生前出版的最后一冊文集,收錄在岳麓書社的“開卷文叢”第二輯之中。至此,谷林生前共出版文集三冊,總計字數不到四十萬字,可謂少矣。谷林去世后,由止庵編選其散落的文字,成為《上水船·甲集》和《上水船·乙集》,但就水準來說,遠不及谷林生前出版的三冊集子。
谷林雖晚來作文,但他起手極高;對于評價文章高下,則常常強調一個“回環咀嚼”,或者是否能夠“咀嚼慢咽”,故而在文章的立意、布局、修辭和素材使用上,谷林都是頗為講究的。在1995年給揚之水的一封信中,他談及了對于寫作讀書隨筆的理解:“寫書話,是不是宜把視線收緊些,引例最好‘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因為不是寫導讀,或曰學術性的評論,隨筆小品拿一本書來做引子,這是借他人酒杯,觸發自己的郁結,引例一多,放心難收,不免‘缺少景深。”在1998年給沈勝衣的一封信中亦有相似的論調:“前面說到的書話極好,是因為濃濃的感情皆淡淡著墨,不用長吁短嘆,沒有宏論儻議,切切實實寫出一些細節,此等風格不僅僅能求之知堂翁集中也。”也正因此,收錄在谷林生前出版的三冊集子中的文章,幾乎篇篇為佳,雖多是讀書小品,但并不泛泛寫來,也不長吁短嘆,更無艱澀的學術話語,均是能夠“切切實實寫出一些細節”,用他的筆頭盡可能把議論的“景深”拉得很遠,故而很有一些可以“回環咀嚼”之處。
現代以來的作家,谷林自始至終都最服膺知堂筆下的文章,而他研讀知堂文章也最為細心,有些甚至到了癡迷地步。《曾在我家》堪稱谷林的代表之作,乃是談他讀周著、藏周著,以及因此而結緣的書人往事。這是一篇寫讀者與自己仰慕的作家交往的文章佳構,寫他搜求周作人文集的往事,以及因此而兩次登門拜訪的經歷。文章沉靜而優雅,也留下了一份特別的文壇資料。《等閑變卻故人心》亦可作為谷林談知堂文章的代表之作,此文系其讀周氏《知堂回想錄》而作,但只談其中的一節《元旦的刺客》,并就周氏回憶1939年元旦在八道灣遇刺一事進行議論。對于周氏的回憶,谷林寫道:“敘事不過兩百字,全景已描繪得清清楚楚,推想當時運作,無非三五分鐘罷了。兩客先后開腔,合并字數,寥寥九字,此之謂要言不煩。”這“寥寥九字”,乃是刺客問:“你是周先生么?”作為學生的訪客沈啟無則回答另三個字:“我是客。”對于這三個字,谷林認為“大堪咀嚼”。由此,谷林繼而談這一對師生后來的關系破裂,并認為此或已為兩人交惡埋下了“伏筆”。
與《等閑變卻故人心》一樣令人“回環咀嚼”的,可推《繪畫,寫歷史》一篇,亦是在字里行間讀出了微意。此文談冰心的散文集《記事珠》,但谷林專門挑出其中的一篇散文《我的故鄉》來談,乃亦是“攻其一點,不計其余”。此文先從他在博物館整理嚴復日記的往事談起,頗有些白頭閑話的寂寞,并不經意地提及日記中的一句“謝子修故,八十七歲”。他在讀了冰心的散文《我的故鄉》后,恰恰證明了謝子修不但是冰心的祖父,且與嚴復是朋友的這個佐證,這種讀書,真有種他鄉遇故知的“幸遇和歡欣”了。到此,谷林又寫到了一個閑話,乃是他因此為“謝子修”所做的腳注上,特別加了“作家冰心的祖父”七個字,并希望由此“引逗某一些讀者的閑覽興趣”。文章至此,本亦該結尾了,谷林卻筆鋒又是一轉,寫到冰心關于童年讀書的記憶以及家庭出身的論述。但經過谷林的又一番考證,這兩條記敘均值得推敲。待到此時,谷林才寫到他作此文的意圖:“人們所有的回憶,不由自主,總是要經過情感的篩選。冰心也是在她記憶的畫本上繪畫吧?”
谷林的這種在字里行間讀出微妙之處,很能體現他作為愛書人的性情之處,想來也與他多年從事會計這一職業所養成的敏感細心很有些關聯的。他還有一些文章,諸如《〈爭座位帖〉與〈苦住貼〉》、《湘西一種凄馨意》、《牙簽與暮齒》、《汗漫游》、《版本的選擇》等,均是這樣值得“回環咀嚼”的篇章。在文章《湘西一種凄馨意》中,谷林特別對照了《湘行散記》和《湘行集》兩個不同版本中的內容,發現沈從文晚年對他這些早年的文字,曾做過大量“極為細微”的改動,“但也因之益見出作者的用心致密,著意推敲”,而這種“暮年經營”,在谷林看來,乃是“他始終沒有忘情文學工作”。至于沈從文改行轉業于文物研究,谷林在文章篇末亦有簡短論述:“原也是尋常行徑,然而由于外力的壓迫,實逼處此,自不能不令人思之于邑。”文章《版本的選擇》,對比兩本不同版本的梁實秋散文集,其中均收錄一篇《談聞一多》,但其中一個版本在聞一多的出生日期上,直接采用了公元紀年,但生辰卻沒有換成陽歷,故而鬧出了笑話。
以上略舉數例,不難看出谷林的書話文章,乃是“拿一本書來做引子,這是借他人酒杯,觸發自己的郁結”。《一個長期的旅程》和《諤諤一士》兩篇文章,均是令人刮目相看的短章。前者談馮友蘭的《三松堂自序》,后者談梁漱溟的《憶往談舊錄》,谷林均拈出兩位讀書人在政治年代的一段特殊遭遇,細究其間的微妙心思,其中頗有些動人心弦之處,這或許正是觸發了他這樣一個亦曾遭遇政治坎坷的小人物的“郁結”之處。可貴的地方還在于,谷林能夠在作文時做到“濃濃的感情皆淡淡著墨”,可謂“發潛德之幽光”矣。與此相類的,還有谷林在2002年8月致小友沈勝衣的一封書信中,寫他在《讀書》雜志上讀到《江河萬里》一文,由此想起與此文所談的著名水利學家黃萬里交往的一點逸事。1995年,谷林因胃癌在北京醫院住院,鄰床的病友枕側放了一冊《宋詞三百首箋釋》,而他也恰恰帶了此書。結識后,他才得知此人正系黃炎培的公子黃萬里。他繼而寫道,黃因反對某大型工程,“被戴上反蘇反社受苦二十年之帽”,“一意孤軍作戰如馬寅老”。
還有兩篇文章,亦是令人會心的。《共命與長生》一文,乃是從六個讀書人關于書的故事,來寫他對于書的態度:“‘誠知此恨人人有,把深愛的分散給也能愛的人們,使所愛的及時得所,豈非便是長生?”谷林生性淡泊,藏書不多,但頗有些令人愛慕的舊物,這些他生前多分散給他欣賞的后輩,使他的愛物終得以“長生”。另外一篇,則是《煮豆撒微鹽》,談及他極為喜愛的周作人文章《結緣豆》。周氏論及京師僧人在佛誕之日,“煮豆微撒以鹽”,“邀人于路請食之以為結緣”,并說他不必去“念佛拈豆”,“姑且以小文章代之耳”。谷林在文章中還引用周氏:“煮豆微撒以鹽而給人吃之,豈必要索厚償,來生以百豆報我,但只愿有此微末情分,相見時好生看待,不至倀倀來去耳。古人往矣,身后名亦復何足道,唯留存二三佳作,使今人讀之欣然有同感,斯已足矣,今人之所留贈后人者亦止此,此均是豆也。”無論怎樣評價周氏做此文的用意,但這又何嘗不應是所有做文章者的夫子自道。谷林于此處感慨:“宿業前緣,真令人無可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