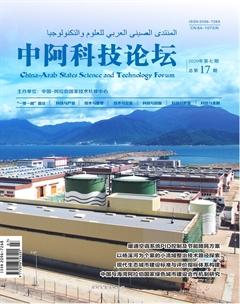基于共生理論的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協同發展策略
焦亮



摘要:基于共生理論構建城市共生單元的粵港澳大灣區共生經濟系統,測度了粵港澳大灣區各地市制造業與生產服務業的產業共生聚集度與協調度,通過人均GDP變異系數間接評價共生界面的功能。研究顯示,粵港澳大灣區各地產業共生關系差異較大,城市間的經濟共生水平較低,須完善產業間共生機制、強化城市經濟共生界面,粵港澳大灣區才能向高級協同發展。
關鍵詞:粵港澳大灣區;共生理論;產業聚集;產業協調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是中央支持香港和澳門融入國家戰略、促進內地和港澳地區共同繁榮、共同發展的重要途徑,更是中國所倡導“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全球化治理的重大戰略舉措,這注定了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道路將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有著根本區別,不同產業間、不同區域間以及與生態環境的共生共榮是其本質特征。文章從地區內產業共生關系和地區間區域經濟共生界面兩個層次對粵港澳大灣區不同地區產業協同發展中存在的問題與調整方向進行分析。
1 共生理論與產業協同發展的一般分析
共生理論最早來源于微生物學研究領域,由德國真菌學家德貝瑞(AntondeBary)于1879年提出,他認為“共生”是“不同種群共同生活在一起”的集居形式,是不同種群內在個體間發生的物質、能量聯系。共生現象不僅存在于生物界,而且也廣泛存在于人類社會體系。Mirata和Emtairah(2005)指出,不同經濟產業間的共生是在一定地理區域內,技術、資源、勞動力和資本等要素在不同產業間流動和交換所形成的長期合作關系[1]。胡曉鵬(2008)提出產業共生除了企業間的廢棄物交換外,還包括從基礎設施及服務共享到知識、技術及學習機制的共享等,產業共生是產業內或產業間的融合、互動和協調發展等關系的總和[2]。袁增偉等(2004)認為,產業共生應立足于生態學基本原理,結合經濟學基本規律和系統工程方法來經營經濟產業系統,同時對傳統產業系統按照這一思路加以改造,進而實現經濟、社會和環境整體效益最大化[3]。文章將以共生理論對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系統內各地產業共生現狀和優化路徑展開分析。
共生系統一般由共生界面、共生單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環境4個要素構成。共生單元是共生系統內能量生產和交換的基本單位。共生模式即共生單元間關系,是彼此之間物質、能量、信息的互換和交流關系,是決定共生系統結構強度的關鍵。共生界面是共生單元間接觸方式和途徑的總和,即共生單元間物質、能量、信息傳導的媒介,它是共生關系形成和發展的基礎。共生環境指共生單元、共生界面以外的所有影響因素的總和。經濟共生系統各要素間關系如圖1所示。
從制造業同生產性服務業的關系來看,它們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協同發展。謝泗新、李曉陽(2019)認為生產性服務業可以作為二、三產業加速融合的催化劑,它能夠為企業引入專業知識、技能人才和發展所需資本[4]。生產性服務業最初隸屬于制造業內部,隨著制造業規模的擴大和分工的深化獨立了出來,制造業的發展需求決定了生產性服務業的規模、種類和質量,同時生產性服務業提供的服務產品也成為制造業的快速增長和效率提升的黏合劑,它們之間是一種典型的共生關系。文章以共生理論的視角對粵港澳大灣區各地的制造業與生產服務業的共生關系及共生界面進行研究。
1.1 制造業與生產服務業間的共生關系
共生關系從行為方式視角可分為寄生、偏利共生、非對稱性互惠共生和對稱性互惠共生。李天放、馮鋒(2013)認為共生能量的生成與吸收消化可以衡量共生關系最基本的動態特征[5]。產業共生關系中如果某一方共生單元所吸收能量超出其生成水平并造成對方損害,則為寄生的共生關系,如雙方的能量生成與吸收水平相當,同時能夠使彼此獲益則為對稱性互惠共生。產業經濟中共生能量和物質的生成和吸收多用集聚度和協調度來測量,集聚度表征能量和物質的生成水平;協調度則表征產業間共生能量和物質吸收消化的協同效應。
Ellison.&.Glaeser提出的產業協同集聚度指標使用較為廣泛,該指標充分考慮到不同產業間市場結構差異,創造了市場結構度量產業地理集聚的途徑,所以測量出的產業集聚的水平能夠較好地解釋產業現實。后有研究者對Ellison.&.Glaeser(1997)提出的協同集聚度指標做了一定的修正,公式為:
其中wi、wj表示權重,可以通過計算單個產業產值或就業人數與兩個產業產值或就業人數之間的比例來得到,Hi、Hj、Hij分別表示第i和j產業以及兩產業之間所形成的地理集中度[6]。計算地理集中度的公式為:
其中GDPi為某產業在第i個地區的生產總值,teri為第i地區的行政地域面積,n為地區個數。協同集聚度γij是正向指標,計算結果越大表示兩產業空間集聚程度越明顯,即兩產業之間共生能量生成水平較高。制造業和生產服務業產業間的協同發展狀況介于協調與非協調之間,是一個模糊集合,模糊數學通常用[0,1]區間內的一個實數來表示某一元素隸屬于模糊集的程度,也可用來表示產業之間的協調度。文中根據汪茂泰的研究,采用隸屬度函數中分布密度函數來反映共生協調度,具體用制造業的實際產值與協調產值的接近程度來表示協調度[7]。上式C(s/m)表示生產性服務業對制造業的協調度,反映實際增長的生產性服務業與協調增長的生產服務業的接近程度;us用來表示生產性服務業產值的實際增長;表示為適應制造業的理想增長需求,即協調增長值;s2是生產性服務業實際增長值的方差。當實際生產性服務業增長值us越接近協調增長值時,產業協調度C(s/m)越大,表明兩個產業的共生協調程度越高;當實際生產性服務業增長值us偏離協調增長值越多,則協調度C(s/m)越小,意味著產業間共生協調程度就越低。文中通過歷年統計數據擬合生產服務系統對制造業系統的回歸模型=α+βum+ε,經一元回歸方程計算得到。
1.2 不同地區產業間的共生界面
區域經濟共生系統的共生界面包含多介質,即通過物質、信息、能源、資金等實現共生單元之間的交流,多重介質的功能發揮決定了共生經濟單元的趨同性,若共生系統逐漸趨向均衡說明共生界面功能穩定。文中通過測算衡量經濟共生系統的主要特征值各地人均GDP變異系數及相關系數的動態變化,來分析粵港澳大灣區經濟共生系統界面的功能。
2 粵港澳大灣區產業共生關系與共生界面的測度
2.1 各地制造業和生產服務業產業共生聚集度的測度
收集粵港澳大灣區各地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增加值以及各行政區面積,利用上述公式計算出2013~2017年間粵港澳大灣區各地制造業、生產性服務業以及兩產業相混合的地理集中度;再運用產業間集聚度公式計算得出粵港澳大灣區各地2013~2017年間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共生集聚度。文中的制造業范圍對應于統計年鑒中去除建筑業的第二產業,生產服務業則由交通運輸與郵政倉儲、信息、批發零售、金融、租賃商務服務、科技服務等6個行業組成。由于歷年統計范圍和口徑變動,江門和肇慶等地缺失的部分生產服務業數據通過第三產業減去房地產、餐飲等生活服務業簡介計算得出。澳門由于制造業數據偏小故不納入計算范圍,計算結果如表1所示。
2.2 粵港澳大灣區制造業和生產服務業產業共生協調度的測度
通過對2013~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制造業和生產服務業產值的數據(如表2所示)擬合得到:Y=-22534.9+1.658X,利用這一模型計算出生產服務業協調增長值,進一步計算得出2013~2017年間,產業共生協調度都接近于1,說明粵港澳大灣區制造業與生產服務業整體發展較為協調。利用這一模型進一步計算可得出2013~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各地產業共生協調度如表3所示。
2.3 共生界面功能——人均GDP變異系數
變異系數是衡量比較度量單位和均值不同時兩個以上數據組變異程度的統計量,通過數據組觀察值的標準差除以均值得到。文中根據表4統計數據計算2013年和2017年粵港澳大灣區各地人均GDP變異系數,分別為0.96和0.86,這一數值處于較高水平,遠大于國內的一些經濟合作區域,說明粵港澳大灣區共生經濟系統的均衡狀態遠未達到。
3 測度結果分析與結論
從產業共生聚集度即制造業和生產服務業的協同產出來看,大灣區各地的差異很大,粵港澳大灣區各地產業共生聚集差異較大。肇慶、江門、惠州產業聚集度很小,生產性服務業與制造業的協同集聚效應才剛開始發揮,需要政府和企業合力推進。廣州和珠海產業聚集度處于中間水平,廣州主要是行政區域地理面積的基數大從而拉低了聚集度,珠海則是制造業規模偏小導致。產業聚集度差異大將是粵港澳大灣區共生經濟體發展的主要阻力。
從產業共生協調度來看,雖然粵港澳大灣區制造業與生產服務業整體發展較為協調,但各個城市共生單元間差異也很大。香港、廣州和深圳生產服務業產業協調度較高,這是互惠型共生關系形成的基礎。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這一指標近年下降很大,反應了互惠型共生關系逐漸向偏利共生轉移的可能。佛山和肇慶則共生協調度很低,反應了生產服務業和制造業持續處于寄生關系這一狀態。
總體來看粵港澳大灣區雖然是我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但研究顯示經濟共生發展水平較低,共生界面功能發揮有限,造成城市經濟共生單元間變異系數較大。隨著粵港澳三地物質、能量、信息等交流通道的不斷改善帶來了變異系數的減少,同時由于制度等因素導致的差異仍然影響著粵港澳經濟共生體界面功能的發揮。要全面提升各個城市的高產業共生聚集度和協調度,構建具體產業城市間的合理共生機制,完善道路、信息等共生介質功能的發揮,才能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共生經濟系統走向高級協同,這將是后續研究的重點所在。
參考文獻:
[1]Mirata M,Emtairah T.Industrial symbiosis networks and the contribution to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J].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2005(10-11):993-1002.
[2]胡曉鵬.產業共生:理論界定及其內在機理[J].中國工業經濟,2008(09):118-128.
[3]袁增偉,畢軍,張炳,等.傳統產業生態化模式研究及應用[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4(02):109-112.
[4]謝泗薪,李曉陽.生產性服務業與區域經濟發展的耦合協調分析——基于京津冀地區的實證[J].商業經濟研究,2019(08):183-185.
[5]李天放,馮鋒.跨區域技術轉移網絡測度與治理研究——基于共生理論視角[J].科學學研究,2013(05):684-692.
[6]Ellison G,Glaeser E L.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 U S.manufacturing industries:A dartboard approach[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9(05):889-927.
[7]汪茂泰.產業協同集聚的測度方法及其應用:共生理論的視角[J].赤峰學院學報(漢文哲學社會科學版),2019(07):37-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