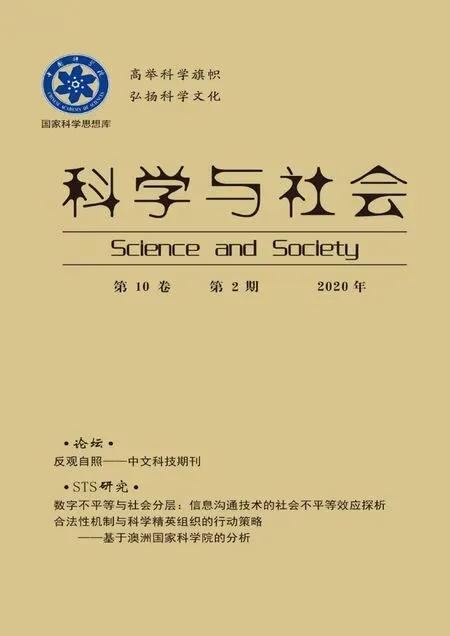跨文化比較視野下的日本生命倫理爭(zhēng)論
——讀洛克《雙重死亡:器官移植與死亡的再造》
白美妃 鄭 肯
(1 中國科學(xué)院科技戰(zhàn)略咨詢研究院; 2 北京大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系)
20世紀(jì)70年代,現(xiàn)代意義上的生命倫理學(xué)開始在日本出現(xiàn)。與其他東亞國家一樣,日本建立生命倫理學(xué)以及相關(guān)制度體系的過程,始于向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全面學(xué)習(xí)與模仿,包括英語文獻(xiàn)的翻譯介紹以及國外政策實(shí)踐的引入移植[1]。然而,一場(chǎng)興起于20世紀(jì)80年代的關(guān)于腦死亡和器官移植的爭(zhēng)論,為日本生命倫理學(xué)的后續(xù)走向烙上了一些具有本土特色的印記。在日本生命倫理學(xué)史上,這場(chǎng)關(guān)于腦死亡和器官移植的爭(zhēng)論后來被視作為一個(g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一方面,因?yàn)檎麄€(gè)社會(huì)(學(xué)術(shù)界、公眾、宗教團(tuán)體、政界……)都卷入了進(jìn)來,這場(chǎng)爭(zhēng)論無疑促進(jìn)了全國性的生命倫理意識(shí)啟蒙;另一方面,這場(chǎng)爭(zhēng)論本身也成為了日本后來解決生命倫理相關(guān)爭(zhēng)論的典范案例[2]。
1990年前后,英裔加拿大醫(yī)學(xué)人類學(xué)家瑪格麗特·洛克(Margaret Lock)正在日本開展醫(yī)學(xué)主題的田野調(diào)查,從新聞媒體鋪天蓋地的關(guān)于腦死亡和器官移植的討論中,她開始關(guān)注這一爭(zhēng)論。作為一位長(zhǎng)期關(guān)注日本醫(yī)學(xué)問題的北美人類學(xué)家,洛克敏銳地發(fā)問:這場(chǎng)爭(zhēng)論為什么會(huì)發(fā)生?在北美(以及歐洲的大多數(shù)國家和地區(qū)),公眾幾乎毫無困擾地接受了腦死亡和器官移植;然而在日本,這一議題卻引起了廣泛且持久的激烈爭(zhēng)論。那么,面對(duì)同一生命倫理議題,為什么日本和北美的公眾反應(yīng)如此不同?
圍繞這一問題,洛克花了十年時(shí)間,跟蹤日本的腦死亡與器官移植爭(zhēng)論,閱讀和分析相關(guān)領(lǐng)域的專業(yè)文獻(xiàn),參加醫(yī)學(xué)界的會(huì)議,拜見日本和北美兩地重癥病房的醫(yī)護(hù)人員、器官移植的醫(yī)生、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①在實(shí)踐中,洛克很難有機(jī)會(huì)對(duì)腦死亡的患者及其家屬進(jìn)行人類學(xué)的訪談。、普通的公眾以及日本反對(duì)腦死亡和器官移植的社會(huì)活動(dòng)家,進(jìn)行深度訪談。在此基礎(chǔ)上,洛克于2002年出版了一本關(guān)于日本腦死亡與器官移植爭(zhēng)論的厚重的民族志,即《雙重死亡:器官移植與死亡的再造》[3]。
一、技術(shù)進(jìn)步帶來的生命倫理難題
通過醫(yī)學(xué)史的追溯,洛克發(fā)現(xiàn):有關(guān)腦死亡與器官移植的爭(zhēng)論,其實(shí)源于一系列新興醫(yī)學(xué)技術(shù)的發(fā)明、應(yīng)用與匯流對(duì)人類社會(huì)既有的關(guān)于死亡時(shí)刻界定之共識(shí)①洛克認(rèn)為:在人類歷史中,對(duì)個(gè)體的死亡時(shí)刻進(jìn)行精確的界定,始終是一個(gè)重要的問題。每個(gè)具體的人類社會(huì),都曾經(jīng)不得不因應(yīng)世事變遷,而重新面對(duì)這一問題,經(jīng)歷爭(zhēng)議,并在經(jīng)驗(yàn)中形成各自相對(duì)穩(wěn)定的標(biāo)準(zhǔn)以界定生死。在20世紀(jì)初期的歐洲,隨著診斷技術(shù)的發(fā)展,關(guān)于死亡時(shí)刻界定的爭(zhēng)議已經(jīng)降至最低點(diǎn)。的重新擾動(dòng)。首先,自20世紀(jì)50年代以來,人工呼吸機(jī)的大量應(yīng)用挽救了無數(shù)本來必死的患者的生命。其次是20世紀(jì)60年代開始出現(xiàn)并不斷普及的體系化的重癥監(jiān)護(hù)室(ICU)。ICU是在整合了術(shù)后恢復(fù)、呼吸治療、休克治療等多個(gè)重癥醫(yī)療科室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而這些重癥醫(yī)療科室的出現(xiàn)則離不開心電圖、心臟復(fù)蘇等重大醫(yī)療技術(shù)的進(jìn)步。進(jìn)入ICU的患者通常面臨三種命運(yùn):第一種是康復(fù)出院,第二種是經(jīng)治療無效而走向死亡,第三種則是在以人工呼吸機(jī)為核心的重癥監(jiān)護(hù)器械的支持下,進(jìn)入了一種尷尬的“活死人”(living cadaver)的中間狀態(tài)—心肺依然正常運(yùn)轉(zhuǎn),維持著有規(guī)律的呼吸,但是腦部經(jīng)歷了不可逆轉(zhuǎn)的創(chuàng)傷,只能永遠(yuǎn)處于昏迷中。這類患者可能存活幾天或幾周,偶爾也有患者存活幾個(gè)月甚至一年之久。這一“活死人”的狀態(tài),突破了人類社會(huì)既有的生死邊界,帶來了潛在的倫理困境[3]64。
而器官移植技術(shù)的出現(xiàn)與應(yīng)用則使得上述潛在的倫理問題凸顯了出來。20世紀(jì)50年代,伴隨免疫學(xué)的發(fā)展成熟,人類器官移植由理論走向?qū)嵺`。1967年南非醫(yī)生實(shí)施了第一例人類心臟移植手術(shù),這開啟了器官移植成為常規(guī)醫(yī)療手段的歷史進(jìn)程。為了解決器官供應(yīng)源的問題,醫(yī)學(xué)界默契地將目光鎖定在了ICU中那些進(jìn)入了不可逆的昏迷狀態(tài)的“活死人”身上。
在這一背景下,以全力救護(hù)人類生命為最高宗旨的醫(yī)學(xué)界,不得不面對(duì)一個(gè)尤其突出的兩難的倫理困境。渴望獲得器官移植以延續(xù)生命的患者與在ICU中即將進(jìn)入“活死人”狀態(tài)的患者本應(yīng)是平等的個(gè)體生命。一方面,如果在個(gè)體死亡許久之后獲取器官,那么移植成功率會(huì)受到重要影響;另一方面,如若為了獲取可移植的器官,導(dǎo)致一個(gè)即將進(jìn)入不可逆的昏迷狀態(tài)的患者在真正“死亡”之前,就被摘取了器官,那么這一醫(yī)療實(shí)踐則涉嫌謀殺。因此,對(duì)潛在的“活死人”的死亡時(shí)刻進(jìn)行精確的界定,就成了一項(xiàng)關(guān)鍵的任務(wù)[3]66。1970年前后,國際醫(yī)學(xué)界“發(fā)明”了“腦死亡”的概念①1968年,哈佛大學(xué)醫(yī)學(xué)院腦死亡定義研究特設(shè)委員會(huì)形成了一份研究報(bào)告并發(fā)表在《美國醫(yī)學(xué)會(huì)學(xué)報(bào)》上。此報(bào)告提出了人類首個(gè)腦死亡判定標(biāo)準(zhǔn),后來也成為國際通行標(biāo)準(zhǔn)的基礎(chǔ)。(以作為法律上的個(gè)體生命的終點(diǎn)),并在數(shù)十年的實(shí)踐中不斷完善相應(yīng)的診斷指標(biāo)體系,在醫(yī)學(xué)界內(nèi)外盡力尋求最大的共識(shí)。
二、日本的腦死亡與器官移植爭(zhēng)論
究其本質(zhì)而言,生命倫理學(xué)是一種用以化解在生命科技發(fā)展中出現(xiàn)的社會(huì)政治與倫理矛盾的工具。因而某一具體的生命倫理工具在長(zhǎng)時(shí)段中的應(yīng)用潛力依賴于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社會(huì)公眾的(經(jīng)濟(jì)、政治與文化等層面的)利益訴求與價(jià)值表達(dá)[4]。作為一項(xiàng)生命倫理工具,國際醫(yī)學(xué)界所發(fā)明的腦死亡的概念并沒能無差異地被順利“移植”進(jìn)入各個(gè)具體的人類社會(huì)中。盡管在北美和日本兩地,整體的醫(yī)療技術(shù)和水平不相上下,神經(jīng)科與重癥科室的醫(yī)生用以診斷腦死亡所使用的邏輯風(fēng)格也極其相似,但是腦死亡的議題在兩地引起的公眾反應(yīng)卻相距甚遠(yuǎn)。在北美及歐洲的大多數(shù)國家和地區(qū),公眾相對(duì)輕易地接受了這一概念;然而,這一概念在日本社會(huì)引起了曠日持久的爭(zhēng)論,最終經(jīng)“調(diào)適修飾”后才勉強(qiáng)被接受。
事實(shí)上,早在1968年(世界首例人類心臟移植的第二年),日本北海道札幌市的和田壽郎醫(yī)生就實(shí)施了日本第一例心臟移植手術(shù),手術(shù)最初被認(rèn)為很成功,但是接受移植的患者在83天后死亡。這一事件后來在日本遭到了多方面的強(qiáng)烈譴責(zé),媒體和公眾對(duì)捐獻(xiàn)者的死亡認(rèn)定環(huán)節(jié)產(chǎn)生懷疑,而醫(yī)學(xué)界則質(zhì)疑采用器官移植這一治療手段的必要性,因此札榥地方檢察院向和田醫(yī)生提起了公訴。盡管1972年此案最終被判定不予追究,但是在日本生命倫理史上,此案被定性為一個(gè)駭人聽聞的丑聞事件。受此事件影響,日本的器官移植領(lǐng)域陷入僵局,此后直至1999年的30年間,日本幾乎沒有公開施行過任何與腦死亡捐獻(xiàn)者相關(guān)的器官移植手術(shù)[3]130-135。
為了推進(jìn)器官移植事業(yè),日本的醫(yī)學(xué)界不斷提出腦死亡立法的需求。自20世紀(jì)80年代初起,在日本,關(guān)于腦死亡與器官移植的爭(zhēng)論風(fēng)起云涌,支持和反對(duì)的力量紛紛利用紀(jì)錄片、電視劇、漫畫乃至能劇來表達(dá)觀點(diǎn)和引導(dǎo)公眾輿論,大大小小的民意調(diào)研數(shù)不勝數(shù),相關(guān)出版物迅速激增。此外,大量的公民社會(huì)組織、宗教團(tuán)體發(fā)起了無數(shù)次反對(duì)腦死亡立法的集會(huì)和示威游行。法律界與政界的專業(yè)人士非常清楚:在社會(huì)共識(shí)達(dá)成之前,腦死亡立法無法實(shí)現(xiàn)。
面對(duì)無休止的爭(zhēng)論,日本政府決定在這場(chǎng)爭(zhēng)論中發(fā)揮更積極的領(lǐng)導(dǎo)角色。1989年內(nèi)閣總理府成立了專門的腦死亡與器官移植調(diào)研臨時(shí)委員會(huì)。在多次調(diào)研國內(nèi)急診科室、舉辦公開聽證會(huì)、針對(duì)專家和公眾進(jìn)行問卷調(diào)查以及出國考察的基礎(chǔ)上,此委員會(huì)于1992年發(fā)布了報(bào)告[3]167-170。基于這一報(bào)告所形成的腦死亡立法的議案被提交給了國會(huì),但是多次被駁回,理由是公共爭(zhēng)論依然激烈,共識(shí)尚未達(dá)成。此后又經(jīng)歷了多年的拉鋸撕扯,日本終于在1997年通過了一項(xiàng)折中的解決方案,即《器官移植法》。這一法律并未明文規(guī)定腦死亡等同于個(gè)體生命的死亡,但是根據(jù)這一法律,被診斷為腦死亡患者的身體可以用于器官移植,只要患者生前以書面的形式表達(dá)了捐獻(xiàn)的意愿,且患者家庭①在《器官移植法》出臺(tái)數(shù)周之后,日本政府還發(fā)布了一項(xiàng)附則以澄清關(guān)于家庭的定義。根據(jù)這一附則,器官捐獻(xiàn)的知情同意涉及與腦死亡患者同居的所有親屬,包括祖父母及孫輩;家庭的“集體意愿”將由家庭自主決定并告知醫(yī)生;如果非同居的親屬表達(dá)了異議,那么器官捐獻(xiàn)的決定需要被重新考慮。沒有予以否決。此法律還規(guī)定死亡的時(shí)間需要被記錄兩次,分別是被認(rèn)定為腦死亡的時(shí)間與心臟停止跳動(dòng)的時(shí)間。換言之,腦死亡患者經(jīng)歷了雙重死亡,《器官移植法》恰好適用于兩次死亡時(shí)間中的特殊階段,如此,器官獲取的合法性才能成立[3]178-185。這些法律規(guī)則所包含的生命倫理認(rèn)識(shí)顯然迥異于北美。
為什么大多數(shù)的日本人不能(像北美人一樣)接受腦死亡和器官移植?在日本,主流的觀點(diǎn)(無論接受或反對(duì)腦死亡和器官移植)認(rèn)為:這是由于日本的傳統(tǒng)和文化在發(fā)揮作用,而北美(相對(duì)而言)則沒有背負(fù)歷史和文化的“包袱”。然而,人類學(xué)家相信:訴諸于籠統(tǒng)的“傳統(tǒng)”和“文化”等術(shù)語,并不足以“照亮”這一場(chǎng)曠日持久的爭(zhēng)論所包含的問題本質(zhì)。在不斷地將日本與北美(及西方社會(huì))的相關(guān)問題進(jìn)行跨文化比較的基礎(chǔ)上,洛克指出:日本人的確受到了其傳統(tǒng)與文化的限制而不愿意接受腦死亡和器官移植,但是,同樣地,北美人也正是由于其傳統(tǒng)和文化的影響而相對(duì)輕易地接受了腦死亡和器官移植[3]1-13。洛克所作的跨文化比較至少體現(xiàn)在如下三個(gè)層面:關(guān)于生命與死亡的本體論(什么構(gòu)成了死亡)、身體的商品化、“生命的禮物”的暗喻。
三、關(guān)于生命與死亡的本體論
自然與人文的二元對(duì)立論是現(xiàn)代世界中占支配地位的一種思想進(jìn)路,事實(shí)上,它構(gòu)成了近代以來西方理性思想體系的重要根基。在這一思想進(jìn)路下,自然依循科學(xué)的法則運(yùn)轉(zhuǎn),它是自在的,獨(dú)立于社會(huì)情境與道德秩序,因而自然與人文之間的邊界也是不證自明[5]1-7的。當(dāng)然,這一思想進(jìn)路正日益受到哲學(xué)家、歷史學(xué)家、社會(huì)科學(xué)家乃至自然科學(xué)家的挑戰(zhàn)。
法國人類學(xué)家德斯科拉(Philippe Descola)就是挑戰(zhàn)者之一。他將此二元對(duì)立論定義為“自然主義本體論”(naturalist ontology)①在其經(jīng)典作品《超越自然與文化》中,德斯科拉所使用的“本體論”一詞指的是“在人們的感知、實(shí)踐和觀念中存在的對(duì)于包括人在內(nèi)的存在體之本質(zhì)的‘看法’”,參考王銘銘. (2019).聯(lián)想、比較與思考: 費(fèi)孝通“天人合一論”與人類學(xué)“本體論轉(zhuǎn)向”. 學(xué)術(shù)月刊(8).。他建構(gòu)了一個(gè)二維的矩陣,試圖勾畫出分布于不同時(shí)空的人類群體識(shí)別(看待)人與非人存在(non-human being)的物質(zhì)性特質(zhì)(physicalities)/內(nèi)在性特質(zhì)(interiorities)的模式的所有庫存,以此來相對(duì)化“西方自然主義本體論”,從而顛覆它作為唯一真實(shí)的傲慢姿態(tài)。他將人類的本體論分為四類(如下圖),其中,自然主義本體論主張人與非人存在的物質(zhì)性特質(zhì)是一致的,而內(nèi)在性特質(zhì)則是不同的(只有人類具有心智)。他還認(rèn)為絕大多數(shù)的現(xiàn)代西方人(因教育的原因)都是不自覺的自然主義本體論者[6]112-125,232-244。德斯科拉的學(xué)術(shù)盟友拉圖爾(Bruno Latour)則指出:在自然與人文二元對(duì)立論的思想進(jìn)路下,“現(xiàn)代人”的工作事實(shí)上包含了兩組完全不同的實(shí)踐形式,其一是通過“轉(zhuǎn)譯”(translation)的工作將自然和人文混合起來;其二則是通過“純化”(purification)的工作將自然與人文(非人類與人類)的領(lǐng)域嚴(yán)格區(qū)分開來,兩組工作互為因果,不可分割[7]12-14。

圖1 人類的四種本體論
如上文所述,在以呼吸機(jī)為核心的重癥醫(yī)療器械的支持下,出現(xiàn)了一種尷尬的不死不活、既死又活的人類身體的狀態(tài),或曰“人-機(jī)混合體”(human-machine hybrid)的狀態(tài)。在自然與人文二元對(duì)立論的框架下,這一“人-機(jī)混合體”無疑是一種模糊的、歧義性的存在,因?yàn)樗黄屏俗匀慌c人文的嚴(yán)格區(qū)分,引起了倫理爭(zhēng)議、疑惑與焦慮。而接下來的任務(wù)就是對(duì)其進(jìn)行“純化”,歸入自然(非人類)或者人文(人類)的領(lǐng)域。在許多西方社會(huì),伴隨器官移植的常規(guī)化進(jìn)程,這類“人-機(jī)混合體”顯然被歸入了自然的領(lǐng)域,同時(shí)也被剝奪了作為人類社會(huì)成員的權(quán)利[3]39-42。這一“純化”的工作實(shí)際上包含了如下邏輯:在深受笛卡爾的身心二元論影響的西方社會(huì),人的心智被認(rèn)為存在于大腦中。一旦患者進(jìn)入不可逆的昏迷狀態(tài)(被診斷為腦死亡),那么心智就消失了,因而有意義的社會(huì)生命也就不復(fù)存在了,剩下的生物體盡管依然活著,但已經(jīng)成為了一種非人存在。正是基于這一邏輯,在北美,如果患者被確診為腦死亡,那么醫(yī)生會(huì)告訴家屬,“那個(gè)人(person)已經(jīng)逝去”[3]245,繼而醫(yī)生可以將患者留下的身體視為非人存在(中立的生物性客體)而進(jìn)行處理,允許器官獲取和移植,而不用承受倫理負(fù)擔(dān)。
然而,在日本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本體論顯然并不是自然主義的,盡管近代以來日本受到了西方思想的深遠(yuǎn)影響。洛克認(rèn)為日本人關(guān)于生命與死亡的本體論以本土的神道教(泛靈論)信仰為底色,又受到了佛教、儒家思想的雜糅影響。首先,泛靈論的觀念彌散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對(duì)普通的日本人而言,無生命的機(jī)械與工具也可以具有精神與生命,例如汽車、地鐵、取款機(jī)、電梯都能夠善解人意,以得體的方式與用戶對(duì)話互動(dòng)。在技術(shù)工人眼里,他們所使用的機(jī)械與工具并不是外在的異化之物,而是自身的精神延展,是自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機(jī)械與工具并不是受人役使,而是作為伙伴,與人類一起工作,這構(gòu)成了一種美好的人-機(jī)混合體的狀態(tài),日本的許多科幻與漫畫作品都體現(xiàn)了這一要義[3]370。與此形成對(duì)照的是,在北美,如果說一個(gè)人失去了意識(shí)/心智,依附于機(jī)器而存在,例如,已經(jīng)腦死亡的患者只能借助呼吸機(jī)延續(xù)肉體生命,那么這一人-機(jī)混合體的狀態(tài)被認(rèn)為是有辱人格尊嚴(yán)的,是絕對(duì)不可接受的,但是在日本卻有一定的文化兼容度。
其次,在東亞哲學(xué)傳統(tǒng)中,關(guān)于如何理解個(gè)體與自然世界之關(guān)系,“氣”的概念非常關(guān)鍵。在這一思想脈絡(luò)下,個(gè)體的健康狀況、精神面貌、命運(yùn)福祉都依賴于“氣”在身體中的順暢運(yùn)行。在日本,中醫(yī)、茶藝、武術(shù)、插花、書法、寫詩等活動(dòng),均被認(rèn)為具有調(diào)理氣息的功用,通過這些活動(dòng),個(gè)體可以放松身體、放空心靈,達(dá)到身心合一的狀態(tài),從而回歸“內(nèi)心”本我。對(duì)于日本人而言,一個(gè)人的核心與本質(zhì)并不是在頭腦中,而是在“內(nèi)心”。值得注意的是,“內(nèi)心”并不是一個(gè)解剖學(xué)意義上的器官,而是一個(gè)文化集體想象的概念,是一個(gè)人真實(shí)情感所在之處,是一個(gè)人穩(wěn)定的內(nèi)在自我的源泉[3]226-229。日本人所謂的一個(gè)人的內(nèi)在自我,顯然不同于西方社會(huì)文化中“個(gè)人”(person)的概念。
然后,洛克指出:對(duì)祖先的尊敬之心,是許多日本人反對(duì)腦死亡的最重要原因,盡管這一因素在公共討論中很少被提及。不同于基督教傳統(tǒng)下的西方人,日本人將個(gè)體的生命理解為家族世系的一部分,而家族世系的生命則可以永久綿延,不以個(gè)體死亡為界限。在這一思維框架下,在個(gè)體死亡后,通過一系列的儀式,靈魂將離開身體,進(jìn)入祖先的世界。在那個(gè)遠(yuǎn)離了生者的日常生活的所在,祖先繼續(xù)存在著,且能吃能喝,有喜怒哀樂。與此同時(shí),逝者將失去其生前個(gè)體的身份,獲得一個(gè)死后的名字,被刻在牌位上,而牌位則被放置在家庭祭臺(tái)上,代表了逝者與家庭之間的連續(xù)性。祖先的世界與生者的世界并不是隔絕的,祖先可以在紀(jì)念儀式等情境下返回和參與家人的日常生活。從個(gè)體生命到祖先的轉(zhuǎn)化,與個(gè)體生前的身份和成就無關(guān),其條件僅在于家人的關(guān)切和紀(jì)念。舉辦喪禮,讓逝者成為祖先,并予以后續(xù)的祭祀,這是作為家人的責(zé)任。尊敬和祭祀祖先,家人可以獲得祖先的蔭庇,這是一種良性的互惠的關(guān)系;反之,逝者不得安寧并將給生者帶來禍害。盡管(受現(xiàn)代化影響)許多日本人聲稱自己是唯物主義者,但是在返回故鄉(xiāng)和家庭時(shí),他們依然會(huì)參與祭祖儀式。在日本,事實(shí)就是“沒有人談?wù)撟嫦龋蛔嫦染驮谀抢铮瑹o需置評(píng)”[3]211-226。與對(duì)祖先的尊敬之心相關(guān)聯(lián),死亡的認(rèn)定也被認(rèn)為首先應(yīng)該是家庭的事情(盡管死亡的認(rèn)定必然主要地基于醫(yī)學(xué)事實(shí))。
另外,受到佛教的影響,許多日本人所接受的死亡判斷標(biāo)準(zhǔn)是溫暖的身體變涼和僵硬。對(duì)于家人來說,如果患者在呼吸機(jī)的支持下有規(guī)律地呼吸著,氣色不錯(cuò),身體溫暖,傷口能流血,且能排尿與排便,那么,無論是否還有意識(shí),他/她依然與家人一起經(jīng)歷著有意義的生活,需要被給予情感關(guān)注,這被認(rèn)為是家庭的責(zé)任[3]267。洛克還發(fā)現(xiàn):不同于北美,在日本,有許多家庭在期待奇跡(腦死亡患者能蘇醒過來)。在這一情境下,(即使在《器官移植法》通過之后)日本的醫(yī)護(hù)人員也會(huì)自覺謹(jǐn)慎地保持作為家庭的“外人”的身份,絕不會(huì)主動(dòng)(或提議)撤銷腦死亡患者的醫(yī)療設(shè)備,而是將死亡認(rèn)定的權(quán)限充分留給家庭[3]272。
四、身體的商品化
器官移植的概念,暗示了人的身體及器官可以被商品化(commodification)的意涵。商品化是馬克思提出的一個(gè)概念,所謂身體的商品化,是指身體組織或器官(在法律上)可以被分割和轉(zhuǎn)讓,從而進(jìn)入交換的系統(tǒng)(盡管可以不涉及金錢支付)[3]9。在歐洲,身體商品化的可以追溯至中世紀(jì)基督教的一些價(jià)值與實(shí)踐。在耶穌復(fù)活的傳說中,身體就被賦予了可以起死回生的特殊含義。在中世紀(jì)的基督教信仰中,圣人的遺體被認(rèn)為包含了生命與力量,具有神秘的治療作用,因而像其他商品一樣被買賣、盜竊、贈(zèng)予和交換。后來,普通死者的遺體亦被安葬在教堂院子里,這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普通人對(duì)死者遺體的恐懼[3]292-293。
另外,在中世紀(jì),教堂與對(duì)醫(yī)學(xué)解剖的著迷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lián)系,這導(dǎo)向了歐洲醫(yī)學(xué)中解剖實(shí)踐的興盛。在14世紀(jì),一些大學(xué)里出現(xiàn)了以教學(xué)為目的的解剖實(shí)踐,解剖的場(chǎng)所也經(jīng)歷了從教堂到劇場(chǎng)的轉(zhuǎn)變,因而具有了景觀的性質(zhì)。隨著解剖成為醫(yī)學(xué)知識(shí)的關(guān)鍵來源,尸體獲得了在醫(yī)學(xué)進(jìn)步事業(yè)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尸體供應(yīng)的短缺,導(dǎo)致了其作為商品的非法交易,在18世紀(jì)早期尸體甚至具有了準(zhǔn)財(cái)產(chǎn)的各種特質(zhì),可以明碼標(biāo)價(jià)、買賣和被私人所有。然而,醫(yī)學(xué)解剖的需求與家屬想要體面安葬死者遺體的愿望之間存在著沖突。為了協(xié)調(diào)這一對(duì)矛盾,英國于1831年出臺(tái)了《解剖法》,這一法律的要旨后來被英聯(lián)邦國家和美國所繼承。英國功利主義哲學(xué)家邊沁在1832年去世后,讓其醫(yī)生好友在一個(gè)露天劇場(chǎng)面向公眾公開解剖,以此鼓勵(lì)公眾捐獻(xiàn)遺體用于醫(yī)學(xué)事業(yè)。在19世紀(jì)末的歐洲,公眾不再公開反對(duì)為了醫(yī)學(xué)目的的遺體解剖行為。在二戰(zhàn)之后,隨著醫(yī)學(xué)研究日益受到國家與公眾的重視,為了醫(yī)學(xué)的目的志愿捐獻(xiàn)遺體的比例出現(xiàn)了大幅上升。洛克認(rèn)為:正是因?yàn)槲鞣缴鐣?huì)在過去數(shù)百乃至上千年的歷史中已經(jīng)消化了身體商品化可能帶來的歧義,所以,在北美和歐洲大部分國家和地區(qū),人們相對(duì)容易地接受了腦死亡與器官移植[3]298-306。
然而,在日本,身體商品化的歷史卻非常短暫。一方面,東亞的醫(yī)學(xué)傳統(tǒng)強(qiáng)調(diào)的是身體系統(tǒng)之間的關(guān)系,因而對(duì)于解剖沒有興趣。17世紀(jì)在接觸歐洲醫(yī)學(xué)之后,日本的醫(yī)生才開始參與解剖,直到19世紀(jì)后半葉解剖才成為醫(yī)學(xué)院的常規(guī)化活動(dòng)。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對(duì)祖先的尊敬之心深深地影響了日本人關(guān)于身體的觀念。對(duì)許多日本人而言,弄臟和擾動(dòng)逝者遺體,是對(duì)逝者的不尊敬,那么逝者的靈魂將會(huì)不安而為害作亂,從而給(沒有盡責(zé)的)家人帶來危害。與此相關(guān),如何處置個(gè)人的身體(無論生前或死后)也并不完全由個(gè)人自主決定,而是家庭集體決定。在20世紀(jì)70—80年代,侵華戰(zhàn)爭(zhēng)期間731部隊(duì)的暴行以及戰(zhàn)后日本醫(yī)院人體試驗(yàn)的違規(guī)行為被媒體大量報(bào)道出來,這強(qiáng)化了日本公眾對(duì)醫(yī)學(xué)研究動(dòng)機(jī)的質(zhì)疑以及不愿意(在器官移植層面)與醫(yī)學(xué)界合作的情緒[3]306-309。
五、關(guān)于生命的禮物
在關(guān)于器官捐獻(xiàn)的科普宣傳話語中,“生命的禮物”是一個(gè)關(guān)鍵的暗喻。禮物是由法國人類學(xué)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莫斯(Marcel Mauss)提出的一個(gè)經(jīng)典概念。莫斯認(rèn)為:在前現(xiàn)代社會(huì)中,所有禮物饋贈(zèng)都伴隨著互惠的期待,因?yàn)樵谒统龆Y物的同時(shí),主人也送出了自己的一部分(即所謂的“禮物之靈”),所以必須以同樣的方式回贈(zèng)。通過禮物交換,人際之間建立起了終生的承諾,而后者又是社會(huì)機(jī)制與階序結(jié)構(gòu)得以建立的基礎(chǔ)[8]155-184。借用莫斯的術(shù)語,英國社會(huì)學(xué)家蒂特馬斯(Richard Titmuss)把自愿無償獻(xiàn)血看作為一種特殊的禮物,即“生命的禮物”。但是,不同于經(jīng)典的禮物,“生命的禮物”發(fā)生于彼此匿名的陌生人之間,且沒有回贈(zèng)的義務(wù)。那么,為什么將“生命的禮物”贈(zèng)送給陌生人?換言之,無償獻(xiàn)血制度設(shè)計(jì)的合理性何在?蒂特馬斯的回答是:在開放的社會(huì)環(huán)境中,對(duì)陌生人的慷慨是基于利他主義的,這是“構(gòu)成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的紐帶和社會(huì)整合的源泉”[9]。
洛克也指出:在北美,“生命的禮物”所表征的器官捐獻(xiàn)不同于莫斯所謂的禮物饋贈(zèng)。在器官捐獻(xiàn)的情境中,互惠是缺失的。對(duì)于接受器官移植的個(gè)體而言,這當(dāng)然是莫大的恩惠(否則他們只能等死)。但是,對(duì)于填寫捐獻(xiàn)卡的個(gè)體而言,在器官獲取的時(shí)刻,他們已經(jīng)無意識(shí)了,回饋則沒有任何意義。對(duì)于捐獻(xiàn)者的家屬而言,他們往往是在面臨著突如其來的喪親之痛的壓力之下,做出無私的捐獻(xiàn)決策,最后僅能得到一封由協(xié)調(diào)機(jī)構(gòu)轉(zhuǎn)交的匿名感謝信。因而洛克認(rèn)為:在北美,器官捐獻(xiàn)是無私的,充滿了對(duì)陌生他者的慷慨,是基于利他主義的慈善捐獻(xiàn)。這一慈善捐獻(xiàn)背后的假設(shè)是:盡管捐獻(xiàn)者及其家屬無法獲得直接的回饋,但是如果他的親屬未來需要器官移植,那么會(huì)有另外一個(gè)陌生的他者會(huì)愿意捐獻(xiàn)。事實(shí)上,利他主義是社會(huì)學(xué)的鼻祖孔德創(chuàng)造的概念,它假設(shè)服務(wù)他人而不期待任何直接的回報(bào),那么最后整個(gè)社會(huì)將受益。面對(duì)19世紀(jì)末城市化的進(jìn)程對(duì)原有社會(huì)結(jié)構(gòu)的巨大沖擊,孔德提倡利他主義以重建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洛克繼而指出利他主義與基于互惠的禮物饋贈(zèng)的差別在于:后者直接指向的是個(gè)體間關(guān)系的建立,而前者則直接指向一種總體的伙伴關(guān)系的建立,且與基督教的美德是兼容的。另外,洛克還指出:盡管“生命的禮物”這一暗喻的使用存在限制,但是“禮物”暗含了如下意涵,即個(gè)體擁有自主的權(quán)利以決定如何處置自己的(身體)財(cái)產(chǎn),這與北美占支配地位的意識(shí)形態(tài)是相合的[3]316-319。
然而,“生命的禮物”這一暗喻則很難在日本的文化情境中扎根。在當(dāng)代日本的日常生活中,對(duì)于維持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而言,莫斯所謂的基于互惠原則的“禮物經(jīng)濟(jì)”依然非常重要。在家庭和社會(huì)生活中,正式的“禮物經(jīng)濟(jì)”界定了互惠與互助義務(wù)關(guān)系的邊界,陌生他者則被排除在外。對(duì)陌生他者的饋贈(zèng)與慷慨也很難被接受,這也部分地抑制了日本人將腦死亡親屬的器官捐獻(xiàn)給陌生人的意愿。洛克還看到:一些關(guān)于器官捐獻(xiàn)的日語廣告使用了“生命的接力棒”、“愛的呈獻(xiàn)”等詞匯(避免“生命的禮物”的直譯),而另外一些廣告語則化用了佛教減少他人痛苦的教義,這些都體現(xiàn)了將器官捐獻(xiàn)從基于互惠的“禮物經(jīng)濟(jì)”的情境中抽離出來的意圖。借用一位日本醫(yī)生的話,洛克得出結(jié)論:器官捐獻(xiàn)更“適合”于基督教的文化氣質(zhì),而不是作為佛教、儒家和神道教融合體的日本文化氣質(zhì)[3]328-330。
六、總結(jié)與討論
“像他人看我們一樣審視自身,能給我們十分的啟發(fā)……思想的宏大卻能使我們把自身列于他人之中來反省其身”[10]。基于人類學(xué)的文化相對(duì)論的原則,將日本與北美“平等”地作為世界眾多個(gè)案中一個(gè)案例(而不是以其中之一作為“進(jìn)步”/“正常”的標(biāo)尺來衡量另一者),加以并置和進(jìn)行跨文化的比較,這使得洛克能夠更清楚地看到日本與北美兩地分別發(fā)生了什么。
20世紀(jì)中期,呼吸機(jī)、重癥醫(yī)療和器官移植等醫(yī)療技術(shù)的發(fā)展,重新擾動(dòng)了人類社會(huì)已有的(相對(duì)穩(wěn)定的)生死邊界,“腦死亡”的概念被“發(fā)明”出來以協(xié)調(diào)其中的生命倫理矛盾,從而為推進(jìn)器官移植的常規(guī)化與制度化開辟空間。但是,腦死亡與器官移植的議題在北美和日本引起了完全不同的公眾反應(yīng)。通過從關(guān)于生命與死亡的本體論、身體的商品化、“生命的禮物”的暗喻等層面的跨文化的比較,洛克指出:受到其傳統(tǒng)與文化的限制,大多數(shù)日本人不愿意接受腦死亡和器官移植,然而,同樣地,正是由于其傳統(tǒng)和文化的基礎(chǔ),大多數(shù)北美人很容易地接受了腦死亡和器官移植。
基于日本與北美兩地的并置比較,洛克挑戰(zhàn)了一種主流的關(guān)于死亡的“理所當(dāng)然”和“確定無疑”的認(rèn)識(shí)—即死亡被視作為與意識(shí)形態(tài)無關(guān)且清晰明了的生物學(xué)事件。洛克繼而指出:盡管醫(yī)學(xué)在死亡的界定這一任務(wù)中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但是死亡并不只是一個(gè)不證自明的醫(yī)學(xué)現(xiàn)象,“生命與死亡的邊界是社會(huì)和文化建構(gòu)的,是多元的和富于彈性的,可以經(jīng)歷爭(zhēng)論而得到重新闡釋”[3]11。洛克的研究也潛在地質(zhì)疑了主流的生命倫理學(xué)(至少在討論腦死亡與器官移植的情境中)的一些基本假設(shè)。在主流的生命倫理學(xué)的基本原則中,人格(personhood)、自主性(autonomy)等核心概念常常被視作為獨(dú)立于文化情境的、普世的存在[11]。事實(shí)并非如此,洛克的民族志材料證明了:受到自然與文化二元論影響的北美人將人格置于大腦中,但是受到神道教、佛教和儒學(xué)混合影響的日本人的人格是家族世系的一部分,在“內(nèi)心”中,甚至與物的靈魂無異。北美人強(qiáng)調(diào)個(gè)體自主處理自己身體的權(quán)利,但是日本人的身體所有權(quán)并非僅限于個(gè)體,因而處理身體的自主權(quán)限屬于作為集體的家庭。而這些跨文化比較視野下的發(fā)現(xiàn),對(duì)于理解不同社會(huì)文化情境下的生命倫理差異,提供了深刻的洞見。
基于腦死亡與器官移植爭(zhēng)論中所積攢的經(jīng)驗(yàn),日本后來相對(duì)成功地形成了關(guān)于人類胚胎之倫理地位的具有本土特色的立場(chǎng)—即認(rèn)為人類胚胎既不是人(person),也不是物,而是值得尊敬和善待的“人類生命的萌芽”,而不是照搬西方社會(huì)關(guān)于人類生命始于孕育之時(shí)的生命倫理觀。僅在器官移植的條件下認(rèn)可腦死亡以及將胚胎視為“人類生命的萌芽”,這些面向現(xiàn)實(shí)的生命倫理問題的日本解決方案,可以視作為日本對(duì)亞洲乃至世界的生命倫理學(xué)的貢獻(xiàn)[1]。
當(dāng)下中國的生命倫理學(xué)也背負(fù)著同樣的歷史使命—即如何“在中國文化所蘊(yùn)含的倫理思想中探尋適應(yīng)科學(xué)研究及技術(shù)應(yīng)用的指導(dǎo)原則,一方面在全球坐標(biāo)下拓展學(xué)術(shù)新領(lǐng)域、回答中國問題,另一方面在國際倫理規(guī)制方面貢獻(xiàn)中國思想和智慧”[12]。面對(duì)這一使命,一向以跨文化比較和文化批評(píng)見長(zhǎng)的人類學(xué),應(yīng)該而且有能力扮演重要的角色,通過扎實(shí)的田野調(diào)查和濃厚的民族志描述,為理解和化解中國情境下的生命倫理問題提供重要的洞見與智慧[13]。
致謝:本文為兩位作者在2018—2019年秋季學(xué)年參加由北京大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系邱澤奇教授開設(shè)的“技術(shù)應(yīng)用與組織變遷”研討班時(shí)的讀書報(bào)告修改而成。感謝邱澤奇、周航、譚威等諸位師友在研討班上所給予的思想碰撞與啟發(fā)。本文文責(zé)自負(f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