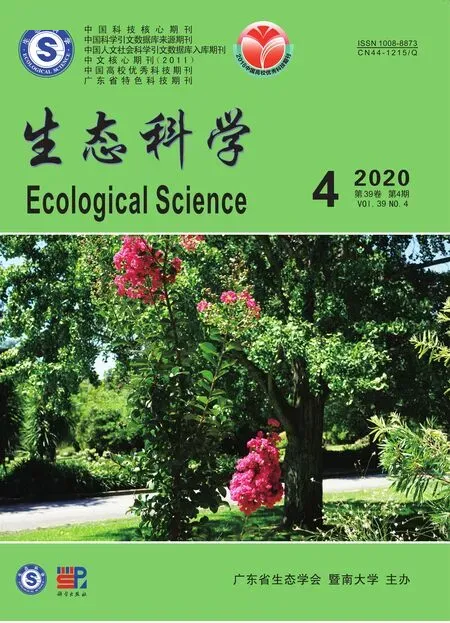青海湖流域植被碳利用效率時空動態研究
蘭垚, 曹生奎, *, 曹廣超, 李曉東, 楊羽帆, 雷義珍
青海湖流域植被碳利用效率時空動態研究
蘭垚1, 2, 3, 曹生奎1, 2, 3, *, 曹廣超2, 3, 李曉東4, 楊羽帆1, 2, 雷義珍1, 2, 3
1.青海師范大學 地理科學學院,西寧 810008 2. 青海師范大學 青海省自然地理與環境過程重點實驗室,西寧 810008 3.青海省人民政府-北京師范大學 高原科學與可持續發展研究院,西寧 810008 4. 青海省氣象科學研究所,西寧 810001
植被碳利用效率(CUE)是度量生態系統植被固碳能力和效率的標尺, 對評估生態系統碳儲量和揭示碳平衡機理具有重要意義。以青海湖流域為研究對象, 利用MOD17A2H數據估算了2000—2018年青海湖流域植被CUE, 揭示了植被CUE的動態變化特征, 并分析其影響因子。得到如下結果: (1)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年內變化表現為從3月開始逐漸增加, 6、7月達到最大, 然后減小; 年均植被CUE為0.58, 其值在0.55—0.63之間變化且呈略微下降趨勢, 線性遞減率為0.01 (10 a)–1; (2)青海湖流域內植被CUE呈現以青海湖為中心“高—低—高”的環帶狀空間分布特征, 其值在0.54—0.76之間變化(除水域之外), 且平均值為0.58; (3)青海湖流域植被CUE主要受氣溫和降水影響, 氣溫對植被CUE的影響較降水明顯, 隨氣溫升高和降水增加, 植被CUE呈減小趨勢。研究結果可為明確該區碳循環過程中的源/匯問題提供數據支撐, 并為高寒內陸地區植被CUE的研究提供方法借鑒, 同時對理解全球變化和預測生態系統對全球變化的響應具有重要意義。
MODIS; 青海湖流域; 植被; 碳利用效率; 時空變化
0 引言
生態系統植被碳利用效率(carbon use efficiency, CUE)作為植被凈初級生產力(net primary production, NPP)與總初級生產力(gross primary production, GPP)的比率[1], 其值大小代表植被固定大氣二氧化碳(CO2)的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態系統植被的固碳潛力和對碳同化能力的強弱, 是決定陸地生態系統碳儲量的關鍵性因子[2-5]。植被CUE也是度量生態系統植被固碳能力和效率的標尺, 植被CUE越高表明生態系統單位固碳的生長轉移越高, 生態系統固碳潛力越大[6]。研究和量化生態系統植被CUE可為確定生態系統碳源/匯提供數據支撐, 并對全球變化背景下生態系統響應的研究有重要意義[7-8]。
近年來, 生態系統植被CUE的研究受到國內外諸多碳循環和氣候變化等學者的關注, 并開展了大量關于陸地生態系統植被CUE的研究工作[9-12], 但是, 目前對陸地生態系統植被CUE是否為恒定值尚存在較大爭議。一種觀點認為植被呼吸與GPP成線性同步變化, 且與光合作用同化的含糖量有關, 植被CUE為恒定值[13-14]。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的驅動過程受光合有效輻射、溫度和降水等環境因子和物種類型的控制,植被CUE并非恒定值[2,6]。例如, Delucia[8]等通過生物計量法和模型估算法對森林CUE研究表明, 森林CUE的值在0.23—0.83之間波動。目前, 大多數有關植被CUE的研究是利用模型和渦度相關系統測量等方法所進行的, 且以森林、草地等單一的生態系統為主[15,16], 以綜合性的生態系統為單位的研究較少, 而關于植被CUE空間變化特征也鮮有報道。據此, 筆者認為造成上述觀點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對象的單一, 而生態系統植被 CUE的研究更需要通過多種生態系統尺度下的對比性研究才能得到較為可靠的結論。
青藏高原作為中國面積最大、世界海拔最高的高原, 是全球氣候變化的敏感區和感應器, 也是維系國內乃至全球生態平衡的重要屏障[17]。青海湖位于青藏高原東北部, 是中國最大的斷層陷落型內陸咸水湖[18], 因地處青藏高原高寒區、西北干旱區和東部季風區的交界處, 使得青海湖成為了維系青藏高原東北部生態安全的重要水體[19]。青海湖流域作為青藏高原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區域乃至亞洲都具有重要的生態地位。故此, 研究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對于區域乃至全球陸地生態系統碳平衡都有重要意義。
本文利用MODIS影像, 分析青海湖流域植被CUE的時空變化特征, 探究青海湖流域植被CUE是否為恒定值。所得結論可為明確該區碳循環過程中的源/匯問題提供數據支撐, 并對高寒內陸地區植被CUE研究提供方法借鑒, 同時對理解全球變化和預測生態系統對全球變化的響應具有重要意義。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青海湖流域位于青藏高原東北部(36°15′— 38°20′ N, 97°50′—101°20′ E), 是一個四面環山的內陸盆地, 流域內西北高而東南低, 海拔在3169— 5268 m之間, 總面積約2.96×104km2[19]。青海湖流域屬于典型的高原半干旱高寒氣候, 流域內干旱少雨, 風力強勁且蒸發量大, 晝夜溫差大, 生長季短, 非生長季長[20], 季節性凍土廣泛發育。流域內多年降雨量在290—580 mm左右, 多年平均降雨量為386 mm, 且主要集中在生長季; 流域內生長季主要以東南風為主, 非生長季主要以西風為主, 年均潛在蒸發量在839—912 mm之間; 青海湖流域年均氣溫在-1.1—4.0 ℃之間, 無霜期約110 d左右[21-22]。青海湖流域水系主要由布哈河、沙柳河(伊克烏蘭河)、甘子河、倒淌河等河流和青海湖構成。研究區植被類型主要包括灌叢、草原、沙生植被、鹽生植被、沼澤草甸植被、高山流石植被等[23]。

圖1 青海湖流域位置
Figure 1 Location of the Qinghai Lake Basin
1.2 數據與方法
1.2.1 數據來源
本研究運用了MODIS產品中的2000—2018 年的GPP和NPP數據, MOD17A2H遙感產品來自于NASA網站(http://modis.gsfc.nasa.gov/), 該產品可提供連續的全球監測初級生產力數據。MOD17A2H數據的時間分辨率和空間分辨率分別是8 d和500 m, 且該數據已經過去云、輻射校正、大氣校正和幾何校正等步驟。利用ArcGIS 10.2軟件和ENVI 5.3軟件對MODIS數據進行處理, 其中包括, 投影轉換、拼接、裁剪、按照元數據文件指示去除異常值、轉換比例因子等操作, 以恢復原始GPP和NPP的值。本研究所使用的增強型植被指數(enhanced vegetation index, EVI)來自MODIS數據產品的MOD13Q1數據, 其時間分辨率和空間分辨率分別是16 d和250 m, 數據格式為HDF, 該產品已經過大氣校正、幾何校正和去云等處理, 獲取數據后進行投影轉換和最大值合成(MVC), 最后利用研究區矢量邊界裁剪后即可應用。
1.2.2 CUE計算方法
CUE定義為生態系統植被凈初級生產力與總初級生產力的比值, 則其表達式為[24-25]:



式中:代表生態系統植被碳利用效率;為植被凈初級生產力(g·m-2);為植被總初級生產力(g·m-2);R為植被自養呼吸(g·m-2)。
1.2.3 CUE年際變化率計算
本文基于一元線性回歸分析方法來模擬2000— 2018年青海湖流域生態系統植被CUE的時空變化趨勢。計算公式如下[26]:

式中:為植被的趨勢斜率;為時間序列長度, 即2000—2018 年共計19 年;為1—19 年的序列號;CUE為第年的值。> 0, 表示在19年間的趨勢為增長, 反之則為減少。
2 結果
2.1 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年內變化特征
近19年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年內各月均值變化顯示(表1), 植被CUE年內變化明顯。近19年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各月平均值從3月開始增加, 6月和7月達到最大值0.58, 而后開始下降; 11月到來年2月NPP接近于0, 故此判斷其CUE接近于0。植被在不同生長階段的CUE空間分布特征顯示(圖2), 5月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在0.39—0.8之間變化(除水域之外), 且植被CUE值在東部偏高, 西部較低, 最高值出現在青海湖東北岸(圖2a); 8月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在0.53—0.78之間變化(除水域之外), 植被CUE值在西部邊界區偏高, 青海湖北岸中部和西岸中部較低, 最高值出現在青海湖東北岸和西北邊界地區(圖2b); 9月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在0.60—0.79之間變化(除水域之外), 植被CUE在青海湖西岸的中部地區較8月有明顯降低的趨勢(圖2c); 10月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在0.34—0.80之間變化(除水域之外), 青海湖流域植被CUE由東南向西北減小(圖2d)。5月和10月青海湖流域植被CUE總體由東南向西北逐漸遞減, 最高值區域分布在青海湖北岸附近。8月和9月植被CUE依然以青海湖為中心, 呈“高—低—高”的環帶狀分布。總體上, 青海湖環湖地區為植被CUE最大值分布區域, 青海湖流域中部地區在生長季初期和末期CUE值偏高, 生長旺盛期較低, 青海湖邊界地區與中部地區相反(圖2)。
2.2 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年際變化特征
2000—2018年青海湖流域植被CUE的年際變化趨勢顯示(圖3), 近19年青海湖流域植被CUE整體呈略微下降趨勢, 線性遞減率為0.01·10–1a。青海湖流域年均植被CUE在0.55—0.63之間變化, 平均值為0.58, 波動幅度較小, 最小值出現在2018年, 最大值出現在2009年。青海湖流域典型年份植被CUE結果顯示(圖4), 2000年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在0.54—0.8之間變化(除水域之外)(圖4a), 最小值區域出現在青海湖北岸的中部地區; 2009年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在0.54—0.8之間變化(除水域之外), 流域大部分地區植被CUE值高于2000年和2018年(圖4b); 2018年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在0.42—0.80之間變化(除水域之外), 流域大部分地區植被CUE值低于2000年和2009年(圖4c)。這3年的最小值區域都出現在青海湖北岸的中部地區, 最大值出現在流域西北邊界處和青海湖東北岸, 2009年整體值偏大, 2018年最大值出現在青海湖東北岸小部分區域。在青海湖流域中部地區(青海湖以西), 2009年值最大, 2000年次之, 2018年最小, 由此可見, 2009年和2018年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并非異常值。

表1 青海湖流域不同月份植被CUE均值變化

圖2 2000—2018年青海湖流域典型月份的CUE空間變化
Figure 2 Spatial variation of CUE valuein typical month in Qinghai Lake Basin during 2000-2018
2.3 青海湖流域植被CUE空間變化趨勢
近19青海湖流域植被年均CUE的空間分布顯示(圖5), 青海湖流域內植被CUE在0.54—0.76之間變化(除水域之外), 且流域內平均值為0.58, 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分布呈現以青海湖為中心的“高—低—高”環帶狀分布特征, 從東南向西北環帶范圍擴大。在青海湖環湖地區出現了第一條環帶狀“高”值區, 且青海湖北岸的高值區大于南岸, 這一高值區主要以農田和干旱草原為主, 其值大約在0.70左右。在青海湖流域中部以灌叢和高寒草甸生態系統為主的地區形成了“低”值區, 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四周的沙柳河、哈爾蓋河、甘子河、布哈河、黑馬河中游一帶, 其值在0.59左右。最后“高”值區, 出現在青海湖流域的邊界地區, 其中最大區域出現在青海湖流域的西北部, 此高值區主要以高山流石植被為主, 其值大約在0.70左右。由于環境因子隨時間的變化存在差異, 植被CUE的年際變化在空間上也存在差異(圖6), 變化趨勢(SLOPE值)范圍在-0.02—0.03之間, 將變化趨勢分為減少(< 0)、不變(≈ 0)和增加(> 0)3部分。青海湖流域有81.02 %的區域為植被CUE減少區域, 有15.17 %的區域為植被CUE不變區域, 其中青海湖湖面占14.76 %, 即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只有0.41 %的區域保持不變, 只有3.81 %的區域為植被CUE增加區域, 而其中不變的區域主要是青海湖東北岸, 增加的區域零星散布在青海湖東部、北部和西部。

圖3 2000—2018年青海湖流域CUE動態變化
Figure 3 Dynamics of annual CUE value in Qinghai Lake Basin during 2000-2018

圖4 2000—2018年青海湖流域典型年份CUE空間變化
Figure 4 Spatial variation of CUE valuein typical year in Qinghai Lake Basin during 2000-2018

圖5 2000-2018年青海湖流域CUE年均值空間分布
Figure 5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UE value in the Qinghai Lake Basin

圖6 2000-2018年青海湖流域CUE空間變化趨勢
Figure 6 Spatial variation trend of CUE value in Qinghai Lake Basin during 2000-2018
3 討論
青海湖流域植被CUE的時空分布是受植被類型、氣溫、降水、海拔和土地營養和管理措施等諸多因素綜合影響的結果。青海湖流域內植被CUE從3月開始增大, 6、7月達到最大值, 隨后開始減小(表1)。5月和10月植被CUE呈現由東南向西北遞減的趨勢(圖2a、d), 這主要是由于海拔由低到高呈環帶狀分布, 自東南向西北升高, 西北部生長季較東部時間短, 使得5月和10月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呈現由東南向西北遞減的規律。6月到9月, 青海湖流域植被處于生長季內, 故此植被CUE變化較為穩定(圖7b、c)。
青海湖流域GPP、NPP與氣溫和降水存在正相關關系(圖7), GPP、NPP與溫度為極顯著相關(圖7a、b),與降水為顯著相關(圖7c、d)。Lieth等[27]研究發現, 干冷生態系統植被NPP隨年降水量和年均氣溫的升高呈線性增加。閆敏等[28]對黑河上游地區總初級生產力研究中發現, 高寒草甸地區植被GPP與溫度和降水呈正相關關系。溫度、降水與GPP的擬合斜率遠大于與NPP的擬合斜率(圖7), 當溫度和降水增加量相同時, GPP的增加量大于NPP的增加量, 從而間接導致植被CUE降低。溫度降低時, 植被維持自身組織所需的能量減少[29], Ra降低, 植被CUE增大。降水較多時, 云量較多, 土壤出現缺氧狀態, 有機質的分解速率下降, 從而導致了CUE減小[30]。溫度和降水影響生態系統植被光合作用和自養呼吸, 間接影響植被CUE的變化。近19年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呈現略微下降趨勢(圖3, 圖6), 這一研究與前人研究結果相吻合[1,12,31], 近19年平均氣溫升高使Ra增加, 導致植被CUE減小。2009年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出現最大值為0.63, 其原因主要是2009年的生長旺盛時期(7月和8月)平均氣溫(12.11 ℃)比近19年平均氣溫(13.01 ℃)低0.9 ℃, 低溫環境致使生態系統植被自養呼吸作用減弱, 使植被CUE增大(圖4b)。2018年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出現最小值為0.55, 其原因主要是2018年的生長旺盛時期(7月和8月)降水達到近19年的最大值127.88 mm, 降水較多時, 土壤出現缺氧狀態, 有機質的分解速率下降, 同時植被的光合作用效率下降, 使得植被CUE減小(圖4c)。

圖7 青海湖流域年均NPP、GPP與年均氣溫、年降水量以及VPD與CUE的關系
Figure 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nual NPP, GPP and annual temperature, precipitation, VPD and CUE in Qinghai Lake Basin
飽和水汽壓差(vapor pressure deficit, VPD)是指在一定溫度下, 飽和水氣壓和空氣之中實際水汽壓的差值, 是空氣干燥程度的一個指標, 其值大小可以反映空氣水分虧缺狀況, VPD還是葉片和大氣界面物質交換的驅動力, 對植物體的生理代謝有重要影響[32]。植物氣孔是植物體與外界大氣進行氣體交換的通道, 在光合作用過程中, CO2通過氣孔進入葉片, 參與植物的光合作用, 而VPD則是通過調節植被的氣孔來影響植被的光合和呼吸速率[33]。青海湖流域的植被CUE與VPD存在較顯著的負相關關系, 即植被CUE隨VPD的增加而減小(圖7f)。溫度和降水的正相關性混淆了植被CUE對于氣溫降水的相關性[29], 同時, 植被CUE受氮沉降、環境條件、光照強度等的綜合影響, 且各影響因子之間的相互關系, 更加混淆了植被CUE與影響因子的相關性。青海湖流域地處干旱區, 溫度較低, 多年平均VPD為0.32 KPa, 溫度增加, VPD開始增大(VPD < 0.5 KPa), 氣孔開放, 蒸騰作用加強而光合作用卻不受影響[34], 呼吸作用增加, 導致了高Ra/GPP和低植被CUE(1-Ra/GPP)。降水增加時, 植被葉片氣孔關閉, 阻礙了植被光合作用, 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呼吸作用, 同樣造就了高Ra/GPP和低植被CUE[35]。
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在0.54—0.76之間變化(除水域之外), 平均值為0.58。袁旻舒等[36]研究中國陸地生態系統總體植被CUE變化范圍在0.33—0.62之間, 且平均值保持在0.5左右, 變化幅度不大; Street[37]等對歐洲亞北極區植被CUE的研究結果表明, 矮灌叢生態系統植被CUE值在0.58—0.74之間。上述植被CUE研究與本文所得結果基本吻合。植被CUE不但受氣溫、降水的影響, 同時也受植被蓋度和植被自養呼吸的影響。增強型植被指數(enhanced vegetation index, EVI)是表征生態系統植被覆蓋狀況變化的一個重要指標, EVI比歸一化植被指數(NDVI)對植被變化的敏感性更強[38], EVI值越大表示植被覆蓋度越大。Chen等[39]研究認為EVI與生態系統GPP有正相關關系。安相等[15]研究認為EVI對生態系統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都有重要影響, 且植被生長狀況越好, 生態系統GPP越高, 但對NPP的影響不大。2000—2018年EVI與GPP和NPP的對比顯示(圖8), 青海湖流域EVI與GPP、NPP的變化趨勢一致, GPP和NPP隨EVI的增大而增加。GPP、NPP與EVI的相關分析表明, 青海湖流域GPP、NPP與EVI呈極顯著正相關關系(<0.01), 確定系數為R2=0.38和R2=0.42, 其擬合方程顯示, EVI的增大量相同時(y=1.268x-97.597, y=0.862x-62.785), GPP的增加量大于NPP的增加量, 從而間接導致植被CUE的值降低。
2000—2018年青海湖流域EVI和Ra平均值顯示(圖9), 青海湖流域EVI和Ra以青海湖為中心由東南向西北形成了“低—高—低”的環帶狀分布特征, 與植被CUE分布特征恰好相反(圖5)。Ra是植物為維持自身生存所消耗的同化物, 在一個生態系統中植物的自養呼吸大小決定了生態系統植被固碳能力的強弱。He等[29]在用不同方法估算全球CUE時發現, 植被CUE的主要差異取決于Ra方面, 而不在GPP方面。青海湖流域以青海湖為中心, 海拔由低到高呈環帶狀分布, 自東南向西北升高, 氣溫和降水以青海湖為中心呈現由暖到寒、由濕到干的環帶狀分布[40]。青海湖環湖地區主要以農田和草地為主, EVI和Ra值較小, 農田灌溉和施肥能引起植被根部呼吸的減少[41], 植被覆蓋度小則地上呼吸較少, 植被CUE較大(圖5), 研究表明農田生態系統、草地生態系統、森林生態系統植被CUE的平均值依次減小[42-43]。青海湖流域中部地區以灌叢和高寒草甸為主, EVI和Ra值較大, 溫度和降水充足, 植被生長茂盛, 自養呼吸消耗量較大, 導致植被CUE值較小(圖5)。青海湖流域邊緣地區主要以流石坡植被為主, 植被稀疏, 海拔較高, 隨海拔升高溫度和降水減少, 植被用于生存所耗費的能量較少[44-45], 植被固碳轉移效率更高[46], 植被CUE較大(圖5)。在適應干旱或寒冷環境時, 生態系統通常出現以短莖或稀疏覆蓋為特征的生命形式[13], 由此造就了稀疏植被生態系統(EVI和Ra較小)的植被CUE值較大。Zhang等[13]在基于MODIS數據的基礎上分析CUE變化時表明, 北溫帶地區茂盛植被地區的CUE比稀疏植被地區低, 與本研究結果相似。

圖8 青海湖流域年均NPP、GPP與EVI的關系
Figure 8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nnual NPP, GPP and EVI in Qinghai Lake Basin

圖9 2000—2018年青海湖流域EVI和Ra空間變化
Figure 9 Spatial variation of EVI andavalue in Qinghai Lake Basin during 2000-2018
4 結論
本文基于MODIS數據估算并分析青海湖流域2000—2018年間的植被CUE時空變化規律, 認為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并非恒定值。得出如下初步結論: (1)青海湖流域內植被CUE從3月開始增大, 6、7月達到最大值, 隨后開始減小。青海湖流域海拔由西北向東南遞減, 西北部生長季較東部時間短, 使得5月和10月青海湖流域植被CUE呈現由東南向西北遞減的規律。(2)溫度和降水增加量相同時, GPP的增加量大于NPP的增加量, 從而間接導致植被CUE的值降低。(3)青海湖流域EVI和Ra以青海湖為中心由東南向西北形成了“低—高—低”的環帶狀分布特征, 與CUE分布特征恰好相反。生態系統植被生長茂盛時, EVI和Ra增大, EVI對GPP影響大于對NPP的影響, 同時自養呼吸消耗量增大, 導致植被CUE值較小。
[1] CHAMBERS J Q, TRIBUZY E S, TOLEDO L C, et al. Respiration from a tropical forest ecosystem: partitioning of sources and low carbon use efficiency[J]. Ecological Applications, 2004(14): 72–88.
[2] RYAN M G, LAVIGNE M B, Gower S T. Annual carbon cost of autotrophic respiration in boreal forest ecosystems in relation to species and climate[J].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Atmospheres, 1997, 102(D24): 28871–28883.
[3] DILLAWAY D N, KRUGER E L. Trends in seedling growth and carbon-use efficiency vary among broadleaf tree species along a latitudinal transect in eastern North America[J]. Global Change Biology, 2014, 20(3): 908–922.
[4] ALLISONll S D, WALLENSTEIN M D, BRADFORD M A. Soil-carbon response to warming dependent on microbial physiology[J]. Nature Geoscience, 2010, (3): 336–340.
[5] MANZONI S, TAYLOR P, RICHTER A, et al. Environ-mental and stoichiometric controls on microbial carbon-use efficiency in soils[J]. New Phytologist, 2012, 196: 79–91.
[6] 朱萬澤. 森林碳利用效率研究進展[J]. 植物生態學報, 2013, 37(11): 1043–1058.
[7] LINDORTH A, GRELLE A, MOREN A S. Long-term measurements of boreal forest carbon balance reveal large temperature sensitivity[J]. Global Change Biology, 1998, 4(17): 443–450.
[8] DELUCIA E H, DRAKE J E, THOMAS R B, et al. Forest carbon use efficiency: Is respiration a constant fraction of gross primary production[J]. Global Change Biology, 2007, 13(6): 1157–1167.
[9] DEWAR R C, MEDLYN B E, MCMURTRIE R E. A mechanistic analysis of light and carbon use efficiencies[J]. Plant Cell and Environment, 1998, 21(6): 573–588.
[10] 陳光水, 楊玉盛, 高人, 等. 杉木林年齡序列地下碳分配變化[J]. 植物生態學報, 2008, 32( 6): 1285–1293.
[11] MALHI Y, ARAGAO L, METCALFE D B, et al.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carbon productivity, allocation and storage in three Amazonian forests[J]. Global Change Biology, 2009, 15(5): 1255–1274.
[12] KWONA Y, LARSEN C P S. Effects of forest type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forest carbon use efficiency assessed using MODIS and FIA data across the eastern USA[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mote Sensing, 2013, 34(23): 8425–8448.
[13] ZHANG Yangjian, XU Ming, CHEN Hua, et al. Global pattern of NPP to GPP ratio derived from MODIS data: effects of ecosystem typ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climate[J]. Glob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 2009, 18(3): 280–290.
[14] LEVY P E, CANNELL M G R, FRIEND A D. Modelling the impact of future changes in climate, CO2concentration and land use on natural ecosystems and the terrestrial carbon sink[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04, 14(1): 21–30.
[15] 安相, 陳云明, 唐亞坤. 東亞森林、草地碳利用效率及碳通量空間變化的影響因素分析[J]. 水土保持研究, 2017, 24(5): 80–92.
[16] PIAO Shilong, LUYSSAERT S, CIAIS P, et al. Forest annual carbon cost: a global-scale analysis of autotrophic respiration[J]. Ecology, 2010, 91, 652–661.
[17] 呂鑫, 王卷樂, 康海軍, 等. 基于MODIS NPP的2006-2015年三江源區產草量時空變化研究[J]. 自然資源學報, 2017, 32(11): 1857–1868.
[18] 翟俊, 侯鵬, 趙志平, 等. 青海湖流域景觀格局空間粒度效應分析[J]. 國土資源遙感, 2018, 3(3): 159–166.
[19] 曹生奎, 曹廣超, 陳克龍, 等. 青海湖高寒濕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動態[J]. 中國沙漠, 2014, 34(5): 1402–1409.
[20] 潘虹, 顧海敏, 史建橋, 等. 基于RS和GIS的青海湖流域植被覆蓋度變化與驅動因子研究[J]. 資源開發與市場, 2016, 32(7): 827–831.
[21] 蘇芬, 劉寶康, 張翠花, 等. 青海湖流域牧草物候期對氣候變化的響應[J]. 青海草業, 2018, 27(4): 12–18.
[22]肖雄, 李小雁, 吳華武, 等. 青海湖流域高寒草甸壤中流水分來源研究[J]. 水土保持學報, 2016, 30(2): 230–236.
[23] 喬凱, 郭偉. 青海湖流域植被的凈初級生產力估算[J]. 水土保持通報, 2016, 36(6): 204–209.
[24] 方精云, 柯金虎, 唐志堯, 等. 生物生產力的“4P”概念、估算及其相互關系[J]. 植物生態學報, 2001, 25(4): 414– 419.
[25] WARING R H, LANDSBERG J J, WILLIAMS M. Net primary production of forests: a constant fraction of gross primary production[J]. Tree physiology, 1998, 18(2): 129–134.
[26] 穆少杰, 李建龍, 周偉, 等. 2001-2010年內蒙古植被凈初級生產力的時空格局與氣候變化的關系[J]. 生態學報, 2013, 33(12): 3752–3764.
[27] LIETH H, WHITTAKER R H. Modeling the primary productivity of the world. Primary productivity of the biosphere[M].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Press, 1975(12): 237–263.
[28] 閆敏, 李增元, 田昕, 等. 黑河上游植被總初級生產力遙感估算及其對氣候變化的響應[J]. 植物生態學報, 2016, 40(1): 1–12.
[29] HE Yue, PIAO Shilong , LI Xiangyi, et al. Global patterns of vegetation carbon use efficiency and their climate drivers deduced from MODIS satellite data and process-based models[J]. Agricultural and Forest Meteorology, 2018, 256-257: 150–158.
[30] MATSON S P A .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 and Nutrient Cycling across a Mesic to Wet Precipitation Gradient in Hawaiian Montane Forest[J]. Oecologia, 2001, 128(3): 431–442.
[31] ZHANG Yangjian, YU Guirui, YANG Jian, et al. Climate-driven global changes in carbon use efficiency[J]. Global Ecology and Biogeography, 2014, 23(2): 144–155.
[32] 杜清潔, 宋小明, 柏萍, 等. 不同水汽壓差對番茄氣體交換參數和生長的影響及綜合評價[J]. 西北農業學報, 2020, 29(01): 66-74.
[33] 牛亞毅, 李玉強, 王旭洋, 等. 干旱年份沙質草地生態系統凈 CO2通量年變化特征[J]. 草業學報, 2018, 27(1): 215–221.
[34] 闞飛, 岳寧, 丁林凱, 等. 不同氣象條件下隴中玉米農田生態系統水分利用效率研究[J]. 灌溉排水學報, 2018, 37(10): 116–122.
[35] 陳小平. 科爾沁沙丘-草甸濕地水熱碳通量變化及響應機制研究[D]. 呼和浩特: 內蒙古農業大學, 2018.
[36] 袁旻舒, 李明旭, 程紅巖, 等. 基于CMIP5 模型結果的中國陸地生態系統未來碳利用效率變化趨勢分析[J]. 中國科學院學學報, 2017,34(4): 452–461.
[37] STREET L E, SUBKE J A, SOMMERKORN M, et al. The role of mosses in carbon uptake and partitioning in arctic vegetation[J]. New Phytologist, 2013, 199: 163–175.
[38] 楊怡, 吳世新, 莊慶威, 等. 2000—2018 年古爾班通古特沙漠 EVI 時空變化特征[J]. 干旱區研究.2019, 36(06): 1512–1520.
[39] CHEN Zhi, YU Guirui, GE Jianping, et al. Roles of climate, vegetation and soil in regulating the spatial variations in ecosystem carbon dioxide fluxes i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J]. PloS One, 2015, 10(4): 1–l4.
[40] 張濤, 曹廣超, 曹生奎, 等. 2000—2012年青海湖流域NPP時空分布特征[J]. 中國沙漠, 2015, 35(4): 1072– 1080.
[41] RYAN M G, HUBBARD R M, PONGRACIC S, et al. Foliage, fine root, woody tissue and stand respiration in Pinus radiata in relation to nitrogen status[J]. Tree Physiology, 1996, 16, 333–343.
[42] CHEN Zhi, YU Guirui, WANG Qiufeng. Ecosystem carbon use efficiency in China: Variation and influence factors[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8, (90): 316–323.
[43] MUHAMMAD K, NADIR A E, LARS R, et al. Spatio-temporal variations in climate, primary productivity and efficiency of water and carbon use of the land cover types in Sudan and Ethiopia[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8, (624): 790–806.
[44] RYAN M G, LINDER S, VOSE J M, et al. Dark respiration of pines[J]. Ecological bulletins, 1994, 43: 50–63.
[45] CANNEL M G R. Physiological basis of wood production: a review[J].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forest research, 1989, 4(1/4): 459–490.
[46] ENQUIST B J, KERKHOFF A J, STARK S C, et al. A general integrative model for scaling plant growth, carbon flux, and functional trait spectra[J]. Nature, 2007, 449, 218–222.
Temporal and spatial dynamics of vegetation carbon use efficiency in Qinghai Lake Basin
LAN Yao1, 2, 3, CAO Shengkui1 2, 3,*, CAO Guangchao2, 3, LI Xiaodong4, YANG Yufan1, 2, LEI Yizhen1, 2, 3
1. College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8, China 2. Qinghai Provincial Key Laboratory of Physical and Environmental Processes,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8, China 3. Academy of Plateau Science and Sustainability, People’s Government of Qinghai Province &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8, China 4. Qinghai Institute of Meteorological Science, Xining 810001, China
The carbon use efficiency (CUE) is a scale to measure the carbon sequestration capacity and efficiency of ecosystem veget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valuating the carbon storage and reveal the mechanism of carbon balance.This paper takes Qinghai Lake Basi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uses MOD17A2H to estimate the vegetation CUE from 2000 to 2018 and to reveal it characteristics of dynamic change and impact factor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vegetation CUE of annual variation was increasing from March and reaching the maximum in June and July then decreasing; and it was 0.58 of average annual, and it varied between 0.55 and 0.63 and slightly decreased, and the linear decline rate was 0.01/10a in Qinghai Lake Basin.(2) The CUE of vegeta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was the “high-low-high” ring-like shape centered, and it varied between 0.54 and 0.76 (except the waters) and the average was 0.58 in the Qinghai Lake Basin. (3) The CUE of vegetation was mainly affected by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and the effect of temperature was more obvious than precipitation. With the increase of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the CUE of vegetation decreased in Qinghai Lake Basin.The results of research can provide data support for clarifying the source/sink problem in the carbon cycle of the region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vegetation CUE in areas of alpine inl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ing global change and predicting the response of ecosystem to global change.
MODIS; Qinghai Lake Basin; vegetation; carbon use efficiency; spatial and temporal variations
10.14108/j.cnki.1008-8873.2020.04.020
蘭垚, 曹生奎, 曹廣超, 等. 青海湖流域植被碳利用效率時空動態研究[J]. 生態科學, 2020, 39(4): 156–166.
LAN Yao, CAO Shengkui, CAO Guangchao, et al. Temporal and spatial dynamics of vegetation carbon use efficiency in Qinghai Lake Basin[J]. Ecological Science, 2020, 39(4): 156–166.
Q148
A
1008-8873(2020)04-156-11
2019-11-25;
2019-12-31
青海省“135高層次人才培訓工程”; 青海省“高端創新人才千人計劃”項目(青人才字[2016] 11號); 青海省重點實驗室發展專項
蘭垚(1993—), 男, 漢族, 陜西岐山人, 碩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為生態水文及生態系統碳循環方面, E-mail: 1246522453 @qq.com
曹生奎, E-mail: caoshengku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