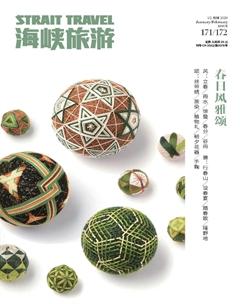古來(lái)春趣復(fù)幾許
郭鈺婷 張曉霏 鄭雯馨



春之雅趣,古來(lái)有之。翻閱那些記載各地節(jié)令風(fēng)俗的古籍,從字里行間都能想象出,古人是如何運(yùn)用各種季節(jié)性的風(fēng)物和熱鬧的活動(dòng)來(lái)迎接春、夏、秋、冬以及那些傳統(tǒng)節(jié)日的。即便是在同一個(gè)春天,各地也能用不盡相同的風(fēng)物、風(fēng)俗展示出他們對(duì)這個(gè)象征了新生的季節(jié)的多面感知。那些感性的、詩(shī)意的表達(dá)延續(xù)至今,便是一個(gè)個(gè)令今人無(wú)比羨慕與向往的風(fēng)雅生活的舊影。
三月三,古有上巳節(jié)。在初春時(shí)節(jié),青年男女相邀到江畔踏春暢游,用三月的桃花水濯足洗纓,當(dāng)中亦有“祓除歲積”的寓意。此外,還有一種“曲水流觴”的娛樂,即人們?cè)诎哆呉来巫拢枇魉悖瑢⒕票杏诤扇~,并從上游放下。所用酒杯被稱為“羽觴”,因其多為木制,兩側(cè)還有“雙耳”可方便舉起。當(dāng)酒杯輕盈浮在水上,并隨意漂流,停在何人面前,何人就要飲酒,因此樂趣無(wú)窮。
關(guān)于“曲水流觴”的由來(lái),有諸多說(shuō)法:一說(shuō)是“周公卜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shī)云:‘羽觴隨波流。”后世便沿襲此俗。漸漸地,“曲水流觴”從單純的飲酒發(fā)展成文人之間詩(shī)酒酬樂的一樁雅事。在山水環(huán)繞之地,既能感知萬(wàn)物復(fù)蘇、欣欣向榮之勢(shì),又有詩(shī)酒與宴樂,因此上巳節(jié)也從最初的祓禊消災(zāi)逐漸變?yōu)榕R水宴飲,成為古時(shí)春日里一種頗具風(fēng)雅的游玩活動(dòng)。
紙鳶即風(fēng)箏,最初是軍事上傳遞消息之用。因造型多為“鷂”及“鳶”等猛禽而得名。
之后漸漸演變?yōu)橐环N民間游戲,尤其在春日,孩童會(huì)相邀往郊外放紙鳶。一說(shuō)為“試春風(fēng)”,一說(shuō)為強(qiáng)身健體。古時(shí)的紙鳶均是竹骨紙糊,除了傳統(tǒng)的猛禽形象,還包括日月、星云、龍鳳、仙人及百烏在內(nèi)的多種造型。乘風(fēng)而上時(shí),系在紙鳶上的飄帶還會(huì)發(fā)出振振聲響。
放紙鳶還是一種具有競(jìng)技意味的游戲,又被叫做“斗鷂子”。即通過操縱手中的線,讓自己的紙鳶勾住其他的紙鳶,雙方一同收線,誰(shuí)能將別人的線絞斷,便為勝者。這當(dāng)中尤為考驗(yàn)個(gè)人的技巧,《紅樓夢(mèng)》中就描述了大觀園里的女孩們相互斗風(fēng)箏為樂的場(chǎng)景。有時(shí)人們還會(huì)特意將線裁斷,放飛紙鳶,希望其將一整個(gè)冬天的“郁氣”也一同帶走。
古人在春回大地之時(shí),也會(huì)舉行一些場(chǎng)面頗為“火熱”的戶外運(yùn)動(dòng),比如拔河戲。其同樣也是從軍事鍛煉逐漸演變成民間游戲的,最初被稱為“牽鉤”,因?yàn)槭怯靡粭l兩端系上很多小鉤的竹纜作為比賽工具,分為兩隊(duì)拉拔;后改為大麻繩,在中端掛上一張界牌,由裁判豎旗示意比賽開始。在喧囂的鑼鼓聲助威下,雙方都竭盡全力爭(zhēng)挽,直至將界牌拉入自己的區(qū)域,贏家會(huì)賞暖酒,輸家就要自飲冷水。
“春來(lái)百種戲,天意在宜秋。”盡管有在春天舉行的各種活動(dòng),多是為了祈求秋天大豐收。但對(duì)于主要在春季舉行的拔河戲是如何與農(nóng)業(yè)豐稔相掛鉤的,似乎沒有很明確的觀點(diǎn),不過這并不影響人們對(duì)這項(xiàng)活動(dòng)的熱衷。不只在民間,唐宋時(shí)代的宮廷也時(shí)常舉行隆重的拔河戲,娛神娛人,與民同樂。
古時(shí)民間迎春,少不了幾場(chǎng)熱鬧盛大的廟會(huì)和巡街。彼時(shí)街道兩旁掛滿春旗春幡,吹響號(hào)角,宣告盛會(huì)開始。商戶紛紛張燈結(jié)彩,裝飾門面,各行各業(yè)都用不同的形式來(lái)參與迎春盛會(huì),七十二行戶各自扮做舞隊(duì),有充當(dāng)春官、春吏的,也有作為歌女、歌童位列其中的;平頭百姓則手持花籃,擁簇左右,儀仗隊(duì)列則懸掛著五彩紙球。
“立春早,則芒神在土牛前;立春晚,則芒神在土牛后。”時(shí)人還會(huì)扮做芒神牽春牛,祈求春耕順利。農(nóng)戶用長(zhǎng)繩盡力將春牛拽住,春牛經(jīng)過家家戶戶,人們要投擲炒豆,意為“撒春”,期望春牛肥健,有利農(nóng)事。同行的鄉(xiāng)老、官吏、學(xué)子則手持春鞭,頭戴春花,為其慶賀。最后還要張春幛,書春賦、春詞,以詩(shī)詞歌賦贊頌春日,才算是圓滿完成了“春之盛會(huì)”。
古代以正月初七為人日,正好是立春,別致的梅花妝就誕生于這日。傳說(shuō)在南朝宋武帝時(shí)期,壽陽(yáng)公主在人日當(dāng)天臥于含章殿,檐下的梅花樹在風(fēng)中一吹,落下來(lái)一朵梅花,正好點(diǎn)在公主額上,形成一種格外別致的裝飾。宮女們覺得在額頭上點(diǎn)上梅花瓣更顯嬌俏,紛紛效仿,以紅點(diǎn)額,謂之“梅花妝”,久而久之這種妝就成了宮廷日妝。
最初的梅花妝取初春時(shí)開放的臘梅點(diǎn)額。但臘梅不是四季都有,于是古代女子使用很薄的金箔剪成花瓣型,貼在額頭或者面額上,顏色除了黃色,還有紅色、綠色,后來(lái)除了梅花形狀,還出現(xiàn)小魚、蝴蝶等靈動(dòng)可愛的動(dòng)物形狀。材質(zhì)也越來(lái)越多樣,紙片、玉片、干花片、魚麟片等都可以用來(lái)點(diǎn)梅花妝,最妙的是有人曾用蜻蜓翅膀點(diǎn)妝。宋代以后,女子漸漸不貼花鈿了,但后來(lái)只要形容艷妝或精致的妝容,就用“梅花妝”一詞。
“初七人日又立春,梅花點(diǎn)額顏色新。此身若在含章殿,疑是壽陽(yáng)宮里人。”在梅花盛放的立春時(shí)節(jié),效仿故人取落梅花瓣點(diǎn)妝,不失為一樁春日雅事。
春社是最古老的中國(guó)傳統(tǒng)民俗節(jié)日之一,人們?cè)诙露胀恋厣裆者@一天聚會(huì)酬神。春社源于人們對(duì)土地的崇拜,我國(guó)先民一直對(duì)土地保有崇敬和膜拜之情,由于“土地廣博,不可遍敬也;無(wú)故眾多,不可一一祭也。故封土立社而示有土尊。”
春社也分官社和民社,官社莊重肅穆,禮儀繁縟,民社則充滿生活氣息。在春社這一天,周圍鄰居會(huì)聚集在一起,在社樹下搭棚屋,設(shè)有專祠,宰殺牛羊、演奏音樂來(lái)祭祀社神,家家戶戶都會(huì)帶著酒前來(lái)祝禱。在祭祀結(jié)束后,鄰里鄉(xiāng)親會(huì)聚在一起飲酒狂歡。大家籌集用來(lái)籌辦盛會(huì)的錢,叫社錢;一起擊鼓祈求豐收,叫社鼓;喝了可以治聾(據(jù)說(shuō)春社當(dāng)天的酒可以治耳聾)的酒,叫社酒;用各種肉拌著飯一塊吃的,叫社飯。《春社出郊》一詩(shī)描繪了社日當(dāng)天的熱鬧歡愉:“千尋古櫟笑聲中,此日春風(fēng)屬社公。開眼已憐花壓帽,放懷聊喜酒治聾。攜刀割肉余風(fēng)在,卜瓦傳神俚俗同。聞?wù)f已栽桃李徑,隔溪遙認(rèn)淺深紅。”
郊游踏青自古以來(lái)是春天里的一大樂事,《論語(yǔ)·先進(jìn)》云:“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七八人,浴乎沂,風(fēng)乎舞雩,詠而歸。”表明在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人們就很喜歡結(jié)伴郊游賞春。最迫不及待出門踏青的當(dāng)屬漢代人,不待春意濃,正月初七“人日”就出門踏青了。唐代人民則喜歡從正月十五開始“探春”,他們會(huì)乘車跨馬到郊野中,支起簾帳設(shè)探春之宴,出游最熱鬧的還是在寒食、上巳、清明期間。有許多唐詩(shī)記錄了春游的美好,如詩(shī)人李華所做《春游吟》:“初春遍芳旬,千里靄盈矚。美人摘新英,步步玩新綠。”此后各朝代一直延續(xù)春游之風(fēng),宋代之后踏青則主要集中在清明節(jié),人們借著清明掃墓的時(shí)機(jī)踏青、聚會(huì),據(jù)《東京夢(mèng)華錄》所記載,時(shí)人“往往在芳樹之下或園固之間羅列杯盤,互相勸酬。”
秋千源于古人揪葦條(或藤條之類)蕩躍遷移的行為動(dòng)作,已流傳2000多年,其中最常見的是以植木為架,系上兩根繩子,繩子下端拴住一塊橫板,人坐于板上,像鐘擺一樣來(lái)回?cái)[蕩。據(jù)說(shuō)本來(lái)叫做“千秋”,后人誤傳為“秋千”。漢武帝時(shí)期為祈求千秋之壽,在宮中興盛秋千之樂,并賦予其美好的寓意。蕩秋千因此在宮廷、民間流行開來(lái),成為歷代最受女子喜愛的一項(xiàng)娛樂活動(dòng)。唐宋時(shí)期,每到寒食節(jié),宮中會(huì)競(jìng)相豎起許多秋千,供宮中妃嬪玩樂。唐詩(shī)宋詞里也有許多吟詠女子蕩秋千的詩(shī)詞,如南宋俞國(guó)寶《風(fēng)入松》里“紅杏香中蕭鼓,綠楊影里秋千。”時(shí)至今日,秋千仍是中國(guó)延邊朝鮮族、云南阿昌族等少數(shù)民族歡度新春佳節(jié)的重要娛樂活動(dòng)。
蘇州人有“春餅、夏糕、秋酥、冬糖”的習(xí)俗,而“酒釀餅”便是屬于春天的蘇式糕點(diǎn)。相傳酒釀餅起源于元朝末年,蘇州張土誠(chéng),因誤傷人命,帶著母親逃命,當(dāng)時(shí)正逢寒食節(jié),母親餓得暈了過去,幸得一位老伯用家中僅有的酒糟做了餅給她,才化險(xiǎn)為夷。幾年后,張土誠(chéng)在蘇州起義稱王,為了不忘當(dāng)年大恩,便下令寒食節(jié)吃酒糟餅,名叫“救娘餅”。后來(lái),蘇州人把“救娘餅”改叫“酒釀餅”,春天吃餅的習(xí)俗也沿襲至今。
此餅以蘇州當(dāng)?shù)氐亩←満途漆劄橹饕希嬗们寰漆劙l(fā)酵而成,內(nèi)餡有葷、素之分,品種主要有玫瑰、薄荷、豆沙等,由于氣候的原因,酒釀餅往往一年只賣一季。食用時(shí),以熱食為佳,方可領(lǐng)會(huì)到甜肥軟韌、油潤(rùn)晶瑩的滋味。
俗話說(shuō),蘇州清明食三色,紅者醬汁肉,綠者青團(tuán)子,而白者便是大方糕。這種糕點(diǎn)的賣相頗為精致,面上印有“福、祿、壽”等字樣和精美圖案,且餅皮薄如蟬翼,若定晴細(xì)看,還能隱約看見包裹其中的內(nèi)餡。因此,這雪白的大方糕又被當(dāng)?shù)厝朔Q作“五色大方糕”,特別是蒸熟后,不同餡的大方糕會(huì)透出不同的顏色,如黑色的芝麻餡、黃色的鮮肉餡、綠色的薄荷餡、紅色的玫瑰餡、豆沙色的豆沙餡等,可見糕點(diǎn)師傅的技藝之高超。
聽聞,大方糕還與戲曲《珍珠塔》中的主人公方卿有關(guān)。方卿功成名就之后,喜歡用糕點(diǎn)做早餐,認(rèn)為吃了代表“高興”。廚師因怕方卿吃厭,費(fèi)盡腦筋,最后想出法子,用方糕代替圓糕,并在面上印上“福、祿、壽”的字樣,且隱約可見不同餡色。方卿見了潔白如玉的大方糕,又驚又喜,在做壽時(shí)將它贈(zèng)給親友,于是這大方糕就在姑蘇地區(qū)流傳開來(lái)。
每年春天,在江浙地區(qū)的餐桌上便少不了一道炒螺螄。俗話說(shuō)“正月螺螄二月蜆”,螺螄可算得上是開春時(shí)最早被端上餐桌的水產(chǎn)美食了。江浙人也素有“清明螺,賽肥鵝”的說(shuō)法,其實(shí)他們俗稱的“螺螄”,與分布在云南省的螺螄是不同物種,實(shí)際應(yīng)為方田螺。春天時(shí),它們?cè)谕晾飻€了一個(gè)冬天的能量,少泥腥味,肉質(zhì)緊實(shí),正是懷胎肥美之時(shí)。所以每年驚蟄到清明期間,便是江浙地區(qū)螺螄銷售的旺季。
方田螺的烹飪方式有很多種,其中最受大家喜愛的,還是醬爆螺螄,其中又以馬路邊的大排檔做得最夠味。辣乎乎的一盤端上桌,一口螺螄,一口冰啤酒,在當(dāng)?shù)厝搜劾铩班菸囘^酒,強(qiáng)盜來(lái)了勿肯走”,也有人贊其“吃一斤鮑魚,還不如嗦十斤螺螄”。
從袁枚到梁實(shí)秋,只要到了杭州,似乎無(wú)人能逃過對(duì)春筍的念想。袁枚還曾在《隨園食單》中提及杭州筍,謂之“問政筍”,并寫道:“問政筍,即杭州筍也。徽州人送者,多是淡筍干,只好泡爛切絲,用雞肉湯煨用。”此外他曾寫過一道“玉片筍”,是“以冬筍烘片,微加蜜焉。蘇州孫春楊家有鹽、甜二種,以鹽者為佳。”可見蘇、杭兩地吃筍的習(xí)慣早已有之,且頗有心得。
時(shí)至今日,當(dāng)?shù)厝藢?duì)筍依然十分偏愛。杭州曾評(píng)選出36道名菜,光春天能吃到的筍就占4道:油燜春筍、南肉春筍、春筍步魚和蝦子冬筍。吃筍的時(shí)節(jié),大概開始于驚蟄前后,菜市場(chǎng)里春筍嬌嫩,再捎上一塊肥豬肉。肥肉熬油,待飽含鮮味的白嫩筍塊散出焦香,再經(jīng)過生抽、老抽、黃酒、紅糖提鮮,最終筍塊油光锃亮,如紅燒肉般咄咄逼人,便是一道令人食指大動(dòng)的“油燜春筍”。
古人借萱草寫下了諸多與母親有關(guān)的詩(shī)詞,后人也將萱草視為中國(guó)的母親花。除了這個(gè)象征意味,萱草還有一項(xiàng)突出的優(yōu)秀品質(zhì)——好吃。南宋人林洪在《山家清供》中有道春日名菜叫“忘憂齏”,采用的原料就是萱草屬成員之一黃花菜:“嵇康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則曰‘丹棘,又名鹿蔥。春采苗,湯瀹,以醋、醬作為齏,或燥以肉。何處順宰六合時(shí)多食此,毋乃以邊事未寧,而憂未忘耶?因贊之曰‘春日載陽(yáng),采萱于堂。天下樂兮,其憂乃忘。”
“春采苗”之“苗”應(yīng)當(dāng)是含苞欲放的黃花菜花苞,用湯焯過,滴醋和醬油簡(jiǎn)簡(jiǎn)單單便能成就這道爽口涼拌菜。或是高級(jí)一些,與肉同炒,兩種做法都鮮嫩得足以使人忘憂。而如今飯店里使用的黃花菜多是干貨泡發(fā),要用肉的油脂去浸潤(rùn)才能勉強(qiáng)接近新鮮時(shí)的口感,“忘憂”怕是忘不了的。
春日食春,將紅的綠的鮮的嫩的統(tǒng)統(tǒng)擺上桌,和著春光一同吃下。晉《風(fēng)土記》中就記載了立春食“五辛盤”的習(xí)俗,元人則攤薄餅,將備好的餡料卷起來(lái)下油焯制成“煎卷餅”。清《燕京歲時(shí)記》也有“打春,是日富家多食春餅”的記載。光陰流轉(zhuǎn),食春之法演變出了諸多形式,在閩南地區(qū),就出現(xiàn)了“春卷”這例可口美味。選水靈的時(shí)令蔬菜與肉類分別炒熟,再混成一鍋,將餅攤至透光如蟬翼,又有著恰到好處的韌勁,卷起餡料趁熱一股腦兒送入口中。閩南不同地方對(duì)于春卷的叫法不一,餡料選材也稍有不同。廈門叫“薄餅”,到了泉州則是“潤(rùn)餅”。而餡料多有包菜、胡蘿卜、荷蘭豆、豆干、蝦仁、肉絲等,可憑個(gè)人喜好調(diào)整。每至清明時(shí)節(jié),閩南人就有吃春卷的食俗,據(jù)說(shuō)是古時(shí)寒食節(jié)之遺風(fēng),也有考據(jù)稱是清明祭祖后為了避免供品浪費(fèi)而誕生的進(jìn)食方法。無(wú)論原因,這一卷卷起的都是春色,品味的都是對(duì)先祖的思念。
“數(shù)間茅舍,藏書萬(wàn)卷,投老村家。山中何事?松花釀酒,春水煎茶”。不知松花的滋味是有多美,能美得入選元代劇作家張可久的人生理想。《山家清供》中有一處詳細(xì)記載,書的作者林洪曾暇日訪友,“以松黃餅供酒”。這松黃,乃松樹春日抽芽時(shí)松花雄蕊所產(chǎn)的花粉,松黃餅就是用松黃為原料做的餅了。林洪記載的松黃餅制作非常簡(jiǎn)單:“春末,采松花黃和蜜模作餅,勻作如古龍涎餅狀。”而吃的儀式卻是相當(dāng)拿腔拿調(diào):“出二童,歌淵明《歸去來(lái)辭》……飲邊味此,使人灑起山林之興,覺駝峰、熊掌皆下風(fēng)矣。”松花量少且花期很短,因此松黃多是進(jìn)貢給皇家的貢品。吃著珍貴的松黃餅,有酒有歌有山景,吃出歸隱的念頭確實(shí)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