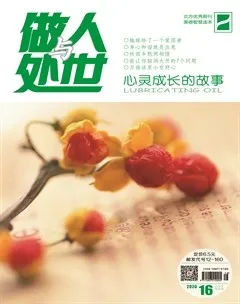但是還有書籍
王樹方

嗶哩嗶哩網站推出了一部紀錄片《但是還有書籍》,講述人與書籍的關系。各個故事里面的人物幾乎都是理想主義者。
在豆瓣網頗有名氣的圖書編輯朱岳,東奔西跑地到處向媒體推薦沒有多少名氣的作家袁哲生。他還因向朋友推薦袁哲生的《寂寞的游戲》被無情拒絕,而惱火地拉黑了該朋友。此書后來終于被廣大讀者所熟知,上榜了各路的年度圖書榜單,似乎昭示著朱岳對朋友的勝利。
北大副教授范曄將出版方邀請他翻譯《百年孤獨》這件事稱為“很難抗拒的誘惑”,是“和大師過招”。流暢詩意、不動聲色的翻譯文本,在當初閱讀時,讓我對馬爾克斯的這位譯者也驚為天人。想象中以為是個溫文爾雅、博聞強識的老翻譯家,卻看到鏡頭下的范曄竟是如此年輕,甚至帶著一絲羞澀。
還有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古籍整理編輯;開著一輛書車,一邊旅行一邊賣書的夫妻;承接父業的舊書店店主;富有童心的繪本畫家;創意十足的封面設計師。每個人和故事都那么美好、感動。
但是最讓我觸動的卻是朱利偉,因為這些都是普通人的故事。“利用每天上下班通勤的一個多小時,朱利偉在擁擠的地鐵和喧囂的人群中,一年讀完了幾十本書。與此同時,愛書人之間的惺惺相惜,讓她開始尋找同類。車廂里,零星有人在看復習備考的書,有人在看英文小說。于是朱利偉開始了地鐵攝影之旅。”她開始有意識地觀察,用手機捕捉地鐵上的讀書人,并將這些照片發布在豆瓣主頁的相冊集,取名《北京地鐵上的讀書人》。
我幾乎是本著朝圣一般的心情去翻找出了這本相冊。最近的照片更新日期就在不久前,相冊的數量已經達到1062張。我一張張地欣賞下去。和媽媽一起讀《窗邊的小豆豆》的小孩,教孫子讀《聲律啟蒙》的老人,拿kindle閱讀的年輕人……一行行,一頁頁,這些照片也像一本書啊。忽然想到一句不合時宜的詩來: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
我默默地把此相冊設為收藏,以便我能收到更新提醒,這真像追一部懸念十足的電視劇。
我也愛讀雜七雜八的書,愛逛各式各樣的書店。但不可否認的是,在微博、短視頻等APP異軍突起的情況下,閱讀甚至日漸式微也淪落為一個小眾的愛好。小眾到何種程度?看到地鐵上翻書的人,就當作是稀有的同道中人,不由自主產生親近的感覺,我甚至想跟他們聊一會天。
我還想起近日發現的一個沮喪的現象。我在跟朋友聊到某些作家時,拼音輸入法居然沒有收錄這些作家的詞條,而這些都是享譽世界的最有名的作家:翁貝托·艾柯、科塔薩爾、保羅·柯艾略……也許手機輸入法是本土輸入法的原因,可能對詞條有“偏科”情況。但在后續聊天過程中遺憾地發現,它對國內熱度頗高的作家,如余秀華、李修文等也并未收錄。我固執地認為,輸入法的詞條庫也反映了當代人精神生活的一種殘缺狀態。我希冀以后輸入法的詞庫,會因世上千千萬萬的人,在聊起這些作家,在拼寫這些作者的名字,終于重視這些詞條。
當然,作家的名字被收錄詞庫不是最終的目的。就像朱利偉和她鏡頭內外的地鐵上的讀書人,獲“年度閱讀場景”獎時,朱利偉說,她的本意并不是要鼓勵每一個人去地鐵上讀書,而是希望我們能夠隨時隨地打開一本書,去感受閱讀的美好之處。切斯瓦夫·米沃什的《但是還有書籍》寫道:“但是書籍將會立在書架,有幸誕生,來源于人,也來源于崇高與光明。”
你沒什么朋友,你被全世界拋棄,你過了沮喪的一天,不管“但是”之前你遭遇了什么,人生哪怕不堪,但是還有書籍。
(編輯/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