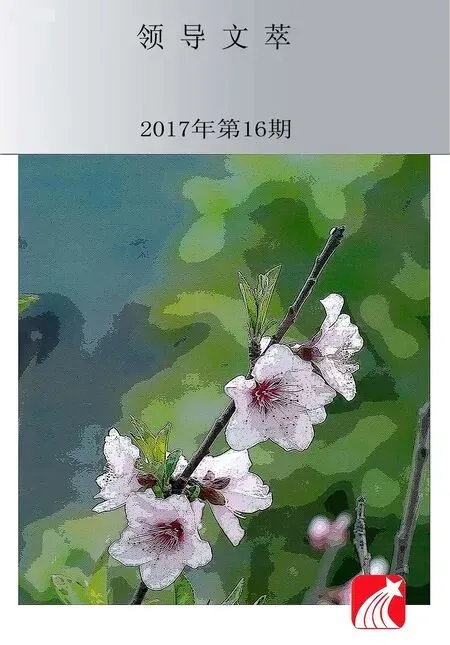政治家的勇氣
陶短房
2019年12月6日清晨,德國(guó)總理默克爾來(lái)到位于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yíng)。她穿著一身黑衣,頸部項(xiàng)鏈都是黑色。站在遇難者照片墻前,默克爾做了迄今為止,德國(guó)領(lǐng)導(dǎo)人對(duì)納粹反猶太罪責(zé)最深刻的反思。
“奧斯維辛是由德國(guó)人經(jīng)營(yíng)的一座滅絕營(yíng),德國(guó)人的責(zé)任永無(wú)終結(jié),沒有商量余地。這是我們身份認(rèn)同中一個(gè)不會(huì)消失的組成部分。”默克爾沉重地說(shuō)道,“鑒于德國(guó)人在這里所犯的野蠻罪行,我深感羞恥。”
對(duì)德國(guó)來(lái)說(shuō),反思、警惕納粹思想,似乎成了一個(gè)永無(wú)止境的事業(yè)。納粹政權(quán)雖然垮臺(tái),但納粹在這個(gè)國(guó)家的影響力,卻并未就此煙消云散。默克爾在演講中提醒德國(guó)人,“記住罪行、讓每個(gè)罪犯的名字被公之于眾,并向受害者致以崇高敬意,是一項(xiàng)永遠(yuǎn)不能停止的責(zé)任,這是不容商榷、和德國(guó)密不可分的,是德國(guó)國(guó)家身份的一部分。”
盡管政見不同,黨派各異,但戰(zhàn)后聯(lián)邦德國(guó)多任總理都公開表現(xiàn)出對(duì)納粹反猶大屠殺的深深懺悔,這幾乎成了德國(guó)領(lǐng)導(dǎo)人的政治傳統(tǒng)。施密特、科爾和默克爾三位德國(guó)(西德)總理先后憑吊過(guò)奧斯維辛集中營(yíng)遇難者。1970年12月7日,時(shí)任西德總理勃蘭特在波蘭華沙猶太人社區(qū)起義紀(jì)念碑前的“華沙之跪”更是震驚世界,這個(gè)紀(jì)念碑也成為“戰(zhàn)后德國(guó)官方對(duì)二戰(zhàn)罪責(zé)深刻懺悔”的標(biāo)志性地點(diǎn)。
2015年,時(shí)任德國(guó)總統(tǒng)高克歷史性地指出,“沒有奧斯維辛集中營(yíng),德國(guó)人就沒有身份,記住犯罪、標(biāo)明犯罪者并公正對(duì)待受害者是每一個(gè)德國(guó)人的責(zé)任”。2017年12月15日,現(xiàn)任德國(guó)總統(tǒng)施泰因邁爾在以色列駐德國(guó)使館發(fā)表演講時(shí)坦陳:“反猶太主義在德國(guó)依舊顯露著邪惡嘴臉。”2017年,德國(guó)執(zhí)政黨基民盟—基社盟(CDU-CSU)提出一份議案,責(zé)成聯(lián)邦政府鼓勵(lì)所屬16個(gè)州采取堅(jiān)決手段,將“煽動(dòng)反猶太仇恨的外國(guó)人驅(qū)逐出境”。
即便反思如此徹底,德國(guó)也經(jīng)歷過(guò)一段逃避時(shí)期。
冷戰(zhàn)初期的20世紀(jì)50年代,西德普遍患有“戰(zhàn)爭(zhēng)失憶”。1959年,西德就全國(guó)中學(xué)畢業(yè)生進(jìn)行問(wèn)卷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57%的學(xué)生沒有學(xué)過(guò)納粹史,79%不知道魏瑪共和國(guó),因?yàn)椤皶细緵]有”。
一些批評(píng)家指出,冷戰(zhàn)需要,以及個(gè)人免責(zé)的實(shí)用主義,導(dǎo)致戰(zhàn)后初期西德的“歷史失憶綜合征”泛濫成災(zāi)。
當(dāng)時(shí)西德國(guó)防軍中不乏納粹軍隊(duì)里的王牌飛行員和王牌潛艇艇長(zhǎng),不少前納粹軍隊(duì)高級(jí)將領(lǐng)受邀撰寫戰(zhàn)史或出版戰(zhàn)爭(zhēng)回憶錄,一些人更躋身戰(zhàn)后軍政高階——如曾擔(dān)任隆美爾參謀長(zhǎng)的斯派達(dá)爾就曾在北約出任要職——他們?cè)谡劶皯?zhàn)爭(zhēng)時(shí)往往“泛泛承認(rèn)罪責(zé),但強(qiáng)調(diào)那是希特勒或別的死人的責(zé)任,回避甚至掩蓋自己和健在者的責(zé)任”。
西方盟國(guó)急于扶植西德對(duì)抗東德是造成這一現(xiàn)象的關(guān)鍵。資料顯示,1946年11月,被認(rèn)為“有嚴(yán)重納粹罪行”者多達(dá)64萬(wàn),到1948年5月只剩2806人,其余幾乎都被赦免了。這導(dǎo)致戰(zhàn)后初期歷史觀的扭曲——40年代末西德成立前夕,西方占領(lǐng)的德國(guó)領(lǐng)土上33%的人相信猶太人本就不該享受平等對(duì)待,47%認(rèn)為納粹是“好心辦錯(cuò)事”,18%仍認(rèn)為“獨(dú)裁者至少建立了一個(gè)強(qiáng)大的國(guó)家”……這個(gè)時(shí)代的西德總理阿登納曾以“大多數(shù)西德人民與納粹暴行無(wú)關(guān)”為由,理直氣壯地拒絕承認(rèn)德國(guó)對(duì)迫害猶太人和納粹侵略的“集體罪責(zé)”。
歷史學(xué)家們指出,是勃蘭特等有勇氣的政治家的高瞻遠(yuǎn)矚和勇敢舉措,才扭轉(zhuǎn)了這一局面。他的“華沙之跪”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采取的勇敢但無(wú)奈的行為,目的是喚醒德國(guó)人,正視那段不堪的歷史,但當(dāng)時(shí)民調(diào)顯示,他這樣做的支持率只有42%。
“令人憂慮的種族主義”
納粹“老人”大量死亡和退休,尤其是冷戰(zhàn)的結(jié)束,才最終讓德國(guó)人甩掉歷史包袱,敢于正視戰(zhàn)爭(zhēng)中的種種不堪。那些曾逃過(guò)制裁的納粹余黨問(wèn)題,也再次擺在德國(guó)人面前。但這也造成另一個(gè)問(wèn)題,新一代人對(duì)歷史的記憶也變得淡漠。
由于對(duì)現(xiàn)實(shí)和傳統(tǒng)政黨、政治家滋生的不滿,也由于對(duì)歷史和德國(guó)二戰(zhàn)歷史罪責(zé)認(rèn)識(shí)模糊,許多德國(guó)年輕一代——尤其發(fā)展相對(duì)滯后的原東德境內(nèi)年輕人——開始支持帶有嚴(yán)重極右和排外傾向的“德國(guó)另類選擇黨”。2017年9月,這個(gè)原本的小眾政黨在德國(guó)聯(lián)邦議會(huì)選舉中贏得多達(dá)12.6%的選票,709個(gè)德國(guó)聯(lián)邦議會(huì)議席中拿下92個(gè),成為議會(huì)第三大黨。
該黨政要不斷發(fā)表拒絕反省德國(guó)戰(zhàn)爭(zhēng)罪責(zé)的露骨言論,該黨著名活躍人士、圖林根分部負(fù)責(zé)人赫克就曾表示,猶太人屠殺紀(jì)念館是“恥辱紀(jì)念”,他的同僚卡爾比茨甚至曾公開為新納粹組織張目。
就在默克爾發(fā)表“奧斯維辛演講”前兩個(gè)月,猶太人傳統(tǒng)的贖罪日,一名27歲的德國(guó)極右翼分子闖入德國(guó)東部哈勒一座猶太教堂,向聚集在教堂中舉行慶祝活動(dòng)的猶太人開槍射擊,導(dǎo)致兩人死亡。
這名被警方稱作“Stephan B.”的兇嫌是德國(guó)本地人,他在屠殺過(guò)程中還用頭盔攝像機(jī)進(jìn)行直播,長(zhǎng)達(dá)35分鐘。施暴過(guò)程中他用英語(yǔ)、德語(yǔ)狂呼“猶太人是全部問(wèn)題的根源”。
正如一些政治評(píng)論家指出的,這起事件充分表明,人們不能再對(duì)現(xiàn)實(shí)版的種族仇恨言行視若無(wú)睹,不能再自欺欺人地假定,納粹思想的余毒已隨著納粹德國(guó)的覆滅而成為永遠(yuǎn)塵封的歷史,不能認(rèn)為“恐怖分子都是特定的外來(lái)或宗教群體”,“只有特定的那類人才會(huì)搞針對(duì)平民的恐怖仇殺”。
德國(guó)之聲電臺(tái)曾經(jīng)研究發(fā)現(xiàn),網(wǎng)絡(luò)時(shí)代煽動(dòng)反猶、反特定群體種族仇恨言論,甚至串聯(lián)實(shí)施暴力行動(dòng)的,大多數(shù)是“獨(dú)狼”,并未加入人們熟知的極端組織。現(xiàn)實(shí)中,人們并不清楚他們的傾向和危險(xiǎn)性,他們?cè)诰W(wǎng)上彼此聯(lián)系,互相影響,他們從來(lái)不乏喝彩者、響應(yīng)者和效仿者。
經(jīng)過(guò)75年的努力后,德國(guó)的反納粹戰(zhàn)爭(zhēng)仍未止息,甚至有戰(zhàn)事更密的可能。默克爾的“奧斯維辛演講”,針對(duì)的不止是歷史,更是當(dāng)下。“我們正經(jīng)歷一種令人憂慮的種族主義,正經(jīng)歷對(duì)民主的攻擊和一種危險(xiǎn)的歷史修正主義。”默克爾說(shuō),“我們有責(zé)任,繼續(xù)保持這一記憶。”
(摘自《看天下》)
- 領(lǐng)導(dǎo)文萃的其它文章
- 完美無(wú)缺的作品
- 你會(huì)回答這個(gè)問(wèn)題嗎?
- 音差陽(yáng)錯(cuò)
- 漫畫
- 智珠
- 小幽默4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