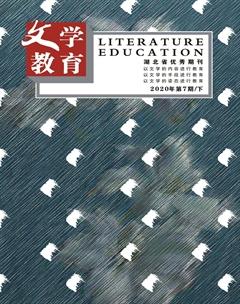亞里士多德悲劇情節(jié)論視域下的《活著》
王琪
內(nèi)容摘要:《活著》是余華先生于1992年完成的一篇家庭悲劇小說(shuō),他運(yùn)用日常化的語(yǔ)言,近乎克制地將福貴一家誤導(dǎo)的命運(yùn)、悲慘的生存境遇鋪陳在世人面前,筆觸無(wú)不浸透著苦難的因子。本文通過(guò)亞里士多德《詩(shī)學(xué)》悲劇理論中的情節(jié)整合論以及情節(jié)論中的“突轉(zhuǎn)”“發(fā)現(xiàn)”分析《活著》中福貴親人接踵而至的悲劇命運(yùn)。
關(guān)鍵詞:《活著》 《詩(shī)學(xué)》 悲劇情節(jié)論
自《活著》發(fā)表以來(lái),文學(xué)界對(duì)它的研究層出不窮,探討內(nèi)容主要體現(xiàn)在:一是對(duì)其主題思想的挖掘,包括苦難意識(shí)、悲劇意識(shí)、救贖意識(shí)。如昌切,葉李《苦難與救贖—余華90年代小說(shuō)兩大主題話(huà)語(yǔ)》中認(rèn)為《活著》體現(xiàn)出堅(jiān)韌的生存態(tài)度可使人在沉淪中得到救贖。二是對(duì)女性性格與形象上的研究。女性作為被遮蔽的群體,在《活著》中閃現(xiàn)著人性光輝,女性作為暴力的犧牲品、苦難的承擔(dān)者仍然有著堅(jiān)韌、顧家、抗?fàn)幍膫惱砻赖隆H缌秩A瑜《暗夜中的蹈冰者—余華小說(shuō)的女性形象解讀》。三是《活著》在國(guó)外的解讀和影響。如林政徑(韓)的《韓國(guó)對(duì)“苦難”母題的接受特點(diǎn)——以余華<活著>為中心的考察》分析韓國(guó)人眼中的苦難意識(shí)基于“苦難的社會(huì)性因素”,而福貴面臨的集體社會(huì)改革與當(dāng)時(shí)的90年代韓國(guó)人所經(jīng)歷的的危機(jī)有著相似之處。四是與同名電影《活著》的比較研究。如姚佩的《從小說(shuō)<活著>到影像改編的審美轉(zhuǎn)換》認(rèn)為張藝謀通過(guò)皮影戲體現(xiàn)人生如戲以及各種場(chǎng)面的視覺(jué)沖擊對(duì)比文本《活著》更體現(xiàn)其悲劇效果。五是從《活著》的敘事策略上,包括敘述視角的切換、敘事張力、死亡的荒誕、重復(fù)死亡的敘述風(fēng)格以及暴力敘述等。如王侃的《論余華小說(shuō)的張力敘事》。
在《詩(shī)學(xué)》中,亞里士多德對(duì)悲劇的探討展現(xiàn)出他卓越的見(jiàn)解,本文以其悲劇理論中的情節(jié)整合論和情節(jié)論中的“突轉(zhuǎn)”“發(fā)現(xiàn)”,來(lái)揭示余華筆下福貴一家的悲慘命運(yùn)。
一.《活著》中情節(jié)的整合性
在《詩(shī)學(xué)》中亞里士多德為悲劇作了定義:“悲劇是對(duì)于一個(gè)嚴(yán)肅、完整、有一定長(zhǎng)度的行動(dòng)的摹仿,······借引起憐憫與恐懼來(lái)使這種情感得到陶冶。”①并為悲劇規(guī)定了六種基本因素,包括形象、性格、情節(jié)、言辭、歌曲、思想,在這六種因素中,他將情節(jié)置于重中之重,認(rèn)為只要作品有布局即情節(jié)有安排,就一定能產(chǎn)生悲劇的效果,可見(jiàn)情節(jié)在悲劇中起著基礎(chǔ)性作用,是悲劇的靈魂。 在情節(jié)安排上,亞氏強(qiáng)調(diào)情節(jié)的有機(jī)統(tǒng)一性及不可分割性。“情節(jié)既然是行動(dòng)的摹仿,他所摹仿的就只限于一個(gè)完整的行動(dòng),里面的事件要有緊密的組織,任何部分一經(jīng)挪動(dòng)或刪削,就會(huì)使整體松動(dòng)脫節(jié)。”②所以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悲劇,其情節(jié)一定是有機(jī)統(tǒng)一并有緊密的聯(lián)系性,是一個(gè)完整的系統(tǒng)。
《活著》毫無(wú)疑問(wèn)的是一部極具悲劇性的作品,契合亞里士多德悲劇定義中的“完整”,通過(guò)“我”和福貴視角的來(lái)回切換,運(yùn)用插敘和倒敘的手法,余華借福貴之口,以福貴的一生作為時(shí)間軸,娓娓道來(lái)這個(gè)家庭在時(shí)代波流沖擊下?lián)u搖欲墜的狀態(tài)。雖然福貴親人“前仆后繼”的逝去,極具偶然性與荒誕性,頗有現(xiàn)代悲劇意味,但情節(jié)的安排并非毫無(wú)緣由,而是完整有機(jī)不可任意刪削的,如在描寫(xiě)福貴被迫隨軍作戰(zhàn)的歷程中,春生這個(gè)人物形象的出現(xiàn),并非是偶然或者隨意的,而是為后文春生的再度亮相埋下伏筆。在《活著》沒(méi)有多余的人物、沒(méi)有多余的情節(jié),甚至不摻雜作者本人的情感體驗(yàn)與道德審視,是一部筆法平淡卻蘊(yùn)含著不可承受之重的社會(huì)縮影圖。
二.《活著》中情節(jié)的“突轉(zhuǎn)”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lái),“復(fù)雜的行動(dòng)”指通過(guò)“發(fā)現(xiàn)”與“突轉(zhuǎn)”或二者同時(shí)發(fā)生而達(dá)到結(jié)局的行動(dòng),并且不是沒(méi)有預(yù)兆的發(fā)生,是依照必然或可然的發(fā)展規(guī)律,是意外之中,具有一定的前后承接關(guān)系。“突轉(zhuǎn)”強(qiáng)調(diào)主人公在復(fù)雜的行動(dòng)中,長(zhǎng)期處于順境或逆境中,但當(dāng)行動(dòng)發(fā)展到某一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態(tài)勢(shì)突變,行動(dòng)隨即轉(zhuǎn)入相反層面,或由順境轉(zhuǎn)逆境,或由逆境轉(zhuǎn)順境。“突轉(zhuǎn)”使得故事情節(jié)一波三折,更加引人入勝。接下來(lái)就情節(jié)論中的“突轉(zhuǎn)”對(duì)《活著》中人物命運(yùn)的反轉(zhuǎn)、無(wú)常進(jìn)行分析。
(一)福貴與龍二命運(yùn)的突轉(zhuǎn)
《活著》之中,龍二的命運(yùn)是極具戲劇性的,他作為當(dāng)時(shí)炙手可熱的賭博師傅,使用手段將福貴的家產(chǎn)奪了過(guò)去,這是他命運(yùn)轉(zhuǎn)向順境的一個(gè)標(biāo)志,同時(shí)也是福貴由順境轉(zhuǎn)向逆境的一個(gè)轉(zhuǎn)折點(diǎn),兩個(gè)人的命運(yùn)發(fā)生了戲劇性的反轉(zhuǎn),在這里就體現(xiàn)了情節(jié)中的“突轉(zhuǎn)”,這是福貴與龍二相關(guān)聯(lián)的命運(yùn)的第一次“突轉(zhuǎn)”,福貴的禍“果”是龍二的福“因”。隨著村里開(kāi)始搞土地改革,龍二不識(shí)時(shí)務(wù),倒了大霉最后被斃。這是福貴與龍二相關(guān)聯(lián)命運(yùn)的又一次“突轉(zhuǎn)”,由于社會(huì)因素,龍二最終落得悲慘的下場(chǎng),這一次龍二的禍“果”又成就了福貴的福“因”。福貴的因禍得福,令他認(rèn)為大難不死必有后福。然而,命運(yùn)的枷鎖從來(lái)沒(méi)有放過(guò)福貴,在僅有的一些溫存背后,是福貴一次次親眼目睹親人的逝去。
(二)鳳霞命運(yùn)的突轉(zhuǎn)
在《活著》中,鳳霞命運(yùn)的“突轉(zhuǎn)”激起無(wú)數(shù)讀者的憐憫,即使處于惡劣的環(huán)境和悲慘的生存境遇之中,她的淳樸善良仍然熠熠生輝。在短暫的幸福婚姻之后,就接受了命運(yùn)的宣判。在作品里有關(guān)鳳霞生產(chǎn)時(shí)的場(chǎng)景一曲三折,在鳳霞推進(jìn)產(chǎn)房之后,緊跟著醫(yī)生就出來(lái)詢(xún)問(wèn)是保大還是保小,二喜撲通就跪在了醫(yī)生面前,懇請(qǐng)她們一定要挽救鳳霞,到了中午醫(yī)生出來(lái)報(bào)喜稱(chēng)鳳霞生了兒子,二喜誤認(rèn)為醫(yī)生放棄了鳳霞,痛斥醫(yī)生保全了孩子放棄了鳳霞,然而醫(yī)生又說(shuō)鳳霞也平安無(wú)事,就在大家松一口氣的時(shí)候,不料鳳霞在天黑前就斷了氣。通過(guò)這緊張的情節(jié),向我們展示了鳳霞命運(yùn)的“突轉(zhuǎn)”,鳳霞的去世無(wú)疑再一次給福貴造成了重?fù)簦P霞死去的那間小屋子,同樣也是十多年前有慶去世的屋子,同一處地方,丟了一雙兒女的性命。鳳霞的突然死亡,同樣是情節(jié)發(fā)展中的“突轉(zhuǎn)”,措手不及的死亡,引起讀者的憐憫與恐懼,死亡的事情屢見(jiàn)不鮮,然眾多的死亡事件偶然的堆積在福貴身上,就極具荒誕意味,這種死亡敘事的筆法,是建立在情節(jié)一次次的“突轉(zhuǎn)”之上。
三.《活著》中情節(jié)的“發(fā)現(xiàn)”
亞氏在《詩(shī)學(xué)》中如此定義“發(fā)現(xiàn)”,“是指對(duì)人物關(guān)系或事態(tài)的由不知到已知的轉(zhuǎn)變,使那些處于順境或逆境的人物發(fā)現(xiàn)他們和對(duì)方有親屬關(guān)系或仇敵關(guān)系,并且一切‘發(fā)現(xiàn)中最好的是從情節(jié)本身產(chǎn)生的、通過(guò)合乎可然律的事件而引起觀(guān)眾的驚奇的‘發(fā)現(xiàn)”③。
(一)通過(guò)斷定而來(lái)的“發(fā)現(xiàn)”
在《活著》之中,有慶和鳳霞死亡時(shí),家珍都不是在場(chǎng)者,是通過(guò)斷定“發(fā)現(xiàn)”一雙兒女的去世,家珍的“發(fā)現(xiàn)”是根據(jù)情節(jié)的發(fā)展產(chǎn)生的,并非盲目的斷定或猜測(cè),而是體現(xiàn)可然律規(guī)則的。這里僅以家珍對(duì)有慶死亡的斷定為例。福貴對(duì)久病的家珍隱瞞了有慶的死亡,他自認(rèn)為如果家珍得知有慶的死訊,家珍必定承受致命的打擊,所以悄悄埋了有慶。在接下來(lái)的情節(jié)中,異常的行為舉止和長(zhǎng)時(shí)間的不歸家,都直接決定了家珍的推斷。《活著》中,福貴曾經(jīng)也有這種斷定的“發(fā)現(xiàn)”,當(dāng)他被迫參與到內(nèi)戰(zhàn)時(shí),在營(yíng)地看到那些橫七豎八的尸體,他就斷定自己也將死在這里。雖然福貴并未喪生,但他當(dāng)時(shí)的“發(fā)現(xiàn)”同樣是隨著情節(jié)的發(fā)展,按照可然律斷定的。
(二)與“突轉(zhuǎn)”共同發(fā)生時(shí)的“發(fā)現(xiàn)”
“當(dāng)‘突轉(zhuǎn)和‘發(fā)現(xiàn)同時(shí)出現(xiàn)的時(shí)候,能引起我們的憐憫和恐懼之情,而悲劇所要摹仿的正是產(chǎn)生這種效果的行動(dòng)。”④因此在情節(jié)的發(fā)展過(guò)程中,這兩種成分共同發(fā)生時(shí),是最能引起讀者驚異的。通過(guò)分析《活著》中有慶生命的“突轉(zhuǎn)”與春生的再度出現(xiàn),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他與福貴家的親屬或仇敵關(guān)系。
有慶的死亡,作者給我們留下一個(gè)懸念,造成有慶死亡的元兇是誰(shuí)?隨著情節(jié)推動(dòng),“突轉(zhuǎn)”和“發(fā)現(xiàn)”成為解決這一懸念的最終結(jié)果。有慶由于為縣長(zhǎng)夫人獻(xiàn)血而亡,福貴與害死他兒子的縣長(zhǎng)為仇敵關(guān)系,但由于“發(fā)現(xiàn)”了對(duì)方的身份,回憶到兩人在戰(zhàn)場(chǎng)上雖非親人更似親人的關(guān)系,卻不得不放棄復(fù)仇的念頭。在這一情節(jié)中“突轉(zhuǎn)”和“發(fā)現(xiàn)”是同時(shí)發(fā)生的,產(chǎn)生了強(qiáng)烈的震撼效果,令人憐憫。
結(jié)語(yǔ):《活著》在文章整體框架上契合亞氏在《詩(shī)學(xué)》中悲劇的定義,同時(shí)情節(jié)的安排與亞氏提出的情節(jié)“整一性”“突轉(zhuǎn)”、“發(fā)現(xiàn)”不謀而合。通過(guò)分析其情節(jié)中體現(xiàn)的“突轉(zhuǎn)”和“發(fā)現(xiàn)”,可以更深刻的感受到苦難猶如瘋狂生長(zhǎng)的野草包圍著福貴,也引起讀者的憐憫與恐懼,承受著家人相繼離世的福貴無(wú)疑成了苦難的象征物,展示出在時(shí)代激流的浪潮與生存環(huán)境的重壓下中,堅(jiān)強(qiáng)善良的福貴近乎荒誕式的人生苦旅。
參考文獻(xiàn)
[1]余華.活著[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2][古希臘]亞里士多德.詩(shī)學(xué)[M].羅念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3]昌切、葉李.苦難與救贖—余華90年代小說(shuō)兩大主題話(huà)語(yǔ)[J].華中科技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01(05)。
[4]林華瑜.暗夜中的蹈冰者—余華小說(shuō)的女性形象解讀[J].中國(guó)文學(xué)研究, 2001(04)。
[5][韓]林政徑. 韓國(guó)對(duì)“苦難”母題的接受特點(diǎn)——以余華<活著>為中心的考察[J].當(dāng)代文壇,2018(06)。
[6]姚佩.從小說(shuō)《活著》到影像改編的審美轉(zhuǎn)換[J].電影評(píng)介,2016(03)。
[7]王侃.論余華小說(shuō)的張力敘事[J]. 文藝爭(zhēng)鳴,2008(08)。
注 釋
①亞里士多德:《詩(shī)學(xué)》,羅念生譯,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頁(yè)。
②同上,第43頁(yè)。
③亞里士多德:《詩(shī)學(xué)》,羅念生譯,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頁(yè)。
④亞里士多德:《詩(shī)學(xué)》,羅念生譯,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0頁(yè)。
(作者單位:山西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