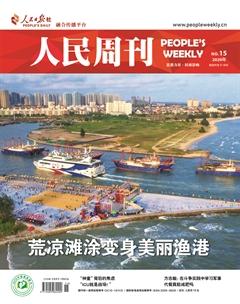古風古韻之點茶
王飛
歷朝風雅,兩晉而外,唯推宋明。其中晉代是濫觴,明代是余緒,宋代則為中興。宋代,對外懷柔偏安,對內開言興商,所以能在北宋興盛167年后,南渡又興盛152年,合計319年。存續超過300年的朝代,自秦以來,唯有漢代和宋代。
宋吳自牧《夢粱錄》中記載:“汴京熟食店張掛名畫,所以勾引觀者,留連食客。今杭城茶肆亦如之,插四時花,掛名人畫,裝點店面……茶肆皆士大夫期朋約友會聚之處。巷陌街坊自有提茶瓶,沿門點茶。”孟元老《東京夢華錄》也有類似記載:“以南東西兩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猶盛。”說明北宋好雅的風氣已經風靡市肆,更不論名人士大夫了。其中宋人愛茶到極致,蔡絛《鐵圍山叢談》記載:“茶之尚,蓋自唐人始,至本朝為盛,而本朝又至佑陵時益窮極新出,而無以加矣。”有宋一朝,春秋大宴皆有茶儀,并賜官員、使臣。宋徽宗趙佶親著《大觀茶論》,詳細描述制作品飲之法。翰林學士、福建路轉運使蔡襄創制小龍團,并著《茶錄》。梅堯臣親自茶地考察制茶,寫《南有佳茗賦》與歐陽修詩茗唱和,謂:“近年建安所出勝,天下貴賤求呀呀。”“停匙側盞試水路,拭目向空看乳花。”不論是君臣還是文人都如癡如醉,沉迷于氤氳的茶氣中。
點茶雅集上的宋盞
宋人樂茶、嗜茶,當時飲茶的方式有兩種:煎茶法與點茶法。煎茶自唐朝遺留延續下來,點茶則為后唐及宋所始創。用水注里的熱水把盞中投放的茶末浸潤、調膏,再注熱水少許,用竹筅調勻,再注水擊拂,如此五六次,盞內起饃,如結浚靄,如結凝雪,此為點茶。當時建州有北苑茶園,茶農每必以自家所產茶,斗以優劣,曰“茗戰”。此風遂入朝中,皇帝及士大夫以此為戲樂,又由上而下,風及國內,帝王貴胄、文人士大夫、禪門僧侶無不沉浸其中。宋徽宗有茶畫《文會圖》,劉松年有《攆茶圖》《茗園賭市圖》《博古圖》,趙孟頫有《斗茶圖》,所有這些呈現出來的茶人、茶具、茶法,相當于歷史之復現。距建州一千五百里之陜西藍田,近年考古挖掘出北宋呂氏家族墓,竟出土有建盞,可知當時茶風之廣。
《大宋宣和遺事》記徽宗“以惠山泉、建溪異毫盞,烹新貢太平嘉瑞茶,賜蔡京飲之”。又記:“夏四月,燕蔡京內苑,輔臣、親王皆與……又以惠山泉建溪異毫盞,烹新貢太平嘉瑞茶飲之。”蔡京《延福宮曲宴記》載徽宗為群臣點茶:“上命近侍取茶具,親手注湯擊拂,少頃,白乳浮盞面,如疏星淡月。”范仲淹有《和章岷從事斗茶歌》曰:“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黃金碾畔綠塵飛,紫玉甌心雪濤起。斗余味兮輕醍醐,斗余香兮薄蘭芷。”世上最為人知曉的《聽琴圖》記錄了當時的君臣風雅場面,此數處的描寫,當應是《點茶圖》,可惜沒能見到有畫家再現君臣斗茶之場面。
既然說“斗茶”,那么點的茶,如何判斷孰優孰劣呢?蔡襄《茶錄》載:“茶色貴白,黃白者受水昏重,青白者受水鮮明,故建安人斗試,以青白勝黃白。點茶,茶少湯多則云腳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其面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為絕佳。”宋徽宗《大觀茶論》載:“色,點茶之色,以純白為上真,青白為次,灰白次之,黃白又次之。”“乳霧洶涌,溢盞而起,周回旋而不動,謂之咬盞。”從這幾位斗茶頂級專家的論述看,可總結為:一斗湯色,白者勝;二斗泡沫,持久者勝。

劉松年《攆茶圖》(局部)
點茶、斗茶魅力何在?當時茶人的詩詞盡記之。宋徽宗《宮詞》云:“螺細珠璣寶合裝,玻璃甕里建芽香。兔毫連盞烹云液,能解紅顏入醉鄉。”蘇東坡詩云:“雪沫乳花浮午盞,蓼茸蒿筍試春盤。人間有味是清歡。”又《水調歌頭》云:“兔毫盞里,霎時滋味舌頭回。”黃庭堅《滿庭芳》:“兔毫金絲寶碗,松風蟹眼新湯。”陸游《烹茶》:“兔甌試玉塵,香色兩超勝。把玩一欣然,為汝烹茶竟。”《試茶》:“北窗高臥鼾如雷,誰遣香茶挽夢回?綠地毫甌雪花乳,不妨也道入閩來。”又《閑中》詩曰:“活眼硯凹宜黑色,長毫甌小聚香茗。”黃庭堅詞云:“纖纖捧,研膏濺乳,金縷鷓鴣斑。”楊萬里《以六一泉煮雙井茶》:“鷹爪新茶蟹眼湯,松風鳴雪兔毫霜。”《游惠山》:“敲火發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傾紫盞,色味兩奇絕。”從色彩斑斕的比擬中,讀之令人向往,是何等之美、何等之樂!
點乃何以美?斗乃何以勝?除茶本身以及技藝而外,器最為要,南宋審安老人創《茶具圖贊》,命名茶器具為“十二先生”,按宋時官制賦以官職并賜以名、字、號,配圖、擬贊。如茶筅為“竺副帥,名善調,字希點,號雪濤公子”,茶碗為“陶寶文,名去越,字自厚,號兔園上客”。“兔園上客”說的就是建州窯的兔毫盞。
點斗之器
瓷最早始于商代,由陶器發展而來,先為青瓷,至唐代,形成“南青北白”之勢。陸羽《茶經》謂:“茶碗,越窯為最,于煎茶法最宜。”明至今為撮泡法,是茶葉浸出汁液而飲,今綠茶、黃茶、青茶、紅茶、黑茶各色茗品繁雜,觀其湯色,白瓷最宜。宋人尚雅尚古,所用瓷器纖秾簡古,汝官哥鈞定,所出皆極品。但宋點茶法,就是喝茶葉末飲品,茶色白,入黑盞,其痕易驗。所以五大窯皆不取,唯取建窯之黑釉盞。唐器闊且矮,當時叫茶碗、茶甌;宋器挺拔收斂,多名以茶盞、建璜。
晚唐五代時,建安之地初造黑釉茶盞,建盞出自建窯,建窯出自建州。宋之建州,在今之福建建陽,建陽有水吉鎮,鎮有后井、池中諸村,窯群眾多:蘆花坪、牛皮侖、庵尾山、營長墘、源頭坑等。這些窯口都地處瓷礦,礦富鐵,是制作建盞的最佳材料;又皆近山林,林多木而有可燃之材;又皆近河流,水為道而有外運之便。
建窯與北苑御茶園同處建州,建州所燒制的建盞,最宜斗茶。細究其原因有三:一曰釉黑。宋徽宗《大觀茶論》謂“斗茶茶色白為貴”“盞色貴青黑,玉毫條達者為上,取其煥發茶色也”。純黑者名“烏金釉”,又有燒造過溫者,釉面出現兔毫、油斑,人奇而以其為貴,專門研究技巧燒造,兔毫越來越有名,人盡追崇,成為名器。二曰胎厚。蔡襄《茶錄》載:“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胚微厚,熁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言其胎厚利于保溫,保溫則饃易生,則水痕出現得遲,則就比薄胎的盞易于取勝。三曰型佳,“底差深而微寬,底深則茶直立,易于取乳”,注水而不濺,擊拂而不溢,托乳而難散。細觀建盞,其口沿薄而圓,腹漸厚,可數倍于口沿,至底為圈足,足矮且狹,內淺修,平滑利落。特別是束口盞,口內部有凸線,擊拂時會防止茶湯濺出來,外部有凹線,恰容下唇,利于品飲。“其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斗試家自不用”。此等佳制,所以當時斗茶人孜孜以求,得兔毫盞為寶。到了元代,馬背上的民族,不好點茶、斗茶,茗飲、茶器遂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