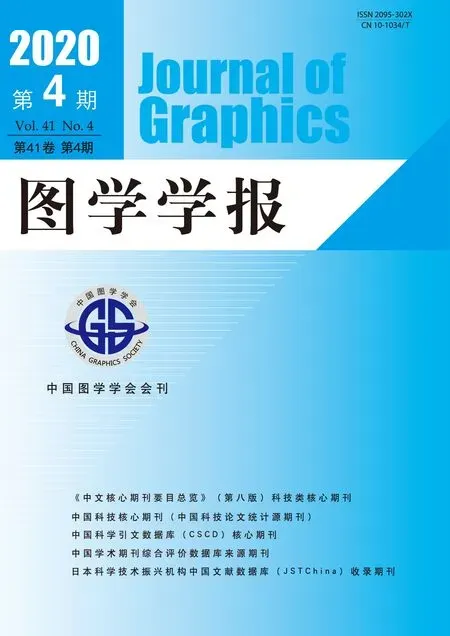BIM正向設計存在的問題和思考
陶桂林,馬文玉,唐克強,杜奕呈
BIM正向設計存在的問題和思考
陶桂林1,馬文玉1,唐克強2,杜奕呈3
(1. 重慶僑恩創源建筑設計有限公司,重慶 400012;2. 成都市建筑設計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0000;3. 貴州省交通規劃勘察設計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貴州 貴陽 550016)
BIM正向設計能夠減少部分建模環節、降低勞動和信息交換成本,其優點得到業界的廣泛認同。隨著國內BIM技術的不斷推廣,現有的BIM咨詢模式已不能滿足快速發展的應用需求,正向設計在實際應用過程中也遇到了很多困難。通過工程經驗和文獻調研總結了正向設計存在的問題,如:①缺乏與之適應的標準;②國內環境的制約;③技術鏈和產業鏈不夠成熟等,并對上述問題進行了思考與分析,得出以下結論:以出圖為導向的正向設計是BIM技術應用的過渡性策略,需補充相適應的標準體系、加大國內BIM軟件和云平臺體系的開發力度、促進設計與施工管理一體化。正向設計的推廣不僅需要有力的技術支持,更需要管理模式的不斷創新,為BIM技術的應用和發展提供保障。
建筑信息模型;集成項目交付;正向設計;綜述;項目管理
建筑信息模型(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BIM)是在建設工程及實施全生命期內,對其物理和功能特性進行數字化表達,并依次設計、施工、運營的過程和結果的總稱[1]。截止2019年3月,全國出臺建筑領域BIM應用標準的省市有北京、上海、重慶、天津、深圳市及浙江、安徽、福建省,極大地推動了全國BIM技術的應用發展。根據住建部印發的《關于推進建筑信息模型應用的指導意見》要求到2020年末新立項項目勘察設計、施工、運營維護中,集成應用BIM的項目比率達到90%:以國有資金投資為主的大中型建筑;申報綠色建筑的公共建筑和綠色生態示范小區。目前國內各大建設方、設計院和施工方都在努力根據相應的國家規范、行業標準和企業標準制定滿足住建部要求的實施BIM計劃,以期在未來的競爭中取得優勢。
可將BIM技術在國內數十年的運作情況劃分為4個階段(圖1):概念化階段、制度化階段、應用發展階段和深化融合階段。概念化階段主要以住建部印發的《關于印發2012年工程建設標準規范制訂修訂計劃的通知》為主要標志;制度化階段主要以2014年7月1日印發的《關于推進建筑業發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見》、同年12月印發的《建筑工程信息模型應用統一標準》征詢意見和2015年6月印發的《關于推進建筑信息模型應用的指導意見》為主要標志;應用發展階段主要以《P-BIM軟件功能與信息交換標準》、《建筑信息模型應用統一標準》GB51212-2016和各省市出臺的相應BIM應用標準為標志;深化融合階段以期與《中國制造2025》、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結合產生出鏈鎖式反應,迸發更強大的生命力。我國現階段BIM技術在建筑領域正處于應用發展階段的初級應用時期,故存在與之適應的問題和不足。如潘佳怡和趙源煜[2]通過調查問卷形式得出了阻礙BIM推廣的41項因素;紀博雅等[3]從經濟學角度分析國內企業應用BIM的經濟阻礙,并指出政府在解決該阻礙時應發揮主導作用,經濟效益是BIM應用的主要影響因素,經濟激勵政策可以加強BIM參與企業的應用程度,激勵效果是決定激勵政策的關鍵。BIM正向設計正是基于我國現階段BIM推廣應用困境提出的一種解決方案[4-7]。

圖1 我國BIM應用階段的劃分
1 BIM正向設計的提出
1.1 正向設計概念
BIM正向設計是以三維BIM模型為出發點和數據源,完成從方案設計到施工圖設計的全過程任務[8]。與傳統二維設計相比較,BIM正向設計的水平、質量和效率均有提高,專業協作更加完善,內容表達更加豐富,其優勢在游樂園[6]、工業廠房[7]、公共建筑[9-11]和道路橋梁[12-14]均有體現。
如果在建筑設計中實現正向設計,可為當下的BIM應用節省部分環節、降低勞動力和信息交換成本。正向設計的意義是讓設計師充分利用信息化平臺表達自己的設計理念,并通過BIM參數化設計快速、高效地實現設計而非將時間浪費在繪圖中[9]。正向設計執行的主要形式是實現方案優化、協同作業、設計信息參數化、計算和模型一體化、出圖自動化等。
1.2 為什么要做BIM正向設計
當下,現有的BIM咨詢應用模式不能滿足國內對BIM應用的迫切需求,全生命周期應用也不能像美國得到迅速普及,由此,正向設計作為一種解決方案便應運而生。現階段國內的建筑行業仍以圖紙為媒介進行信息交流傳遞,而BIM則依賴信息模型和信息應用技術平臺進行信息傳遞。我國雖然引進BIM技術數十年,但是并沒有改變我國基本的建筑行業狀況,業主、設計院和施工方的人員構成、信息傳遞模式和建筑行業的生產力方式均以傳統方式為主。這就導致了我國短期內應用全生命周期BIM技術不能像美國那樣降低生產成本,帶來經濟效益[15]。同時我國勞動密集型和粗放的建筑市場缺乏創新能力,導致BIM技術全周期的應用反而增加成本投入,極大地限制了其在我國的應用和推廣[3]。
為此,我國對BIM技術的探索被局限在了以出圖為導向的正向設計,并兼顧三維模型咨詢。這也間接地促進了設計方參與BIM建設的力度,從建筑設計階段開始推行正向設計,通過圖紙和模型依次貫穿甲方和施工方,減少施工變更、提升建造質量、平衡效益分配,積極推動建筑信息化建設。正向設計可以做到一模多用,不同應用階段均只需在一個模型上完善,從而極大地節省了人力成本。BIM的精細化設計可提前發現設計中的問題,優化設計、錯漏檢查、同時降低施工階段可能存在的返工風險,最終實現提升項目整體品質、節約成本、控制工期的目標[11]。除此之外,正向設計的廣泛應用將會帶來業務需求、標準體系、產業聯動等一系列變化,且需要建筑業內的相互協同和監督。
2 正向設計存在的問題
2.1 缺乏針對性技術規范和數據標準
國際智慧建設聯盟(building_SMART International)提出BIM領域的數據基礎標準主要圍繞數據定義(terminology)、數據儲存(storage)和數據處理(process) 3部分進行編寫,其分別對應字典框架(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dictionaries,IFD)、工業基礎分類(industry foundation classes,IFC)、信息交付手冊(information delivery manual,IDM)。截至2019年11月,國內頒布的BIM基礎標準見表1。除了國家標準外,還有眾多的地方標準和企業標準正在日益完善。

表1 國內頒布的BIM基礎標準
許多學者認為現存的建筑行業系統、國內規范標準是推動BIM發展急需破除的障礙[15]。王藝霖[16]明確了不同階段模型的審核要點,規范了模型審核工作流。目前的制圖標準和規范大都是按照二維設計進行編撰的,是服務于傳統設計的產物。從BIM角度分析,一些制圖和規范表達都顯得重復、多余,甚至累贅。比如,現在的審批平臺仍以審核圖紙為主要手段,依據的是傳統設計規范標準。而BIM是通過模型審核為主導,但其出發點和依據仍然相當模糊。若完全執行BIM正向設計,設計師的出圖效率將大打折扣,遠不及傳統設計,這也是正向設計難以推廣的主要原因。我國的BIM標準體系參照現行的國際標準體系編寫,但傳統的制圖規范標準、施工隊伍整體水平和歐美國家還有很大差距。歐美國家的制圖標準更有利于BIM的正向推廣,這就要求我國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出臺一些符合自身發展階段的應用規范和標準,能夠為BIM的正向設計鋪平道路。
2.2 國內環境制約
正向設計難以推廣的根本原因是國內環境的制約,主要包括軟件技術、建筑行業信息化、分配制度等。
馬智亮[17]認為BIM在國內的發展主要受軟件、標準和應用模式的制約。徐博[4]利用BIM技術對鐵路工程進行正向設計研究發現基礎平臺專業化程度偏低,正向設計效率偏低、需根據國內設計習慣加強二次開發,提高設計效率。楊杰等[18]根據給排水結構工程的正向設計研究得出需要解決的問題是模型輕量化和結構計算一體化的建立。PRUSKOVA和KAISER[19]認為從設計師的角度出發,BIM正向設計主要障礙是缺乏合適的技術工具,其不僅需要適用的軟件,還要有精準數據共享及協作。國內正向設計實踐證明與之相適應的國產軟件設計能力還不能滿足市場需求,需要加大研發力度。國內的BIM軟件商主要有廣聯達、鴻業科技、PKPM、盈建科和廣廈科技等,而能提供正向設計的卻很少。且正向設計軟件思路大多以二維設計流程為模板,采用簡單三維模型二維化表達模式,而不是通過尋求與BIM相適應的工程運作模式和標準化設計,最終很難取得滿意的應用效果。
BIM正向設計的推進依賴建筑行業的信息化程度,因為BIM融合了計算機輔助設計(computer aided design,CAD)和現代項目管理2大專業領域知識。但我國建筑行業整體信息化水平偏低,信息化率僅為0.3%,而國際水平是我國的10倍,其是導致我國建筑業利潤率一直偏低的原因。高承勇[20]認為建筑的信息化和工業化相互促進、支撐,可以有力地推動建筑設計、施工和運維技術的發展。同時馬智亮[21]認為應從熱點信息技術和應用模式2個方面把握建筑企業信息化發展趨勢。正向設計是BIM技術系統的一部分,其所創造的成果容易形成信息孤島,不利于充分發揮效益優勢。
分配制度也是阻礙正向設計推廣的重要原因之一。宋家仁等[22]通過納什談判和威脅談判分析業主方和設計方的利益得出建筑工程應用BIM技術對雙方收益均有所增加,且對業主方的收益更大,建議業主方在合同中添加補充設計方的收益條款。顏磊[23]通過公平關切理論建立利益分配模型解析后得出合理的利益分配有益于工程參與方整體利益最大化,且業主方應根據貢獻度進行公正合理的利益分配。徐瑾等[24]以大型公建項目為例運用shapely值法建立利益分配模型,研究了新環境對各參與方應用BIM技術風險和利益分配的影響,并通過修正模型實現了項目中各參與方利益分配的公正性和合理性。BIM正向設計正在逐漸打破傳統的建筑行業分配體制,因此,科學分析各方運用BIM技術參與度,重建建筑供應鏈利益分配格局應亟待解決。目前,我國正向設計的主體是設計院,而直接受益者是建設方和施工方,但設計院需要對計算機硬件和人才進行升級,從而增加了生產成本,卻很難成為正向設計的關鍵受益者。這種情況直接導致了正向設計源頭設計院缺乏推廣的積極性,整個產業鏈也就很難實現良性循環。
2.3 BIM技術鏈和產業鏈不夠成熟
BIM不是單一的應用軟件,而是一個集成專業知識、信息平臺和軟件功能的高層次平臺,成為實現數據交換、信息交流和部門協同的核心。正向設計作為BIM技術鏈條中的一個環節,與其成熟度息息相關。本文主要對BIM+PM和BIM+數字加工2項技術集成進行深入闡述,因為其對正向設計具有更大影響。
傳統的項目交付模式主要有CM-at-Risk (construction manager at risk),DB(design-build),DBB (design-bid-build)等,由于存在業主方、設計方和施工方之間利益和風險分配不均衡,形成了長期的競爭對抗關系,致使建設成本較高和周期較長[25]。于是歐美等發達國家于上世紀90年代開始在項目中使用集成項目交付(integrated project delivery,IPD)管理模式并取得成功,有效克服了傳統管理模式高成本和長周期的缺點。隨著BIM技術的快速發展,其所具有的信息化、集成化和協同性等特點為IPD管理模式推廣提供了強大的支持[26]。但是相較于美國,我國基于BIM的IPD協同工作模式的應用還非常有限。2011年徐韞璽等[27]基于BIM建設項目IPD協同管理研究指出BIM、協同工作流和基于價值的群決策機制是IPD框架的重要組成部分。2014年馬智亮等[28]通過分析國外22個IPD項目案例,建立了基于IPD的項目信息利用框架。2016年徐友全和孔媛媛[29]通過定量分析CNKI有關IPD的文獻數據,得出BIM技術應用是IPD項目成功的關鍵,國內推廣IPD存在的障礙主要是BIM技術、政策法規和缺少適合國情的合同文本。2017年馬智亮和李松陽[30]對我國IPD模式在PPP項目管理的應用研究,提出2種可操作模式并指出其所面臨的挑戰。2018年高崧和李衛東[31]研究BIM發展路線和一體化項目交付時指出我國BIM的應用還處于技術層級,缺乏深層次的價值應用,建議BIM和IPD的緊密協作,助推一體化交付模式更加完善。總之,BIM+IPD在我國的應用還處于起步階段,仍有很長的路要走。2019年美國學者NGUYEN和AKHAVIAN[32]將IPD、精益施工(lean construction)和BIM整合為一個信息框架,即ILB模式,并運用扎根理論分析了美國72個真實建筑項目,完善了整個項目管理領域的知識體系。項目交付模式越來越向深度協同、高效集成和信息同步共享的縱深發展,但我國的項目管理大部分還處于傳統交付模式,極大地束縛了BIM技術的應用,正向設計更是舉步維艱。
BIM技術與數字化加工集成是利用制造設備將BIM模型中的數據信息進行數字加工,主要用于預制混凝土構件、管線預制加工和鋼結構加工等方面,國內主要是以裝配式建筑的形式進行推廣。BIM的虛擬建造為裝配式建筑的施工提供了堅實基礎,節約建造成本、縮短施工周期、加強安全工作環境且便于精細化管理[33-35]。但目前我國裝配式建筑+BIM應用技術集成還處于初級階段,仍面臨如相關技術標準不完善、裝配結構設計以傳統理念為主、BIM技術和裝配設計結合不緊密、軟硬件配置難以滿足現實需求等問題[36-37]。另外,ZHANG等[38]詳細分析了阻礙香港采用裝配式制造的22個因素,得出了最大的影響因子有設計變更僵化(inflexible for design change)、現場儲存空間不足(lack storage space on site)、引入時間長(long lead-in time)、設計周期長(long design time)、初始成本高(high initial cost)和總成本高(high total cost)。
目前的裝配式建筑和傳統方式相比總成本偏高和周期偏長的原因主要是構件生產企業的產能未充分發揮,無法形成規模效應降低成本、設計和施工缺乏工業化生產的實踐能力效率低下[39]。這與BIM+裝配式可以降低建造成本和縮短施工周期的優點是不矛盾的,實現的前提條件是該技術集成必須是成熟和完善的。對于中國建筑行業巨大的異質市場,阻礙BIM和裝配式建筑應用的原因有其獨特性質,且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關聯構成了復雜的網絡。TAN等[40]利用層級關聯模型(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SM)分析了中國BIM和裝配式建筑的阻礙因素,并將其分為3個層級,同時,針對每個層級提出了相應的對策。第1層級應根據國情以學術研究、標準制定和面向國內軟件開發應對;第2層級應建立適合BIM應用的生態系統,如成熟的工作流和管理機制,加強個體的技能培訓;第3層級應加強BIM在裝配式建筑項目中的應用物有所值。在我國乃至發達國家BIM+數字加工技術應用都面臨很大的阻礙,若不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對于正向設計的產業鏈延續無異于釜底抽薪。
3 正向設計發展路徑思考
3.1 完善正向設計制圖標準
目前我國勘察設計過程中,圖紙不可或缺,只能將BIM信息數據轉化為圖紙形式[41],正向設計由此提出。我國與美國標準體系相似,面向軟件開發和建設行業2類人員有IFC、IFD和IDM 3類標準。美國和中國在施工圖繪制方面有較大差別,BIM圖紙繪制更適合美國體系。我國正向出圖、制圖仍采用二維設計時的制圖標準,如09J801《民用建筑工程建筑施工圖設計深度圖樣》、09G103《民用建筑工程結構施工圖設計深度》等,其存在重復應用和效率偏低的弱點,不利于正向設計的推廣,BIM正向制圖如圖2所示。BIM是攜帶信息的三維模型,其已具備了指導施工的巨大優勢,可大大減少對二維圖紙的依賴。未來在施工過程中將會出現無紙化操作,可利用移動設備觀察模型、提取相關信息并指導施工。二維設計信息媒介傳輸方式和表現形式均為圖紙;BIM設計信息傳輸途徑是電子移動設備、云平臺等,表現形式多樣,既可以是平面也可以是3D形式和動畫模擬等。我國的BIM標準體系應考慮現階段在過渡過程中兩者混合且以傳統應用為主的局面,因該階段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需要制定適合的制圖標準為解決BIM正向設計掃除障礙,盡最大努力實現各個專業的完全正向設計,解除目前BIM在設計中的尷尬地位。
另外,還必須清晰地看到,BIM技術是面向整個生命周期,集設計和管理為一體的復雜的技術平臺,又因BIM技術標準體系編制緊促,在BIM實施過程中會出現一些問題和困惑,從客觀上要求不斷地完善我國的標準體系[42-44]。
3.2 加大BIM相關軟件研發力度
全球建筑軟件市場規模到2021年預計達到110億美元,年復增長率11.0%;2022年預計達到115億美元,年復增長率19.1%。世界上BIM領先的軟件企業主要有美國的Autodesk,Bentley Systems,Trimble和德國的Nemetschek等。目前中國有最大體量的建筑市場,且國內BIM軟件開發企業有廣聯達、魯班、鴻業科技、天正、PKPM、盈建科、北京博超時代、翻模大師、廣廈結構和橄欖山等。經過對比國內外典型的BIM應用軟件和成熟度(表2),發現我國的BIM軟件公司多為二次開發、規模較小,缺乏核心技術,受制于人,難以形成國際競爭力。究其原因,BIM軟件的發展是從汽車、航空等先進制造業起步并拓展而來,從二維和三維CAD逐步演化、技術積累,再擴張到現在的多維BIM技術。近年,我國制造業水平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為BIM軟件的研究開發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這種小而多的局面無法形成像Autodesk這樣集成式的軟件開發商,能夠針對BIM行業的開發和研究做出突出貢獻,提出新穎的解決工程問題辦法、改變行業運行規則。國內軟件開發商研究的重點多集中在BIM行業的某一個或幾個急需的點,而對BIM宏觀政策、未來“BIM+”的研究投入偏少。國內軟件商與施工方、甲方相比地位差距很大,資金不足、研發人才匱乏,解決工程問題的新概念和新思路很難被提出、更難成為現實。目前技術的追趕難度依然很大,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于技術供給側的國產軟件核心技術水平和市場需求側建筑現代化的管理水平。對此,特提出3點建議:

圖2 BIM正向設計平面圖

表2 典型的BIM軟件公司及產品成熟度
(注:研發:市場較少使用,研發為主;成熟:市場已廣泛使用,但穩定性有待提高;穩定:占該領域市場主導地位,性能穩定)
(1) 政策上。政府應給予軟件業更大的政策優惠,減免稅負,增加知識產權保護力度,創造良好的競爭環境。
(2) 策略上。并購小型的、先進的BIM軟件公司,加速掌握核心技術,更多地依靠自主研發創新,且加強人才培養力度。
(3) 技術上。結合國內的規范和國情開發國產的BIM軟件平臺,系建模、計算、管理、算量、運維等為一體。另外,應重視云計算、5G技術的集成開發,保持在新技術領域不落后與人。
3.3 推進設計和施工統一化進程
推進設計和施工一體化進程是解決BIM應用向技術鏈和產業鏈深度推廣的關鍵因素。加強工程交付模式創新、提高工程建設質量和效率成了建筑業需要迫切解決的問題。因存在參與者之間利益目標不一致和應用碎片化現象,傳統的交付模式(如DBB, DB, CM-at-Risk)阻礙了相互協作,增加了建設成本和項目周期。而且隨著國內建筑項目越來越復雜,該缺點表現的更加突出[45]。根據2.3節國內外文獻研究表明,集成的信息管理需求和BIM技術平臺高度契合,可以克服傳統交付模式存在的大量缺陷。根據美國建筑師協會定義,IPD模式是一種集人員、平臺、架構和設施為一體,讓所有參與者通過充分發揮個人才干達到優化建造、減少浪費,最大限度提高項目整體效率和價值,從而使各方獲取最大收益的一種交付方式[1]。IPD和BIM應用均是將設計和虛擬模擬提前到項目建造前,各方通過虛擬建造分配責任、風險和收益,然后通力合作完成實際項目建造。
現階段,BIM技術的應用成熟度還不能完全滿足IPD的理想需求,需要進一步研究開發和IPD相適應的BIM技術應用。另外,國內建筑行業交付模式還是以傳統交付為主,缺乏相應的理論框架和實踐經驗。在實際工程項目中應用IPD模式并不容易,需要建立一系列的支持其運行的系統技術平臺,如缺乏合理的補償模型。ELGHAISH等[46]在掙值管理和作業成本法的基礎上提出結合BIM自動補償優化風險/收益共享機制。設計和施工一體化是我國推廣建筑現代化重要組成部分,技術和管理模式創新是成功的基石。
針對上述問題提出以下建議:①加速推動設計和施工的統一化進程,全面接軌國際先進管理方式,并結合中國實際摸索一套適合自身的工程管理模式。②適應新型IPD模式,強化設計先導作用,強化設計對使用功能、性能與質量的作用,充分發揮建筑師的主導作用。③全力推行工程總包,促進設計施工深度融合,提高設計水平,注重設計優化、深化,強調總包統籌。
3.4 正向設計是過渡性策略
目前國內提出的正向設計仍然是以圖紙為信息載體,這主要是因為BIM技術本身還處于初始階段,不夠成熟,各項理論和實施策略充滿不確定性,技術發展和工程管理尚未成熟[3]。以圖紙作為信息傳遞載體和BIM的設計初衷是不相符的,具有很強的時代局限性。《2019上海市建筑信息模型技術應用與發展報告》提出了需要全面落實的4項任務:①加強“1+X”模式人才培養;②建立本市BIM計價規則;③加強BIM技術應用過程監督;④推進施工圖審查和竣工交付由二維向三維轉變。第4項針對正向設計存在的方向性問題進行了解決,同時報告提出建立基于BIM技術的建設管理智能審批平臺,健全與之相匹配的管理體制和工作流程,形成在設計階段以“審模”為主,在施工階段以“按模”施工、驗收,在交付階段以“竣工模型”為主的新模式的解決方案。
未來BIM正向設計將遵循BIM的本質要求,強化與之相符的信息流傳遞,優化傳統管理理念,充分發揮信息化環境下的新技術,如5G和物聯網將加速BIM推廣,AI和云計算將賦能BIM升級。未來建筑信息的傳播應以信息模型的方式在設計方、甲方、施工方、造價方和采購方等部門傳遞,并以云平臺為載體協作共享管理,甚至部分工作將通過AI智能完成。在信息模型替換圖紙后,目前的“正向設計”也將走向終結,符合BIM內在規律的設計模式將發揮更大優勢。
4 總結與展望
BIM正向設計是探索BIM技術應用的方式之一,其有力地促進了該技術的應用推廣。但從國內外的研究來看,BIM技術仍處于初始階段,全生命周期的應用還面臨諸多挑戰,以圖紙為導向的正向設計具有很強的時代局限性。我國正向設計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 缺乏針對性技術規范和數據標準。現階段以出圖為導向的正向設計規范標準不夠完善,不能和現階段的實際情況吻合,制約了制圖效率。
(2) 國內環境因素的制約。缺乏自主開發的BIM軟件平臺體系,且二次開發參差不齊;建筑信息化和工業制造信息化程度偏低;現有建筑行業分配體系制約BIM正向設計。
(3) 國內BIM技術鏈和產業鏈還不完善。現有項目交付模式和正向設計不匹配,影響應用效率;裝配式建筑還不成熟,制約了BIM技術的推廣。
針對正向設計存在的問題,提出了解決方案,并對以圖紙為導向的正向設計進行了思考。
未來工程信息傳遞必將以信息模型為主,以云計算為基礎,通過人工智能和物聯網技術賦能升級,各種管理、審核和施工驗收等均通過云平臺實現。
[1]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建筑信息模型應用統一標準》GB/T 51212-2016[S]. 北京: 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2016: 1-2. National Standards of P. R. China.Unified standard for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GB/T 51212-2016[S]. Beijing: China Architecture & Building Press, 2016:1-2 (in Chinese).
[2] 潘佳怡, 趙源煜. 中國建筑業BIM發展的阻礙因素分析[J]. 工程管理學報, 2012, 26(1): 6-11. PAN J Y, ZHAO Y Y. Research on barriers of BIM application in China’s building industry[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012, 26(1): 6-11 (in Chinese).
[3] 紀博雅, 戚振強, 金占勇. 基于外部性分析的建筑業BIM應用阻礙及對策[J]. 施工技術, 2014, 43(3): 84-87. JI B Y, QI Z Q, JIN Z Y. Obstacl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BIM application in building industry based on the externalities analysis[J].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2014, 43(3): 84-87 (in Chinese).
[4] 徐博. 基于BIM技術的鐵路工程正向設計方法研究[J]. 鐵道標準設計, 2018, 62(4): 35-40. XU B. Research on forward design method of railway engineering based on BIM technology[J]. Railway Stabdara Dwsign, 2018, 62(4): 35-40 (in Chinese).
[5] 許志堅, 陳少偉, 羅遠峰, 等. 基于Revit的正向設計族庫建設研究[J]. 土木建筑工程信息技術, 2018, 10(6): 102-106.XU Z J, CHEN S W, LUO Y F, et al. Research on establishing family library in Revit for the forward design[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2018, 10(6): 102-106 (in Chinese).
[6] 高一鵬. 基于主題樂園項目的BIM正向設計技術研究[J]. 建筑技術開發, 2018, 45(14): 30-31.GAO Y P. Research on BIM forward design technology based on theme park project[J]. Architectural Design, 2018, 45(14): 30-31 (in Chinese).
[7] 張朝虎. 盛吉申電子產業園二期全專業BIM正向設計實踐[J]. 工程建設與設計, 2019(10): 276-278. ZHANG C H.The Practice of full professional BIM positive design of the second phase of Shengjishen Electronic Industrial Park Project[J]. Construction & Design For Project, 2019(10): 276-278 (in Chinese).
[8] 吳文勇, 焦柯, 童慧波, 等. 基于Revit的建筑結構BIM正向設計方法及軟件實現[J]. 土木建筑工程信息技術, 2018, 10(3): 39-45.WU W Y, JIAO K, TONG H B, et al. BIM forward design method and software implementation of building structure based on Revit[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2018, 10(3): 39-45 (in Chinese).
[9] 張淇. BIM正向設計過程研究—以廣州空港高層辦公建筑為例[J]. 低碳世界, 2019, 9(5): 162-164.ZHANG Q. Research on BIM forward design process, Guangzhou Airport high-rise office building[J]. Low Carbon World, 2019, 9(5): 162-164 (in Chinese).
[10] 浦至, 鄭昊. 超高層辦公樓建筑多專業協同BIM正向設計[J]. 土木建筑工程信息技術, 2019, 11(1): 110-119.PU Z, ZHENG H. BIM-based multi-speciality collaborative forward design for super high-rise office building[J].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ivil Engineering and Architecture, 2019, 11(1): 110-119 (in Chinese).
[11] 魏欣. BIM正向設計的應用與優勢南航武漢機場南工作區綜合保障樓[J]. 中華建設, 2018(8): 112-114.WEI X. BIM forward design application and research, Southern Airlines Wuhan Airport south work area comprehensive security building[J]. China Construction, 2018(8): 112-114 (in Chinese).
[12] 王文虎, 張易辰. 公路設計BIM正向設計理念探討[J]. 工程技術研究, 2019, 4(5): 190-191.WANG W H, ZHANG Y C. Highway design BIM positive design concept[J]. Engineering Design, 2019, 4(5): 190-191 (in Chinese).
[13] 何其檜. 公路工程BIM正向設計探討與實踐[J]. 價值工程, 2019, 38(26): 231-232.HE Q H. Discussion and practice of forward design of highway engineering BIM[J]. Value Engineering, 2019, 38(26): 231-232 (in Chinese).
[14] 劉瑋. 獨柱型鋼塔斜拉橋設計及BIM正向設計應用[J]. 工程建設與設計, 2019(15): 158-161.LIU W. Design of a single-column-shaped steel tower cable—stayed bridg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BIM forward design[J]. Construction & Design For Project, 2019(15): 158-161 (in Chinese).
[15] LIU B S, WANG M, ZHANG Y T, et al. Review and prospect of BIM policy in China[M]. Bristol: IOP Publishing LTD, 2017: 245.
[16] 王藝霖. BIM正向設計模型審核工作的研究[J]. 山東工業技術, 2019(12): 113-114.WANG Y L. Research on BIM forward design model review[J]. Shandong Industrial Technology, 2019(12): 113-114 (in Chinese).
[17] 馬智亮. BIM技術及其在我國的應用問題和對策[J]. 中國建設信息, 2010(4): 12-15.MA Z L. BIM technology and its applica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China[J]. Information of China Construction, 2010(4): 12-15 (in Chinese).
[18] 楊杰, 楊海濤, 羅晨皓, 等. 基于BIM的給排水工程結構正向設計研究[J]. 中國市政工程, 2018(4): 71-74, 111-112.YANG J, YANG H T, LUO C H, et al. Study on the forward design of water supply & drainage engineering structure based on BIM[J]. China Municipal Engineering, 2018(4): 71-74, 111-112. (in Chinese).
[19] PRUSKOVA K, KAISER J. Implement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to the design process using the scheme of BIM execution plan[J]. IOP Conference Series: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9: 471: 022019.
[20] 高承勇. 以信息化推進建筑工業化進程[J]. 中國勘察設計, 2014(9): 40-43.GAO C Y. Promote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on industrialization with informatization[J]. China Inestigation & Design, 2014(9): 40-43 (in Chinese).
[21] 馬智亮. 全球建筑業企業信息化發展趨勢[J]. 施工企業管理, 2015(4): 97-98.MA Z L.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informatization of global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J].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Management, 2015(4): 97-98(in Chinese).
[22] 宋家仁, 申玲, 李云飛. BIM應用中業主與設計方利益分配博弈分析[J]. 價值工程, 2017, 36(6): 42-44.SONG J R, SHEN L, LI Y F. The game theory analysis between owner and the design company on the benefit distribution of BIM application[J]. Value Engineering, 2017, 36(6): 42-44 (in Chinese).
[23] 顏磊. BIM項目業主與設計方公平關切利益分配研究[J]. 水利技術監督, 2019, 27(4): 155-158.YAN L. Research on fair concern distribution between owners and designers of BIM projects[J]. Technical Supervision in Water Resources. 2019, 27(4): 155-158 (in Chinese).
[24] 徐瑾, 陳相勇, 鐘煒. 基于Shapely修正的BIM項目利益分配模型研究[J]. 價值工程, 2017, 36(26): 58-61.XU J, CHEN X Y, ZHONG W. Research on BIM project profit distribution model based on shapely amendment[J]. Value Engineering, 2017, 36(26): 58-61 (in Chinese).
[25] AIA National, AIA California Council. Integrated project delivery guide 2007[EB/OL]. [2019-12-13]. https://help.aiacontracts.org/public/wp-content/uploads/2020/03/IPD_Guide.pdf.
[26] 黃聰聰, 姚傳勤. 基于BIM和IPD協同管理模式的淺析[J]. 四川建筑, 2017, 37(6): 230-232.HUANG C C, YAO C Q. Analysis of the cooperative management mode based on BIM and IPD[J]. Sichuan Architectural, 2017, 37(6): 230-232 (in Chinese).
[27] 徐韞璽, 王要武, 姚兵. 基于BIM的建設項目IPD協同管理研究[J]. 土木工程學報, 2011, 44(12): 138-143.XU Y X, WANG Y W, YAO B.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IPD collaborative management based on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J]. China Civil Engineering Journal, 2011, 44(12): 138-143 (in Chinese).
[28] 馬智亮, 張東東, 馬健坤. 基于BIM的IPD協同工作模型與信息利用框架[J]. 同濟大學學報: 自然科學版, 2014, 42(9): 1325-1332.MA Z L, ZHANG D D, MA J K. BIM-based collaborative work model and information utilization framework for IPD projects[J]. Journal of Tongji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2014, 42(9): 1325-1332 (in Chinese).
[29] 徐友全, 孔媛媛. IPD模式的國內研究現狀及展望[J]. 工程管理學報, 2016, 30(5): 12-17.XU Y Q, KONG Y Y. The research status and forecast of IPD in China[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016, 30(5): 12-17 (in Chinese).
[30] 馬智亮, 李松陽. IPD模式在我國PPP項目管理中應用的機遇和挑戰[J]. 工程管理學報, 2017, 31(5): 96-100.MA Z L, LI S 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IPD in PPP project management in China[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2017, 31(5): 96-100 (in Chinese).
[31] 高崧, 李衛東. 建筑信息模型的發展路線及一體化項目交付[J]. 工業建筑, 2018, 48(2): 8-15.GAO S, LI W D. BIM development route and integrated project delivery[J].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2018, 48(2): 8-15 (in Chinese).
[32] NGUYEN P, AKHAVIAN R. Synergistic effect of integrated project delivery, lean construction, and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on project performance measures: a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J]. Advances in Civil Engineering, 2019, 2019: 1-9.
[33] 馮曉科. BIM技術在裝配式建筑施工管理中的應用研究[J]. 建筑結構, 2018, 48(S1): 663-668.FENG X K. Application of BIM technology in assembly building construction management[J]. Building Structure, 2018, 48(S1): 663-668 (in Chinese).
[34] 田東, 李新偉, 馬濤. 基于BIM的裝配式混凝土建筑構件系統設計分析與研究[J]. 建筑結構, 2016, 46(17): 58-62.TIAN D, LI X W, MA T. Research on design and analysis of prefabricated concrete building component system based on BIM[J]. Building Structure, 2016, 46(17): 58-62 (in Chinese).
[35] ZHANG J Y, LONG Y T, LV S Q, et al. BIM-enabled modular and industrialized construction in China[J]. Procedia Engineering, 2016, 145: 1456-1461.
[36] 林樹枝, 施有志. 基于BIM技術的裝配式建筑智慧建造[J]. 建筑結構, 2018, 48(23): 118-122.LIN S Z, SHI Y Z. Intelligent construction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based on BIM technology[J]. Building Structure, 2018, 48(23): 118-122 (in Chinese).
[37] 薛茹, 王新淵, 史科. 基于建筑信息建模技術的裝配式建筑施工問題及對策分析[J]. 工業建筑, 2018, 48(11): 207-210.XUE R, WANG X Y, SHI K. Construction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 analysis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 based on BIM[J].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2018, 48(11): 207-211 (in Chinese).
[38] ZHAGN W, LEE M W, JAILLON L, et al. The hindrance to using prefabrication in Hong Kong’s building industry[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8, 204: 70-81.
[39] 張健, 陶豐燁, 蘇濤永. 基于BIM技術的裝配式建筑集成體系研究[J]. 建筑科學, 2018, 34(1): 97-102, 129.ZHANG J, TAO F Y, SU T Y. Research on BIM-based prefabricated building system[J]. Building Science, 2018, 34(1): 97-102, 129 (in Chinese).
[40] TAN T, CHEN K, XUE F, et al. Barriers to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BIM) implementation in China’s prefabricated construction: an interpre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ISM) approach[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9, 219: 949-959.
[41] 孫同謙, 徐崢. BIM標準對市政給排水專業的指導[J]. 中國給水排水, 2016, 32(4): 28-31.SUN T Q, XU Z. Guidance of BIM standard for municipal water supply and drainage professional[J]. China Water & Wastewater, 2016, 32(4): 28-31 (in Chinese).
[42] 高崧, 李衛東. 建筑信息模型標準在我國的發展現狀及思考[J]. 工業建筑, 2018, 48(2): 1-7.GAO S, LI W D. Some thoughts on the state-of-the-art of BIM standards in China[J].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2018, 48(2): 1-7 (in Chinese).
[43] 周洪波, 施平望, 鄧雪原. 基于IFC標準的BIM構件庫研究[J]. 圖學學報, 2017, 38(4): 589-595.ZHOU H B, SHI P W, DENG X Y. Research on BIM component library based on IFC standard[J]. Journal of Graphics, 2017, 38(4): 589-595 (in Chinese).
[44] 王茹, 宋楠楠, 藺向明, 等. 基于中國建筑信息建模標準框架的建筑信息建模構件標準化研究[J]. 工業建筑, 2016, 46(3): 179-184.WANG R, SONG N N, LIN X M, et al. Research on BIM component standardization based on cbims frame[J]. Industrial Construction, 2016, 46(3): 179-184 (in Chinese).
[45] MA Z, ZHANG D, LI J. A dedicated collaboration platform for integrated project delivery[J]. Automation in Construction, 2018, 86: 199-209.
[46] ELGHAISH F, ABRISHAMI S, HOSSEINI M R, et al. Integrated project delivery with BIM: an automated EVM-based approach[EB/OL].[2019-12-23]. https:// 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926580519312142.
Problems with and reflections on BIM forward design
TAO Gui-lin1, MA Wen-yu1, TANG Ke-qiang2, DU Yi-cheng3
(1. Chongqing Join Creation 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al Design Co. Ltd, Chongqing 400012, China; 2. Chengdu Architectural Design & Research Institute, Chengdu Sichuan 610000, China; 3. Guizhou Transportion Planning Survey & Design Academe Co.Ltd, Guiyang Guizhou 550016, China)
The BIM forward design has become widely recognized due to its advantages of simplifying the modelling process and reducing costs of labor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As the BIM technology has been increasingly popularized in the architecture industry in China for many years, the current BIM consulting model cannot satisfy the highly demanding application. Many challenges still remain when the BIM forward design was applied in the practical projects. This study performed a critical survey based on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from many projects and the literature investigation, so as to summarize the existing questions as follows: ① the lack of adaptive standards; ② domestic constraints; ③ underdeveloped related technical and industrial chai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entioned questions, several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such as: The drawing-oriented application is a transitional strategy. The effective solutions for developing the BIM forward desig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adaptive standard. The domestic BIM software and cloud platforms should be developed, and the integration of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should be reinforced. Not only is the strong support of technical required, but the innovation of management mode is needed to guarantee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BIM.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 integrated project delivery; forward design; review; project management
TU 17
10.11996/JG.j.2095-302X.2020040614
A
2095-302X(2020)04-0614-10
2020-02-14;
2020-04-13
13 April,2020
14 February,2020;
陶桂林(1986-),男,河南商丘人,中級工程師,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為BIM正向設計及其現實應用,建筑領域衍生式設計等。E-mail:taoguilin2940@126.com
TAO Gui-lin (1986-), male, intermediate engineer, master. His main research interests cover BIM forward design and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generative design of architecture.E-mail:taoguilin2940@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