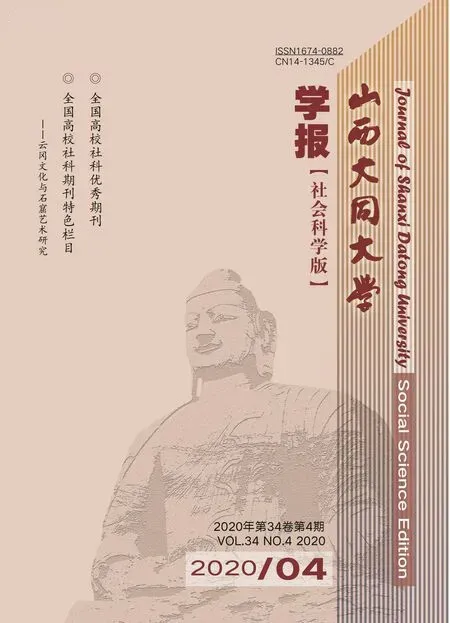老年人精神需求滿足與社會支持的關系機制研究
——基于中國老年社會追蹤調查(CLASS)的數據
李肖亞,孫金明
(廊坊師范學院社會發展學院,河北 廊坊 065000)
習近平總書記在改革放開40 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40 年來,我們始終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進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不斷改善人民生活、增進人民福祉。”隨著老年人口的增加,中國進入老年社會,未富先老的國情吸引了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如何應對來勢洶洶的“銀發潮”,保障老年人老有所依的民生福祉成為整個社會的共同焦點,老齡化和老年人成為學術研究的熱點問題。老年人的精神健康是老年人安享晚年的保障,是老年福祉本身的題中之意,也因此成為本文的關注點。
一、研究綜述
社會支持理論起源于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主要是社會學、社會工作、心理學等社會科學領域和精神病學、流行病學等醫學領域的研究主題。古典社會學大師涂爾干在其《自殺論》中即關注到社會支持對于降低自殺率的積極作用。[1]文化人類學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先突出了“社會支持網絡”一詞。[2]但社會支持理論的快速發展則是在20世紀60年代,并于20 世紀70 年代成為獨立的學科分支。作為一個跨學科概念,社會支持并沒有一個統一的概念定義,甚至對于社會支持應該包含的內容也是有分歧的。在社會學領域中,社會支持研究主要集中于社會資本、社會關系網和社會資源;在社會工作領域中,社會支持研究的對象主要有老年人、婦女、留守兒童、大學生等;在社會心理學和心理學領域,社會支持研究主要應用于抑郁癥、精神病、吸毒、慢性疾病等的治療。[3]
Cohen將社會支持看作一種幫助個體有效應對生活事件壓力的資源。[4]Cobb將社會支持定義為社交網絡中個體能夠感知被尊重、被關心的信息。[5]韋恩·韋登認為,社會支持指“來自個人社交網絡的多方面的援助與情緒支持”。[6]程艷敏認為“社會支持是個體所經歷的一切社會關系提供的有助于減輕個體心理應激反應、緩解個體心理緊張狀態、提高個體社會適應能力的各方面幫助”。[7]Lin 等將社會支持分為情感性支持和實質性支持(如財務支持、家務等)。[8]Morgan 等將社會支持分為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兩個方面。[9]邱海雄認為社會支持至少應該包括主體、客體、內容三個要素。[10]瞿小敏也認為應該對老年人社會支持的質量、內容以及老年人自身作為社會支持的客體對其自身所獲得支持的具體感受進行研究。[11]
部分學者認為社會支持的對象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有的學者則認為全體社會成員都有成為社會支持的對象的可能。筆者比較認同后一種觀念。彭揚帆研究了社會支持理論視域下失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援助,提出了政府、社會和社區三位一體的失獨老人心理健康救助機制。[12]韋艷將社會支持分為代際支持和社會交往兩個層次,其中代際支持主要包括生活照料、經濟支持和情感支持三個方面,最終得出代際支持中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以及社會交往對農村老年女性孤獨感具有顯著性影響的結論。[13]李建新將社會支持操作化為家庭支持和社區支持兩個變量,發現獲得更多家庭及社區支持的老年人對生活質量的評價也會更高。[14]吳敏則將社會支持量化為感知支持,即個體感知到而非實際獲得的支持,并得出社會支持絕對規模量的大小并不必然改善農民工的心理健康的結論。[15]瞿小敏將軀體健康和心理健康兩個變量作為中介變量來分析社會支持對老年生活滿意度的影響,并發現情感性支持可能比生活照料等實質性支持作用更大。[11]
結合現有理論與研究成果,本研究將社會支持視為一種能夠幫助個人提升社會適應能力的社會資源,將其分為物質支持和精神支持兩個層次,并在這一層次上展開研究。
二、數據來源和研究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大學組織的一項全國大型老年調查項目(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是一個全國性、連續性的大型社會調查項目。在全國范圍內以60 歲以上老人為調查對象,共獲得有效樣本11511 人。本文根據研究需要,從中剔除掉作為因變量的“精神狀態”變量的未填答個案,并為了提高研究的效度,進一步剔除掉職業變量的未填答個案,最終篩選出5991個樣本,其中的有效樣本為男性2979 人,女性2970 人,農業戶籍人口2205 人,非農業戶籍人口3782人。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基于SPSS24.0版本進行分析,主要的分析方法有統計描述和二分類logistic 回歸分析。其中統計描述主要是對目前老年人的精神狀況及不同種類的物質支持進行描述分析,主要有“積極狀態”和“消極狀態”兩種維度;均值分析主要用于不同群體特征的老年人的精神狀態的比較;二分類logistic回歸分析則用來探尋社會支持作為自變量和老年人精神狀態作為因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考察,并作為本文的主要討論內容。
因變量老年人精神健康狀態積極時取值為1,概率為P(0≤P≤1),老年人精神健康狀態消極時取值為0,其概率為1-P,其線性回歸方程為:

將上述方程做Logit變換,得


以上即為Logistic回歸模型。由上式可逆推出

變量經過對數化處理的logistic模型,能夠較好的滿足定量變量的建模要求。
(三)具體的數據處理 本文將老年人的精神狀況作為因變量,該變量是由共12 個陳述的總加量表得分計算出來的綜合分值。該量表包括“過去一周您覺得自己心情很好嗎”,“過去一周您覺得孤單嗎”,“過去一周您覺得不想吃東西嗎”,“過去一周您睡眠不好嗎”等12 個問題。每個問題設置沒有、有時、經常三個答案,分別賦值1 分、2 分和3分,每個被調查者的最終得分小于19 的話轉化為取值1,也就是“積極狀態”大于等于19的話轉化為2,也就是“消極狀態”。
自變量根據社會支持的定義,將已有的社會支持分為物質支持和非物質支持,其中涵蓋了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分類因素,精神支持包括由家人、親戚或朋友提供的精神層次的非物質的支持;物質支持則指由親友和親友之外的社會組織、社區或國家提供的金錢、實物、服務等方面的支持。其中,物質支持包含的問題有享受的社會保障待遇、接受的社會服務、社區提供的活動設施、是否受到老年優待等問題;精神支持包括同住人數、婚姻狀況、健在的子女數量和可求助親友數。享受的社會保障待遇由老年人每個月的各項社會保障待遇相加得到的總額再進行分類。可求助的親友數量是一個由6個問題組成的總加量表的得分轉化而來。
除因變量外,筆者還納入了學界認為的可能影響老年人精神需求滿足狀態的其他變量作為控制變量,有年齡、性別、婚姻狀況、教育程度和退休前的職業、戶籍這幾個變量。
(四)研究假設 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1、社會支持資源越充足,老年人精神需求越容易獲得滿足。
假設2、子女數量越多,精神需求越容易獲得滿足。
假設3、老年服務越豐富,精神需求越容易獲得滿足。
三、研究結果
(一)中國老年人精神健康狀況的現狀 統計數據顯示,中國大部分老年人的精神狀態比較積極,達到69.8%。但是考慮到中國老年人的基礎數額較大,精神狀態消極的老年人為數也不少。非農業戶籍老年人比農業戶籍老年人精神狀態更積極,前者比后者積極者比例多達15%,說明戶籍對于老年人晚年的精神狀態影響較為顯著。男性老年人比女性老年人精神狀態更加積極,前者比后者比例多11%,男性較女性更容易有積極的老年生活;在消極狀態人口中,男女比例則基本持平。從職業類型上看,不同職業類型間差距較大,國家和企事業單位的領導,其老年人精神狀態積極的比例最高,達到81.1%,遠高于農林牧漁從業者的56%,這也從側面印證了戶籍對精神狀態的影響,非農業戶籍老年人大部分集中于非農職業。從學歷上看,呈現出非常明顯的正相關態勢,學歷越高,精神狀態積極者比例越高,每個學歷層次之間相差了將近10個百分點。此外,年齡不同的老年人精神狀態也不同,60—69 歲的低齡老年人比70—79 的老人精神狀態積極的比例高接近4個百分點,70—79歲的老年人又比80—89 的老年人積極比例高接近3 個百分點。
從健在子女數量和可求助的親友數量上來看,可求助的親友數量多的老年人比可求助親友數量低的老年人精神狀態積極的比例高,沒有可求助親友的老年人消極的比例達50.2%,而可求助親友數量高的老年人消極比例僅為27%。健在的子女數量對老年人精神狀態的影響則體現在有無健在子女上,無健在子女的老人消極的比例達46.8%,而有健在子女的老年人中這一比例僅為30%左右。而健在子女的數量對老年人精神狀態的影響則不顯著,健在子女為多個和1個的老年人精神狀態差別不顯著。此外,婚姻狀況也對老年人的精神狀態有顯著影響,有配偶的老年人精神狀態積極的比例為75.1%,而無配偶老年人這一比例僅為56.6%,相差將近二十個百分點。
所利用的社會服務、擁有的社區活動場所和是否享受老年優待這些差異也會影響老年人的精神狀態。基本體現為可利用的服務越多、擁有的社區活動場所越多、可享受老年優待,老年人越傾向于積極的精神狀態。而在物質支持方面,影響最顯著的因素則是社會保障總額,社會保障額度高的比額度低的老年人精神狀態積極的比例高接近三十個百分點。
(二)老年人精神健康狀況的影響因素分析為了確定老年人的精神狀況和社會支持的關系,筆者按照社會支持的分類構建了三個模型,第一個模型納入控制變量和精神支持因素的變量,第二個模型納入控制變量和物質支持因素的變量,第三個模型納入前面所有類型的變量。通過三個模型確定各個變量的影響大小及在模型中的變化。
模型一可以分析出社會支持的精神支持方面對老年人精神狀態有顯著作用,精神支持的整體資源越豐富,老年人越傾向于積極的精神狀態。其中,婚姻狀況、可求助親友數和同住人數的顯著性水平都小于0.001,對老年人精神狀態有顯著性作用。具體表現在有配偶的老年人精神狀態消極的發生比是沒有配偶的老年人的一半;全模型中控制了其他影響因素后,有配偶的老年人精神狀態消極的發生比是沒有配偶的老年人的一半。可求助親友數為0 或1(得分小于等于6)的老年人精神狀態消極的發生比是可求助親友數大于3 的老年人的3.1倍;在控制了其他影響因素的全模型中,可求助親友數為0或1的老年人精神狀態消極的發生比是可求助親友數大于3 的老年人的3.1 倍。從同住人數上看,獨居老人精神狀態消極的發生比是同住人數5 人以上的老年人的1.6 倍;控制了其他影響因素后的全模型中獨居老人精神狀態消極的發生比也是同住人數5 人以上的老人的1.6 倍。健在子女數量對老年人精神狀態的影響則不顯著,有0個健在子女的老年人精神狀態消極的發生比僅是有3個及以上健在子女的老年人的1.1 倍;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影響后這個數值仍然是1.1。考慮到健在子女數量和可求助的親友數可能有共線性,在剔除可求助的親友數量這一變量后重新進行Logistics回歸分析,模型一中健在子女數量的顯著性水平為0.558,全模型中健在子女數量的顯著性水平為0.546,仍不具顯著性作用。在全模型中同時納入健在子女數量和可求助親友數的交互作用,交互作用亦不具顯著性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佐證了李建新、韋艷之前的研究結論,即有非親屬交往對象和交往頻繁的老年女性孤獨感大幅下降,來自子女的社會支持會隨著子女數量的減少而減少。[13][14]這個結論與賀寨平的研究結果不是很一致。[16]
模型二顯示的是社會支持的物質支持層面與老年人精神狀態的關系。社會保障待遇總額每月1000 元以下的老年人精神狀態消極的發生比是社會保障待遇每月3000元以上的老年人的1.5倍;在控制了其他影響因素的全模型中,社會保障待遇總額每月1000 元以下的老年人精神狀態消極的發生比是社保待遇每月3000 元以上的老年人的1.5 倍。享受老年優待的老人精神狀態消極的發生比是不享受老年優待的老年人的0.88倍,在控制其他變量影響因素的全模型中這一數值保持不變。在社會服務方面,沒有社會服務的老年人精神狀態消極的發生比是接收3 項及以上社會服務的老年人的1.2倍;在控制其他變量影響因素的全模型中,這一數值增長到1.7。有0—1項社區活動場所的老年人精神狀態消極的發生比是有4項及以上社區活動場所的老年人的1.3 倍;在全模型中控制其他影響因素后這一數值降低到1.2。
模型二的Nagelkerke R2較模型一要小,說明社會支持的物質支持層面的因素對老年人精神狀態的影響要小于精神層面。其中,僅有社會保障總額這一因素的顯著性水平小于0.001,其他變量的影響都不顯著。這個結論在一定程度上和其他學者的發現并不一致。[14]筆者進一步分析發現,社會服務等其他變量影響并不顯著的原因在于,目前中國針對老年人的專門服務和其他物質支持仍然太少。如下表所示,在老年飯桌、日托、心理咨詢等老年服務中,91.4%的老年人使用過0項,剩下的則是使用過1—3項,使用過4項以上的老年人數則為0。在老年活動場所方面,35%的老年人沒有專門的社區活動場所,剩下的43.5%的老年人有1—2 項活動場所。同時,有62.7%的老人為享受過老年優待。
在控制變量中,所有的模型都顯示性別、年齡、宗教信仰、戶籍這些變量對老年人的精神狀態沒有顯著性影響,學歷和職業的顯著性水平都小于0.05,對老年人精神狀態具有顯著性作用。具體表現為學歷越高,老年人精神狀態消極的發生比越低,學歷為文盲的老年人精神狀態消極的發生比是學歷為大專及以上老年人的1.688 倍;從職業上來看,職業為國家機關和企事業單位領導人的老年人精神狀態消極的發生比是無業老年人的0.7倍。

表1 老年人物質支持現狀
四、研究結論
社會支持理論認為,個體周圍的社會資源所提供的精神或物質支持有助于個人降低心里緊張狀態,減輕個體心理壓力,更好地適應社會生活。通過實證分析,結合社會支持的相關理論,我們得出如下結論:第一,社會支持資源越豐富,老年人的精神狀態也更積極,筆者的第一個研究結論得到了實證驗證。無論是物質支持還是精神支持都顯示出這樣的作用方向。物質支持和精神支持中的任何一種支持資源的豐富都有利于老年人的精神狀態向積極的方向發展。
其次,在具體的支持類型中,精神支持層面作用更顯著的變量是“可求助的親友數”和婚姻狀態。能夠見面聯系的親友數越多,能夠提供幫助的親友數越多,老年人的精神狀態越積極。而健在的子女數量在這個問題上并不具有顯著性影響。
再次,在所有類型的物質支持資源中,社會保障資金總額的影響最為顯著,當下的中國老年人受國家的社會保障政策影響更大。老年社會服務和老年活動場所這些相對正式的支持類型則影響不顯著。我國在為老服務方面還相對薄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同時,在分析過程中我們發現,中國老年人的精神狀態呈現出顯著的城鄉差距,契合了我國的城鄉二元化格局。老年人整體上精神狀態積極人數遠大于消極人數,但同時亦存在大量缺乏社會支持的老年人,處在物質和精神雙重匱乏的境地。物質支持中起最主要作用的社保待遇在城鄉之間的差距較大,調查數據顯示仍有不少老年人沒有享受任何社保待遇,與此同時部分老年人的每月社保總額加起來接近10 萬(包括退休金)。這種差距深層次地影響著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和身心健康。
根據研究結論,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議:一、加速統籌城鄉之間、地域之間、行業之間的社會保障政策,健全農村老年人救助機制,盡快實現應保盡保的社會保障政策的全國統籌。二、加速推進社會工作隊伍建設,尤其是農村社會工作,社會工作者介入獨居、喪偶和失獨老人的精神需求。在老年服務領域,深化老年社會服務內容,創新老年社會服務形式,使更多的老年人有機會使用更專業的老年服務。
本研究還有以下不足之處:一、對于社會支持的操作化定義,限于篇幅所限,僅從社會支持的物質和精神層面來測量,沒有關注老年人的個人老化態度和主觀上對社會支持的利用度。二、在具體的變量選擇上,僅考察了健在子女數量這一因素,而沒有納入具體的子代對親代的支持狀況;在社會服務的考察上也是從社會服務的量上進行測量,沒有能深入社會服務的微觀層次,測量具體的老年社會服務差異。本研究計劃進一步深化這兩個變量的測量,探索社會支持與老年人精神健康狀況的微觀作用機制,以促進實現老年人安享晚年、老有所樂的老年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