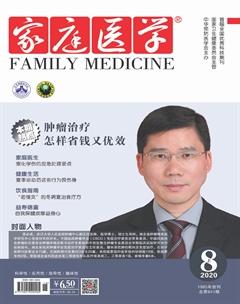三陰性乳腺癌治療初現曙光
羅勤
近年來,隨著診療技術的不斷完善,乳腺癌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質量有了顯著改善。唯獨三陰性乳腺癌因缺乏有效的“治療靶點”,成為乳腺癌治療的一道世界性難題。最近,復旦大學腫瘤醫院的一項針對三陰性乳腺癌的重要研究成果在腫瘤學頂尖期刊《Cancer Cell》(《癌細胞》)發表,影響很大。該院專家團隊歷時五年聯合攻關,繪制出全球最大的三陰性乳腺癌隊列多組學圖譜,并提出三陰性乳腺癌分子分型基礎上的精準治療策略,這意味著既往缺乏有效療法的三陰性乳腺癌有望獲得“分類而治”。
三陰性乳腺癌更兇險
乳腺癌的病理檢查結果中有4個指標最為重要,即雌激素受體(ER)、孕激素受體(PR)、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ERBB2)、腫瘤細胞的增殖指數(Ki67)。 這4個指標檢查結果的不同組合,形成了乳腺癌lumina A(腔面A)、lumina B(腔面B)、HER-2陽性和“三陰性”四個亞型。其中三陰性乳腺癌之所以稱為“三陰”,是因為這種乳腺癌的雌激素受體、孕激素受體和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2,三個主要治療靶點均為陰性。
抗癌藥物要發揮作用,必須在腫瘤細胞上找到作用的“靶子”,這個“靶子”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藥物靶點。由于三陰性乳腺癌缺乏雌激素受體(ER)、孕激素受體(PR)和人表皮生長因子受體(HER-2)這三個治療靶點,內分泌治療和針對Her-2的靶向治療均無效,患者往往只有化療“一條路”。 臨床上相當一部分患者承受不了化療的毒副作用帶來的痛苦,且因“盲目”化療容易產生耐藥,3年后的復發率高達40﹪~50﹪;而一旦發生遠處轉移則幾乎不可治愈。更為矚目的是,三陰性乳腺癌在亞洲年輕女性群體中處于高發態勢,發病率占據所有乳腺癌15﹪~20﹪。因此,三陰性乳腺癌堪稱乳腺癌中最“毒”的類型,也是乳腺癌治療面臨的一道世界性難題。
三陰性乳腺癌不是單一的類型
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三陰性乳腺癌并不是單一的類型。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邵志敏教授團隊釆用高通量基因芯片和測序技術,對465例三陰性乳腺癌標本展開研究,繪制出全球最大的三陰性乳腺癌隊列多組學圖譜,并通過對龐大基因數據分析,證實三陰性乳腺癌可分為不同的亞型,且不同亞型患者存在生存期差異,對不同治療方案敏感性也不同。
根據這些亞型表面蛋白的不同特征,邵志敏教授團隊將三陰性乳腺癌分類并命名為4個不同的亞型:免疫調節型、腔面雄激素受體型、基底樣免疫抑制型、間質型。這是國際上首次基于多維大數據系統提出的三陰性乳腺癌分類標準。為尋找三陰性乳腺癌的治療靶點指明了新的方向。
三陰性乳腺癌分型的重要意義
邵志敏教授團隊根據三陰性乳腺癌的不同亞型進一步分析,破除了以往三陰性乳腺癌治療“方向模糊”的困難,有助于醫學專家“有的放矢”地選擇治療方案。
比如免疫調節型三陰性乳腺癌,其癌細胞周圍有大量淋巴細胞,提示可能對免疫治療敏感;而在腔面雄激素受體型乳腺癌細胞有明顯的HER-2基因突變,提示靶向治療可能有效。
因此,對三陰性乳腺癌的不同亞型的分析,為科學家尋找相關治療靶點指明了方向,有助于提高三陰性乳腺癌的療效。
我國三陰性乳腺癌呈現獨有特征
過往研究已經證實,我國乳腺癌發病與西方國家有明顯不同特征。例如,我國乳腺癌在不同年齡階段發病率呈現“雙峰”現象,兩個發病高峰分別在45~55歲和70~74歲,不同于北美國家持續增長型或東歐國家的平臺維持型。我國乳腺癌平均發病年齡為51歲,比歐美囯家低10歲左右。邵志敏研究團隊還發現,中國乳腺癌患者中PIK3CA突變頻率與西方數據庫相當,而PIK3R1基因突變頻率明顯高于西方人群。
在三陰性乳腺癌的研究中,邵志敏研究團隊將標本數據與美國的相關數據庫進行對比,結果發現我國三陰性乳腺癌有自己獨特的特征。例如PIK3CA基因突變,在我國三陰性乳腺癌患者人群中的比例要顯著高于美國。表明三陰性乳腺癌不僅有獨特的亞型,且呈現出一定的區域差異。這將為后續開展針對國人三陰性乳腺癌的藥物研發、臨床試驗提供數據和證據的支持。
研究成果正積極向臨床應用轉化
目前,邵志敏研究團隊正積極將研究成果向臨床應用轉化。根據前期實驗結果發明了臨床實用的三陰性乳腺癌分子分型方法,結合乳腺外科正在大力推行的精準醫學基因檢測,可以為每一位患者進行精確的分子分型并鑒定藥物靶點,從而有望在臨床中實現精準治療。
據悉,復旦大學附屬腫瘤醫院開展了針對難治性三陰性乳腺癌的精準治療的臨床研究——FUTURE研究,該項目獲得倫理委員會的批準立項,試圖在三陰性乳腺癌中根據患者各自基因變異位點的特征,精準地分成4型、7個不同的靶向臂。力爭盡快研發針對三陰性乳腺癌不同靶點的藥物,最終實現對三陰性乳腺癌患者的“分類而治”,讓患者盡早獲得精準且能明顯提升療效的治療方案。對于化療后耐藥的晩期三陰性乳腺癌患者而言,這項研究將帶來生機和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