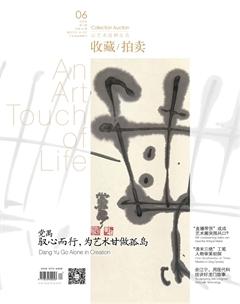在聆聽中以聲博物
輪奐 易隸



聲音,無處不在,但以聲音作為一種獨立的藝術形式,對許多人來說,似乎還是陌生的概念。實際上,藝術除了視覺上的“觀賞”,聲音可以增添作品“聆聽”的感官維度。不僅如此,聲音也是承載歷史記憶的重要載體,可以從聽覺上喚起觀者的回憶與心理共鳴。隨著藝術形式在邊界上日益消弭,聲音藝術也開始被博物館納入展示甚至收藏的范疇,甚至出現一些以聲音為主題的博物館,讓展覽不再是單純的視覺呈現,而是“以聲博物”,用耳朵的傾聽找回原始的天籟。隱匿在維新學堂中的聲音博物館
廣州老城鬧市,坐落著一座青磚黛瓦的古建筑群——萬木草堂,這里曾是中國近代維新派創辦的著名學堂,聚徒講學,宣傳改良主義思想,成為戊戌變法策源地。為此,建筑得以完整保留,在鋼筋混凝土的現代建筑包圍中,顯得獨樹一幟。偶然間走進這座極具嶺南特色的院落,會瞬間覺得別具洞天,透過天井仰望,老樹婆娑,偶然間的幾聲鳥鳴,讓人從車水馬龍的喧囂中抽離,尋得久違的靜謐心境。
鮮為人知的是,萬木草堂不僅是維新學堂的紀念地,這里還是中國首家聲音博物館。不過,它并非一座收藏、展示聲音設備的博物館。五年前,當代聲音藝術家陳弘禮相中了這處獨具嶺南特色的院落,引入當代聲音藝術,創立聲音博物館,打造成一座展示、探索聲音藝術空間。
聲音博物館的參觀之旅,由一扇漆黑的大木門開啟,進入后,一旁的工作人員會遞上耳機,隨即跟隨指引步入展廳參觀。萬木草堂內部空間在保留原有格局的基礎上被改造成展示聲音藝術的空間,這里沒有懸掛或展柜陳設的藝術品,而是設置了影像設備,當觀者戴著耳機步入特定的場景時,耳旁便會響起與場景相呼應的聲音。每一處都經過巧妙的設計與布置,在這里,一步一景,移步換聲。作為觀眾,不妨靜下心境,在聆聽中體會何為聲音藝術。
聲音藝術,既前衛又古老
需要普及下的是,聲音藝術這一名詞實際上由英文“Sound Art”翻譯而來,通常用來指稱關注聲音與聆聽的藝術分支,其根源部分來自音樂領域,部分來自于建筑、雕塑、裝置等視覺藝術領域。它最早出現在20世紀末期,最早由加拿大作曲家、聲音藝術家丹·蘭德( Dan Lander)正式提出。聲音藝術是以廣義上的聲音(包含傳統意義上的噪音與樂音)為主要創作媒介,主張尊重聲音本體,重視主動聆聽而非“創作”的一種藝術類別。聲音藝術家通常利用錄音設備到自然界或社會生活中收集各種聲音素材,并對其進行剪輯處理,結合多媒體技術進行展示,除了作為聽覺的感官元素加入到作品中,也有專門創作聲音作為主題的裝置作品。在國外一些博物館、美術館,已策劃了不少探討聲音藝術的展覽,如2001年紐約惠特尼美術館的“比特流”(Bitstreams)、2002年巴塞羅那當代美術館的“聲音的過程:新聲音地理展”(Sonic Process:ANew Grogrcphy of Sound)等,聲音藝術早已被視為一種獨立的藝術形式。
此外,隨著新媒體藝術的興起,還有一些結合景觀、環境藝術的聲音作品,也被稱之為聲景藝術。藝術家選擇在特定的空間或場景下為觀者呈現特定的聲音,依此帶來視覺與聽覺的交互體驗。這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聽雪敲竹”“雨打芭蕉”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可以說,聲音是理解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也是構建意境十分重要的元素。古人熱哀以聲傳情,以情潤聲。因此,聲音藝術既古老,又前衛。
以聲博物
因此,以古建筑作為載體,將聲音博物館建在萬木草堂中,正是這座博物館的一大特色。談及打造這座博物館的初哀,創始人陳弘禮表示最初起源于鄉愁:“我從小對聲音非常有興趣,許多年后,一件很震撼的事情是我回到自己的家鄉,為了方便交流,大家都說普通話,鄉音不見了。我想把鄉音留住,也激發了我在聲音藝術領域的探索。”陳弘禮從古代經典中汲取靈感,有感于莊子《齊物論》“人籟、地籟、天籟”的聲音哲學,以及《禮記樂記》對“聲”“音”“樂”的闡述而獲得啟發,將聲音歸納為自然之聲、社會之聲、人文之聲三大部分。進而希望通過“以聲博物”“以聲傳情”“以聲尋史”的方式,讓聲音博物館與萬木草堂的特色與功能完美融合,前衛的聲音藝術與古老的傳統文化可以實現碰撞、交融。“我希望通過聲音的藝術,幫助大家一同想象當時梁啟超、康有為在這里辦學的情景、生活的狀態。大家耳機中聽到的朗朗讀書聲、鼓聲、粵劇聲都是在嘗試還原當時的情境。”在陳弘禮看來,這是一場天地人文的對話,也是一場傳統與現代的對話。通過創意+文化+科技的方式,賦予傳統新的生命力。
在展陳設計上,聲音博物館運用自己開發的手機小程序巧妙布置了“移步換聲”的聲景藝術作品《萬物有聲》,包括六個聲音景觀:物語、草堂懷古、雨打芭蕉、碧澗談、竹林聽風、憶故人。觀者掃碼二維碼戴上耳機,漫步到相應的場景就會自動切換到這六種稀世之音:走至井邊,還會智能觸發出汨汨水聲;一手憐取芭蕉葉,雨點擊木聲特定之音入耳畔……聲音博物館還在建筑中設置了聲音劇場,定期邀請詩人、畫家、音樂人等各界人士前來雅聚,共同探索聲音藝術與傳統文化的互通。
結合新技術,聲音博物館還自主研發并擁有知識產權的聲景交互系統,提供全新的聲景藝術交互體驗藝術展。如聽見《清明上河圖》,與其他公共空間聯手,與戶外建筑結合,呈現世界首次有聲音設計、可聲音交互的《清明上河圖》,整個展覽一共設有十個場景,每個場景有幾十種聲音,每個人在同一個場景會聽到不同的聲音。采用全息聲體驗,在藝術展不同區域會發出聲音裝置,帶來交互體驗效果。
總之,與其說萬木草堂是一座博物館,更確切地說是一座以多學科、多角度跨界搭建的共享學術知識、藝術交流的平臺。保存老北京今昔的聲音總站
史家胡同的“館中館”
無獨有偶,位于北京東城區朝陽門街道史家胡同,也有一家聲音博物館。在史家胡同博物館這座小型博物館里隱藏著一個館中館,是一間只有幾平方米的小隔音房間,這個稱呼為“胡同聲音”的小屋子就是聲音總站的開始,當時的叫法是“聲音博物館”。
這里是聲音總站的第一站,由老北京叫賣開始的。比如:只有老北京才有的鴿哨聲、吆喝聲、響器聲;平房大院里棗兒的落地聲、公共汽車售票員的報站聲等。坐在四合院里,還可以聽到賣各種各樣吃的、用的以及提供各種服務的,比如理發的、算命的、看病的、收舊貨的。每一個買賣都有自己獨特的叫賣吆喝特點,有的叫有的唱,還有的用特別的響器。史家胡同博物館的游客可以單獨聆聽聲音,也可以根據季節選擇聽老北京環境聲音。館中關于老北京的聲音已有200余種,記錄著北京老胡同的今昔。
聲音總站是由藝術家秦思源發起的一個長期的、多面向的藝術項目,始于一個僅以聲音探索北京歷史的計劃,在這個計劃里收錄了那些已經消逝但仍被北京的居民所銘記的聲音。
史家胡同博物館,和秦思源的家庭也有著密切的關系。這個地方曾是秦思源的外祖母凌叔華(清末進士凌福彭的女兒)的嫁妝。外祖母凌叔華是與林徽因、冰心齊名的“民國才女”,外祖父陳源(筆名陳西瀅)則是著名的魯迅論敵,兩人曾爆發過多次筆戰。母親陳小瀅在英國廣播公司國際部擔任記者時,因為一次采訪結識了愛人——英國著名漢學家秦乃瑞,曾多次以中英友好人士身份來華訪問,曾受到周恩來總理的接見。母親為他取名為秦思源,一是為紀念外祖父陳源,二是有飲水思源的寓意。秦思源雖然出生在英國,但從小就喜歡中國文化,大學所學專業也與中國有關。2002年之后,秦思源就搬到中國定居了。后來母親陳小瀅女士將這所宅院的房屋產權轉讓給街道辦事處用于公益,建立了胡同博物館。
喚醒情感和記憶的聲音
實際上,聲音總站,更像是一座“流動”的博物館,除了以史家胡同博物館為基地,它還與其他藝術機構進行合作,舉辦展覽與活動。
秦思源在2004年策劃過的一個中英藝術家跨界項目《都市發聲(Sound and the City)》。這個項目由英國使館文化處發起,秦思源作為藝術總監邀請了英國多位藝術家以及中國的藝術家參與,共同開展了一系列活動探索、記錄生活里的聲音環境。當時史家胡同博物館籌備期間的規劃方向是做老北京題材的博物館,參加顧問會議時秦思源建議做一些關于老北京聲音的內容。為了研究方案,秦思源重聽了在2005年策劃的“都市發聲”項目的錄音內容,其中一些很普通的日常聲音勾起了當時的感受。秦思源發現聲音這個媒介的力量,就像一個時間機器,能夠喚醒一個人的身體記憶。從而提議博物館用聲音表現北京歷史,讓觀眾能聽到各種以前的聲音。
當聲音總站第一站落地時,秦思源說它沒有個開幕日期,它已經開了,只是它比較小,“未來不是說某個點越來越大,而是它越來越分散,它的社會性在壯大”。
秦思源認為,聲音總站對自己來講是一個藝術創作,還是一個個人的藝術作品、個人行為。在秦思源的體驗中,他驚訝地發現,因為聲音可以作為一個特別有豐富可能性的媒介。所以他坦承,作為一個聲音收集者,自己并不癡迷于聲音本身,他不是聲音的發燒友,他喜歡的是聲音對記憶與情感的喚醒,從而引發更多人的共情互動。
秦思源更注重從自己的視角出發,他希望是用他的主動性來做,平時會在自己的微博上用Vlog的形式發布一些自己拍的視頻。他希望是自己主動帶來的關注,然后公眾一起參與進來。秦思源認為聲音總站這個項目是需要公眾參與,它才能有一個存活的意義。聲音是關于公共意識的,也是關于社會,同時因為這些聲音的存在,才會產生公共的興趣。
最真實的聲才最感動
“我不是來展現那些聲音,而是調動社會來錄這些聲音。”秦思源認為聲音總站這個項目核心的可能性是社會互動,打開了這個社會互動,就是說和社會公眾一起去打造項目的內容和概念,這也是秦思源直堅持的興奮點。
秦思源錄制過很多種聲音,包括北京和和藏區理塘地區,還將在中國其他地方收集聲音。在他看來,北京這座城市的核心魅力,就是它的豐富性。在這座城市里,什么樣的人都有,干什么樣的事都有,對秦思源來說有種臥虎藏龍的感覺,而這種感覺就是秦思源特別喜歡的北京特色,也是為什么最后會選擇扎根的原因。秦思源認為,正是這樣的豐富性,讓北京擁有了真正的內容,相對于其他城市來講更有它的真實感。這樣的豐富性,正是最寶貴的東西。
其實老北京的聲音并不好收集,為了將真實的聲音進行細致的還原,秦思源講究得很,曾經為了錄制最地道的鴿哨聲,秦思源和他的團隊前后錄制了小半年的時間。
秦思源解釋:鴿哨分不同材質,鴿哨的高低音很豐富,聲音有很大區別。而且群鴿子在空中盤旋,和幾只鴿子的鴿哨,也不樣。這些真實的聲音能夠打動他,可以帶他回到20多年前的北京老胡同。所以他要留住這種真實。
或許,聲音總站,最能詮釋這座前衛的聲音博物館,將來也會成為一個保存著更多記憶和感情的聲音空間。
(編輯/雷煥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