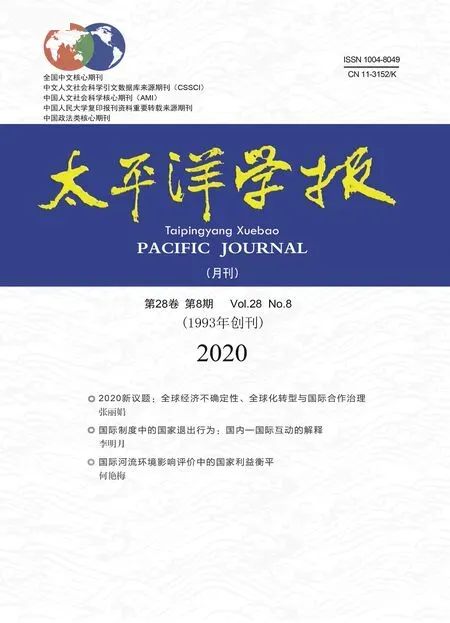國際制度中的國家退出行為:國內—國際互動的解釋
李明月
(1.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湖北 武漢 430073)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國際社會日益結成一張制度網絡,其中包括各種國際組織、雙邊和多邊條約及其他制度安排。雖然大多數國家仍然處在當初加入的國際制度中,但也發生了一些國家退出或威脅退出國際制度的現象。近年來,英國退出歐盟,部分非洲國家退出國際刑事法院,美國自特朗普政府執政以來接連宣布退出《巴黎協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伊朗核協議和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使得國家的“退群”行為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作為諸多國際制度的創建者和主導者,美國的退出尤其成為新的話題和研究熱點。那么,國家為什么會退出先前加入的國際制度?而這其中還隱含著一個深層問題,即國家的國際制度行為為何會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并不是國際關系學者通常所關注的從游離到參與的改變,而是從參與到退出的改變。本文努力探索上述問題,并力求做出有價值的解釋。
一、“退出”現象及既有解釋的不足
國際制度是規定行為的職責、限制行動及影響行為者期望的持久且互為聯系的一組正式或非正式的規則。(1)Robert Keohane eds.,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3, 轉引自蘇長和:“重新定義國際制度”,《歐洲》,1999年第6期,第24頁。國際組織和國際條約是國際制度的基本組成要素,也是國際制度的承載平臺和表現形式。1945年至2014年間,政府間國際組織中發生的成員國退出現象達200余次。(2)Inken von Borzyskowski and Felicity Vabulas, “Hello, Goodbye: When Do States Withdraw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4, No.1, 2019, p.339.如果將其他形式國際制度中發生的退出行為計算在內,或考慮國家的暫時退出與部分退出行為,那么將是更為龐大的數據。由于各類國際制度數量的日趨增長和國家參與國際合作的絕對數量優勢,國際制度中的國家退出行為仍不是常態。本文之所以要研究國際制度中的國家退出行為,是因為“退出”是國際社會的重要現象,然而有關國家退出國際制度的系統性研究仍然較少。
1.1 “退出”的概念界定
“退出”被認為是一個國家根據條約(包括創建政府間國際組織的基礎條約)中規定的退出條件終止其成員資格的行為。(3)Laurence R. Helfer, “Exiting Treaties”,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91, No.7, 2005, pp. 1579-1648.若當事國單方行使退出權,而其他當事國在一定時間內不提出反對,那么該條約對退出國來說已經終止,但對其他當事國來說,仍繼續有效。(4)《維也納條約法公約(1969)》第56條用兩種方式表達“退出”,即“單方解約(denunciation)”或“單方退出(withdrawal)”。其中,單方解約既適用于雙邊條約,也適用于多邊條約;單方退出只適用于多邊條約。參見United Nations,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y 1969”, May 23, 1969;銀紅武著:《條約退出權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也就是說,“退出”是一種單邊行動,并不需要其他成員國的同意和支持。但是,國家首先要向組織和組織內的其他成員國告知退出,然后再根據國際制度的退出程序和時間表完成退出的形式化要求。例如,《里斯本條約》第50條對成員國退出歐盟的主要程序作出了規定:退出國必須正式通知歐洲理事國其“脫歐”意向,之后歐盟必須與退出國就退出歐盟的具體細節進行磋商談判并締結一項協議,協議生效后(或如果協議不能生效,則自退出國發出通知之日起兩年后),條約將不再適用于退出國。(5)Official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Journal, “Consolidated Versions of the 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and the Treaty on the Function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ropean Union, C115, May 9, 2008.
一般意義上理解的“退出”,是相對弱勢、被秩序主導國質疑合法性,以及處于邊緣地位或具有離心力的國家迫于形勢作出的選擇,如本來就頗具離心力的英國作出退出歐盟的決定。(6)任琳:“‘退出外交’與全球治理秩序——一種制度現實主義的分析”,《國際政治科學》,2019年第1期,第88頁。從歷史上看,主導大國頻繁退出國際制度的現象較為少見。傳統觀點認為,主導國是現存國際秩序中最大的既得利益者且對現狀滿意,它們通常運用保持、吸收和驅逐戰略維護其地位;新興國家因在當前的國際秩序中缺少制定規則的權力,現存制度規范并不能很好契合自身的利益需求,而被視為既有秩序的挑戰者,往往通過選擇性或部分退出、呼吁和革新來改變現狀。(7)See Lauchlan T. Munro, “Strategies to Shape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Exit, Voice and Innovation versus Expulsion, Maintenance and Absorp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39, No. 2, 2018, p. 310;汪海寶、賀凱:“國際秩序轉型期的中美制度競爭——基于制度制衡理論的分析”,《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第59頁。然而,美國近年來接連退出或威脅退出的行為似乎為主導國退出國際制度提供了更多例證,而被視為崛起國的中國在國際制度中表現出的積極、開放和包容態度與之形成鮮明對比。可見,“退出”并不是弱勢國、崛起國、主導國或其他某一類型國家所特有的國際制度行為,任何國家都有可能退出。
“退出”作為一種國際制度行為有時并不是真實和徹底的,國家有時會策略性地選擇威脅退出,來改變自身的不利處境或獲取額外收益,即國家威脅所參與的國際制度,如果不改變對本國的不利狀況,就將退出該制度。如特朗普總統就曾公開威脅退出世界貿易組織,除非其改變對待美國的方式。(8)“Donald Trump Threatens to Pull United States Out of the WTO If It Does Not ‘Shape Up’” The National, August 31, 2018.無論威脅退出國最終是否退出國際制度,只要制度內的成員國接受了該國的利益訴求,該國的預期目標就實現了。威脅退出是一種策略性欺騙,有其特殊功效,但并不是真的退出,而是通過威脅退出達到重建國際秩序的目標。(9)任琳:“‘退出外交’與全球治理秩序——一種制度現實主義的分析”,《國際政治科學》,2019年第1期,第85頁。威脅退出和實際退出都能起到一定的震懾作用,因而成為國家用來表達對條約體制或國際組織不滿的重要方式。
1.2 退出行為為何重要
雖然“退出”并不是國際制度中的普遍現象,但會對國際合作、退出國家和存留國家的政策、某一領域內國際制度的未來發展、國際組織的經費和未來政策行動等產生重要影響。國際制度既有其加入條件的規制,又有退出的自由權利,這一方面體現出其開放性,另一方面也體現了尊重國家自主權的特性。(10)馬英杰、張紅蕾、劉勃:“《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退出機制及我國的考量”,《太平洋學報》,2013年第5期,第26頁。可見,國際制度中退出條款和退出機制的設計具有一定積極意義。首先,退出行為為國家在現有合作形式之外創造新的合作形式提供了可能,無論國家大小強弱,都能夠通過退出策略表明自己對國際制度的態度并增加發言權。二十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美國相繼退出國際勞工組織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該行為導致對上述組織喪失支持和資金資助遲滯,迫使組織改變自身行為,隨后美國又加入了上述組織。其次,退出行為還是國家對國際制度不合理和低效率的回應與質疑,國家從國際制度中退出的行為可推動國際制度的發展。例如,不少非洲國家認為國際刑事法院存在司法偏見,繼布隆迪于2016年10月退出后,南非和岡比亞也宣布退出,納米比亞和肯尼亞等非洲國家則表示正在考慮退出國際刑事法院的可能性。(11)近年來,國際刑事法院多次受到司法偏見的指責。2016年10月18日,布隆迪因反對國際刑事法院關于布隆迪存在“大量侵犯人權的暴力行為”的指控,成為第一個宣布退出國際刑事法院的國家。10月21日,南非政府因無法執行國際刑事法院的相關規定,正式啟動退出程序。10月25日,岡比亞認為國際刑事法院在戰爭罪指控方面存在偏見,也宣布將退出國際刑事法院。“不滿‘雙重標準’岡比亞宣布退出國際刑事法院”,新華網,2016年10月27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10/27/c_129338759.htm。成員國怨聲載道和集體退出的趨勢可能會促使國際刑事法院做出一定的變革。最后,退出行為可使國家在國際制度約束與行使國家主權之間得到緩沖地帶。英國退出歐盟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要換取對英國主權的“完全控制”,而不必再繼續向歐盟“讓渡”立法權等國家主權。(12)“英國‘退歐’風波后的國家中心主義”,中國社會科學網,2015年12月21日,http://mil.cssn.cn/dzyx/dzyx_llsj/201512/t20151221_2790493.shtml。
國際制度中的國家退出行為雖然有助于成員國尋求新的合作形式,創造新的利益格局,更好地維護自身利益,但也可能對國際合作、全球治理和國家間關系造成不良影響。國家之間的復合相互依賴使很多地區性和全球性問題只能通過國際制度合作解決,國家退出國際制度可能會對某一問題領域的治理進程造成阻礙。在國際制度中,弱勢國家退出的影響可能是有限的,但秩序主導國退出的影響則是系統性的,可能危及世界格局和全球治理秩序的穩定。例如,德國和日本先后從國際聯盟中退出,造成了國際體系的混亂,并最終引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制度退出行為已經對經濟貿易、安全合作和全球治理諸多層面的國際秩序構成挑戰。(13)汪海寶、賀凱:“國際秩序轉型時期的中美制度競爭——基于制度制衡理論的分析”,《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第57頁。因此,分析國家為何以及何時會退出國際制度,能為評估全球治理進程和國際秩序維護提供一種新的視角。
1.3 既有解釋的不足
在國際關系領域中,國際制度研究大多關注國際制度為何以及如何形成,為什么國際制度重要以及哪些國家在國際制度設計中最為重要,關于國家退出國際制度的一般性研究并不多見。要探尋國家退出國際制度的深層原因,必須對其鏡像問題,即國家為什么參與國際制度進行分析。新現實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者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國際制度能為其成員國帶來高于不參與狀態的合作收益。(14)新現實主義者雖然強調相對收益,但也沒有否定絕對收益在國家選擇參與國際制度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參見劉宏松:“對國家參與國際制度的另一種理性主義解釋——國際制度中‘自為其事’權力理論書評”,《國際論壇》,2006年第5期,第13-18頁。新自由主義者認為,國際制度可以降低交易費用,提高良好聲譽的價值,增加決策和行為的透明度,減少不確定性等,參見[美]羅伯特·基歐漢著,蘇長和等譯:《霸權之后——世界政治中的合作與紛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8-133頁。按照這種邏輯,國家退出國際制度是因為國家參與的成本已經超過了其所獲得的制度紅利,不符合國家的利益。但是,對于這種收益變化導致退出的結果,新現實主義者和新自由主義者給出了不同的解釋。
新現實主義認為,擁有更強大軍事和經濟實力的國家可以更工具化地利用國際制度,國際體系中權力結構的變化會導致相對收益的變化,從而導致國家退出國際制度。一戰后,德國實力增長帶來的歐洲權力結構變化的確是其退出國際聯盟的重要原因,但是國際制度中的很多退出現象并不能用權力結構變化來解釋,如英國退出歐洲聯盟就很難說是歐盟內部權力結構變化的結果。而新自由主義認為,國際制度的高成本和低效率會使得國家參與的絕對收益不斷下降,從而導致國家退出。雖然這往往也是政治家在宣布退出時的理由,但公開宣稱的原因可能并不是真實原因。僅僅對國際制度不滿并不一定導致成員國的退出,一方面,國家可能找到解決制度設計和有效性等問題的方式,另一方面,行動慣性和沉沒成本也會使國家繼續留在國際制度中,尤其是當退出成本更高的時候。(15)Inken von Borzyskowski and Felicity Vabulas, “Hello, Goodbye: When Do States Withdraw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14, No.1, 2019, p.337.
在回答國家為什么會參與國際制度時,建構主義認為國際制度規范可以改變國家對利益的認知,改變國家偏好,使國家對國際規范產生認同,在認同的基礎上遵守國際規范,參與國際制度。(16)[美]瑪莎·芬尼莫爾著,袁正清譯:《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頁。也就是說,國家因認為符合國際制度規范的行為是合法的進而遵約。國家退出國際制度則是因為國際規范和國內規范的匹配程度發生了變化。(17)關于國內規范與國際規范的匹配與互動的研究可參見Amitav Acharya,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8, No.2, 2004, pp. 239-275;潘忠岐:“國內規范、國際規范與中歐規范互動”,《歐洲研究》,2017年第1期,第18-36頁等。然而,國際社會現實卻表明,有些國家會拒絕與國內規范相一致的國際規范,退出相關的國際制度。美國作為諸多國際制度的創建者和主導者,退出了涉及多個問題領域的相關制度,并且曾反復退出和加入某些國際制度,很難說此類行為皆因國內規范與國際規范的匹配程度發生了變化。因此,國內規范和國際規范的匹配程度并不能有效解釋國際制度中的國家退出行為。
綜上所述,國際關系領域較少關于國家退出國際制度的一般性且得到普遍認同的理論,主流理論學派也無法做出全面的解釋。此外,國際法領域對國際條約退出機制的研究,以及對條約退出權的研究能提供良好的借鑒。(18)參見馬英杰、張紅蕾、劉勃:“《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退出機制及我國的考量”,《太平洋學報》,2013年第5期,第24-32頁;銀紅武著:《條約退出權研究》,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但是,該領域往往回避和忽略對國家退出實踐及其影響的研究,對國家何時和為何要退出也缺乏系統性研究。(19)韓逸疇:“退出,呼吁與國際法的演化和發展——基于阿爾伯特·赫希曼的理論視角”,《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第188頁。
隨著國際制度中的國家(尤其是主導國)退出行為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國內外也涌現出一些具有洞察力的研究。在體系層面,除新現實主義關注的權力結構變化及新自由主義關注的國際制度本身的高成本低效率外,還有學者從地緣政治因素、國際制度內社會關系變化等角度進行了解釋。(20)See Inken von Borzyskowski and Felicity Vabulas, “Hello, Goodbye: When Do States Withdraw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 14, No. 1, 2019, pp.335-366; Mingtao Shi, “State Withdrawal from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Changing Social Relations within Divergent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5, No. 2, 2018, pp.221-241.不少學者轉向國內政治層面尋找國家退出國際制度的內在邏輯,如國內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對國際制度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質疑,(21)Jack Snyder, “The Broken Bargain: How Nationalism Come Back”, Foreign Affairs, March/April 2019, pp. 54-60.國內政治結構變化帶來的國際制度行為變化等。(22)Helen V. Milner and Dustin H. Tingley, “Who Supports Global Economic Engagement? The Sources of Preferences in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5, No.1, 2011, pp. 37-68.
國家的國際制度行為是一個復雜的國內—國際互動過程。(23)目前有關國家國際制度行為的研究大多是從國內和國際互動的角度進行解釋,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運用雙層博弈理論進行分析,認為國家的國際制度行為及其變化是國際層次的談判與國內層次批準博弈的結果。參見韋進深著:《決策偏好與國家的國際制度行為研究》,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Harry Noone, “Two-Level Games and the Policy Process: Assessing Domestic-Foreign Policy Linkage Thoery”, World Affairs, Vol. 182, No.2, 2019, pp. 165-186.僅從體系層面或國內政治層面對國家退出國際制度的行為進行分析都是不全面的,任何單一因素都不能導致結果,還有其他變量在發揮作用。然而,要區分出哪一種因素在國家的退出行為中扮演更重要的作用往往是困難的,“真正的挑戰在于必須理解不同的因素如何互動,從而導致了特定社會事實”。(24)唐世平著:《國際政治的社會演化:從公元前8000年到未來》,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15頁。因此,本文將從國內—國際互動的角度對國家退出國際制度的行為進行解釋。國家在國際制度中的收益變化、國家退出國際制度的偏好形成及最終決策,都是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結果。
二、國內—國際互動中的收益變化與行為選擇
收益變化是國家行為選擇的動力。國家參與國際制度獲得的制度紅利是不斷變化的,這主要涉及國內與國際兩個層面互動過程中成本和收益的變化。雖然一般認為國家在國際制度中收益的衰減并不足以充分解釋國家為何退出國際制度,但合作狀態的巨大收益的確是國家參與國際制度的主要動力。國家不需要加入一個不符合其利益的國際制度,甚至有觀點認為制度只是實現國家利益的手段,制度之所以有效,只是因為國家相信制度符合自己的利益。(25)Robert Jervis,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Understanding the Debat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1999, pp. 55-62.更重要的是,國際制度不只為國家提供一種簡單的二元選擇——加入或不加入、存在或退出,即使國家在國際制度中的收益減少,也并非只有退出這一種選擇。
2.1 國家在國際制度中的收益變化
國際制度并不會保持其原始狀態,持久存續的國際制度會隨著國際社會政治、經濟和技術環境的變化而變化。原來制定或參與國際制度的環境發生重大變化,可能導致國家在國際制度中的收益有所下降。一方面,由于技術進步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人類的生產活動會創造一定的剩余,從而使各類組織都不同程度地具備承載低效運行的能力,因而績效退減一定會發生。(26)[美]艾伯特· O. 赫希曼著,盧昌崇譯:《退出、呼吁與忠誠:對企業、組織和國家衰退的回應》,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5年版,第3頁。無論國際制度設計得多么完善,都會有不斷衰退的傾向,這種衰退既可能是持久的,也可能是間歇的。這種衰退必然會帶來國際制度的高成本和低效率,增加國家參與的成本并降低收益。另一方面,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參與國際制度收益的進一步增長就會變得愈發困難。經濟盈余比付出的成本上升得快,國家才有參與制度的能力和動力。然而根據收益遞減規律,當國際制度發展到某一階段時,國家付出的成本會逐漸超過經濟盈余,尤其對于主導國而言,維持國際現狀的經濟成本往往比用于支撐其地位和現狀的財政能力上升得更快。因此,主導國參與和維持國際制度的成本終會超過收益,其他國家也會存在同樣的發展趨勢。
除上述絕對收益變化外,差異化收益的累積也會造成國家相對收益的變化。國際制度給所有參與者的行為設定了各種約束,這種設定往往決定了相關議題領域的利益分配結構。國際制度通常體現的是制度中權力最大的那部分成員的利益,至少該制度建立之初的情況如此。(27)[美]羅伯特·吉爾平著,宋新寧、杜建平譯:《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頁。隨著時間的流逝,由于經濟、技術和其他領域的發展變化,國際制度中各國利益與權力平衡的狀況也必然發生變化,國家在國際制度中的相對收益也會發生變化。相對收益受損會使國家產生危機感或不公正感,可能導致國家國際制度行為的改變。
更重要的是,國家對利益的認知也處在不斷變化之中。國內利益集團的變動、經濟和人口的長期變化及其他方面的發展,都會引入各種新的利益,而這些利益最終會在國家立場上得到反映。因此,國家在國際制度中收益的變化可能并不是絕對收益或相對收益下降,而是國家利益認知變化后對參與國際制度的成本和收益做出的重新判斷。例如,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議定書》,以及特朗普政府宣布并正式啟動退出《巴黎協定》程序,并不完全是美國在國際氣候制度中的絕對收益或相對收益發生了變化,更多的是新政府上臺之后對國家利益的認知發生了變化,進而對參與國際制度的成本和收益進行了重新衡量。
綜上所述,國家在國際制度中的收益變化,既包括絕對收益和相對收益的變化,也包括利益認知變化導致的收益變化。既有國際層面國際制度效能下降、制度內權力結構變化的原因,也涉及國內層面政治結構變化等因素。因此,國家在國際制度中的收益衰減實際也是國內—國際互動的結果。
2.2 國家的制度行為選擇
無論絕對收益或相對收益的下降,還是利益認知變化導致的收益下降,都會對國家繼續參與國際制度合作的動力和能力產生負面影響,但這并不意味國家必然會產生退出的偏好或決策,相反,國家有多種行為選擇來應對其在國際制度中的收益損耗。
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在其《退出、呼吁與忠誠:對企業、組織和國家衰退的回應》一書中提出了“退出—呼吁”機制。根據其觀點,當一國在其參與的國際制度中利益受損或遭遇不公時,國家會采取退出制度或在制度中呼吁改革這兩種策略來表達利益訴求。(28)Scott Gehlbach, “A Formal Model of Exit and Voice”,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 18, No.4, 2006, pp.395-396.但事實上,國家并不是在退出和呼吁之間做單一選擇,而是面臨二分法的選擇,即退出或不退出,若不退出的話,是選擇呼吁改革,還是沉默忍受。(29)Brain Barry,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by Albert O. Hirschma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No. 1, 1974, pp. 91, 97.選擇退出,意味著國家不接受不利變化,通過退出制度來改變不利處境。選擇沉默,意味著國家接受不利變化,不改變其制度行為,但這并不是因為它們不希望以建設性的方式回應不滿,而是它們根本無力采取其他行動。(30)William Roberts Clark, Matt Golder, and Sona N. Golder, “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Model of Politic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7, No.1, 2017, p.721.選擇呼吁改革,意味著國家不接受不利變化,而是通過各種方式在內部尋求改變,修正國際制度中的規則、政策或產出,以求恢復原本的有利環境。成員國威脅退出,即如果國際制度沒有滿足其要求便退出,實際上也是一種呼吁。
如圖1所示,面對國際制度中收益受損的情況,國家有三種可能的行為選擇:呼吁改革、退出和沉默。國際制度的參與國具有異質性,它們在制度內部呼吁或退出的成本和收益是不一樣的。假設國家退出國際制度的預期收益是E1(E1>0),退出的成本是C1(C1>0);沉默實際意味著國家并沒有改變其行為,假設其收益和成本皆為0(不考慮已經產生的利益受損);國家通過呼吁來改善自身處境的預期收益和成本分別為E2和C2(E2>0,C2>0)。國家是否選擇呼吁主要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國家是否愿意承擔這種不確定性;二是呼吁后國際制度發生改進的概率。(31)[美]艾伯特· O. 赫希曼著,盧昌崇譯:《退出、呼吁與忠誠:對企業、組織和國家衰退的回應》,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5年版,第31頁。呼吁涉及國家在國際制度中的話語權和討價還價的能力,這種話語權通常在制度設計之初就已經確定,大部分國家往往無法通過在制度內部呼吁使其發生有利于自身的轉變。若國際制度選擇忽略呼吁國家的訴求,則呼吁國不能達到其預期收益。呼吁無效后,國家再選擇退出的收益仍為E1,而退出的成本為C1+C2;沉默的收益仍為0,成本則為C2。

圖1 利益受損時國家的制度行為選擇資料來源:筆者結合艾伯特·赫希曼的“退出—呼吁”機制及其他相關文獻自制
既然在面對收益受損時,國家有退出、呼吁和沉默三種選擇,那么國家為何要選擇退出?日常的外交政策制定主要以當前政治上的緊急事務為導向,集中于短期的成本和收益;與此相反,加入或退出國際制度這一更審慎的過程會考慮更長遠的利益和價值觀。(32)Abram Chayes and Antonia Handler Chayes, “On Complianc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7, No. 2, 1993, pp. 175-205.簡言之,國家退出國際制度,除了短期的退出成本和收益的衡量,即當E1-C1>0時國家才會選擇退出,還需要對退出的前景進行衡量。在某些情況下,國家希望通過有效的呼吁來改變國際制度,然而往往因為呼吁的成本過高或國家無力對制度和制度內的其他行為體施加影響而導致國家直接選擇退出。即使是像美國這樣的主導國也是如此,若美國能輕易通過呼吁改變對其不利的制度環境,也就無需承擔退出成本。國家選擇直接退出國際制度時的預期就是退出后的前景要優于留在制度中的前景,即E1-C1>E2-C2。
還有一種情況,在面對收益受損時,國家并不會直接選擇退出,而是優先選擇呼吁,也就是說,國家預期的呼吁前景要優于直接退出的前景(E2-C2>0且E2-C2>E1-C1)。這也可以解釋為何同樣面對收益變化的情況,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中選擇威脅退出,而直接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國際制度。呼吁失效后,若退出的收益仍大于退出成本,并且退出的前景仍優于忠誠于組織的前景,即E1-(C1+C2)> 0-C2且E1-(C1+C2)>0時,退出仍可以作為呼吁的替代選擇。事實上,呼吁是否有效也取決于行為體退出的前景。沒有退出的可能性,呼吁也就毫無意義。
綜上所述,國家在國際制度中的利益受損并不會直接產生退出的偏好和決策,并不是所有在國際制度中利益受損的國家都會選擇退出。國家的退出選擇是通過短期的成本收益計算與未來收益前景的衡量而得出的。影響成本與收益考慮的環境變化因素甚多,不可能一一列出,而且取決于國家如何理解退出國際制度的成本和收益。盡管人們把成本和利益作為客觀的且可以做定量分析的要素來談論,但實際上它們都具有很大的主觀和心理成分。(33)[美]羅伯特·吉爾平著,宋新寧、杜建平譯:《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7頁。毫無疑問,無論是客觀的成本收益計算,還是主觀的理解與認知,都是對國內和國際兩個層面環境因素的綜合考慮。
三、國內—國際互動與國家退出偏好的形成
簡單來說,偏好就是存在多種行為選擇的情況下,對其中一種選擇的傾向性影響最終的決策與行為。國家在國際制度中出現利益受損時,并非只有“退出”一個選項,但為何產生對“退出”的傾向性呢?根據上文所述,當退出的收益預期大于呼吁和沉默時,國家就會傾向于退出。然而,由于不確定因素和決策者的有限理性,(34)在實踐中,決策者既受到環境不確定的局限,也受到自身認知能力的局限,后者即為“有限理性”。參見[美]羅伯特·基歐漢著,蘇長和、信強等譯:《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紛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1頁。國家的退出偏好很可能并非基于完全理性的成本收益計算,而是受到國內外因素互動的影響。國際制度中的權力分配會對國家是否退出及采用的退出策略產生影響,國內退出偏好是國內不同行為體利益和偏好復雜博弈的結果,國際制度的約束力作為一種外在激勵效用也會強化或弱化國家的退出偏好。
3.1 國際制度中的權力分配
有不少學者將國家國際制度行為的變化歸結于國際權力結構的變化。的確,國家退出國際制度的行為在國際體系的轉型期較為常見,如德國和日本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退出國際聯盟。圍繞國際制度的締造、改革和退出所展開的博弈,本質上是大國權力、利益和聲譽的競爭。(35)汪海寶、賀凱:“國際秩序轉型期的中美制度競爭——基于制度制衡理論的分析”,《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第59頁。由于當前國際體系處于深刻的變化過程中,制度變遷與權力轉移相輔相成,由此也導致了一些國家退出國際制度的現象。尤其是當國家實力的增長或衰落引起國家在國際權力結構中權力序位提高或降低,即國內—國際權力互動發生變化時,必然會導致國家的國際制度行為發生變化。然而,權力結構的變化并不能充分解釋為什么有些國家退出了,有些國家仍然忠誠于制度;為什么有些國際制度頻繁出現退出甚至集體退出,而有些國際制度仍然保持著活力。
權力序位能為國家在面對收益受損時圈定不同的行為備選方案,因此,國家退出偏好的形成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國際制度中權力分配的影響。這里的權力既指整體實力,包括經濟實力、政治和軍事實力、文化和價值觀的影響力,也指在特定問題領域或制度領域內的實力。當利益受損時,實力地位會影響國家的國際制度行為選擇,每個國家退出的成本和收益都是不同的。
在國際制度中面臨收益降低的風險時,實力強大的國家通常有呼吁和退出兩種選項。強大的實力可以賦予國家對國際制度一定程度的操控力,甚至一些實力強大的國家正是國際制度的最初創立者,在工具化利用國際制度時會更加積極主動。當國際制度不能滿足其需求時,這些國家可以在內部呼吁進行變革或實行威脅退出策略。它們可以將其擁有的物質資源轉化為具體制度中利害攸關問題的談判籌碼。(36)[美]奧蘭·R. 揚:“政治領導與機制的形成:論國際社會中的制度發展”,載[美]莉薩·馬丁、貝思·西蒙斯著,黃仁偉、蔡鵬鴻等譯:《國際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頁。甚至,威脅退出策略會比在內部呼吁變革更加有效。因為其他成員國面對不滿現狀國的呼吁訴求時可以選擇不作為而沒有任何損失,但如果不滿現狀國威脅退出制度,選擇不作為的其他成員國將可能承受不滿現狀國退出國際制度帶來的損失。(37)劉宏松、劉玲玲:“威脅退出與國際制度改革:以英國尋求減少歐共體預算攤款為例”,《世界政治研究》,2019年第1輯,第76-77頁。例如,2017年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后,多次聲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給予墨西哥和加拿大太多讓步,以致美國利益長期受損,要求重新談判和修訂相關條款,否則將退出。最終,墨西哥和加拿大同意重新談判。在這一過程中,美國利用自身貿易優勢地位率先與墨西哥達成協議,倒逼加拿大在談判中妥協。2018年10月,三方完成新一輪談判,并將該協定重新命名為《美墨加三國協議》(USMCA)。這個新協議在美國關注的汽車制造業、勞工和環境法規、藥品定價等方面都發生了有利的改變,被特朗普稱為“美國有史以來達成的最好的、也是最重要的貿易協議”。(38)“美墨加三國領導人在阿根廷簽署新版貿易協定”,新華網,2018年12月2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8-12/02/c_1210006785.htm。
國家選擇在內部進行呼吁,既取決于呼吁的成本和收益,也取決于該國相信國際制度未來發生更大變革的可能性。(39)Jonathan B. Slapin, “Exit, Voice, and Cooperation: Bargaining Power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Federal System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21, No. 2, 2009, p.189.然而,呼吁并不一定會得到制度內其他成員國的積極回應。實力強大的國家也可能選擇退出,除了呼吁的成本過高或無法進行可信和有效的威脅退出之外,該國對退出前景的預期可能要高于留在制度內的前景,但強勢國家退出之后往往不會游離于國際制度之外。一方面,退出國退出之后仍然在制度外呼吁,推動新的國際談判,要求相關國際制度進行重大改革。如1984年,美國以管理不善和腐敗等理由宣布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03年重新加入,2019年1月又以教科文組織助長“反以色列偏見”為由再次退出。(40)“美國和以色列1月1日正式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新華網,2019年1月3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9-01/03/c_1210028955.htm。另一方面,實力強大的國家往往會有替代性的選項,即退出后創立新的國際制度。它們不僅有能力和意愿主導國際制度和規則,還有能力廢舊立新,退出已不符合本國利益的制度,設立符合本國利益的新制度。例如,美國退出旨在給予發展中國家特殊照顧的《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并以此為基礎迫使發展中國家接受有利于美歐利益的義務性規定,進而推進了世界貿易組織及相應國際貿易規則的創立。(41)Richard H. Steinberg, “In the Shadow of Law or Power? Consensus-based Bargaining and Outcomes in the GATT/W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6, No.2, 2002, pp.339-374.
在國際制度中發生收益受損時,實力較為弱小的國家會有退出和沉默兩種選項。只有當行為體有退出或威脅退出的能力時,它在制度內的呼吁才是強有力的。如果行為體的退出威脅不可信,或者它是否留在制度內并不被重視,那么它的呼吁將是無效的。相反,有能力進行有效呼吁的行為體通常不需要發聲,因為制度會預測它的愿望并做出積極反映。(42)William Roberts Clark, Matt Golder, and Sona N. Golder, “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Model of Politic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7, No.1, 2017, p.751.較為弱小的國家通常沒有能力對國際制度和其他成員國施加影響,其成員資格可能對國際制度而言意義不大。因此,當制度談判對其不利時,較為弱小的國家要么直接從國際制度中退出,要么沉默。一方面,弱小國家往往在國際制度中處于相對底層和邊緣的位置,缺少必要的社會資本來面對制度壓力。另一方面,由于國際制度的非中性或其本身存在的某種傾向,不同成員國在國際制度中可能受到差別對待,弱小國家可能在制度內外的待遇相差無幾。
3.2 國內利益與偏好
國內不同行為體具有不同的利益和偏好,國家的行為偏好并非某一行為體利益和偏好的體現,而是多方利益主體參與的復雜博弈結果。但由于對外事務的特殊性和機密性,國家的外交政策往往由該國占統治地位的成員或統治聯盟的利益決定。國家對外行為偏好最主要體現的是決策者的利益和偏好。例如,在美國的外交政策中,保守主義主要強調實力,尤其是軍事力量在外交政策中的作用,強調維護美國的主權、安全和國家利益。同時,保守主義是共和黨的主流意識形態,當共和黨執政時,保守主義對外交政策的影響往往占主導地位。(43)周琪著:《意識形態與美國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頁。此外,在外交事務的實際操作中,總統居于主導地位,是核心決策者,導致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與踐行都深受總統個人風格和偏好的影響。
首先,偏好具有主觀性。國家的國際制度行為選擇主要掌握在決策者手中,奉行“國際主義”的決策者可能會對國際制度采取更積極的態度,而奉行“孤立主義”的決策者可能對國際制度采取消極態度。國家在國際制度中持續出現利益損耗,會導致國家內部對國際制度的需求發生變化。當決策者或執政黨的意識形態和利益取向傾向于改變體系時,國家更有可能形成退出的偏好。特朗普作為總統候選人時曾針對外交政策發表演講,他指出,“我們將不再讓這個國家和人民屈服于全球主義的虛假之歌”。(44)Julian Hattem, “Trump Warns against ‘False Song of Globalism’” The Hill, April 27, 2016, https://thehill.com/policy/national-security/277879-trump-warns-against-false-song-of-globalism。特朗普政府上臺后,“放棄”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選擇放棄很多國際制度和框架”,不是因為任何軍事或經濟力量的喪失迫使美國削減其全球承諾,(45)David Wright,“Haass Says US Engaged in Abdication of Global Leadership”, CNN, January 3, 2018, http://www.cnn.com/2018/01/03/politics/richard-haass-trumpleadership-cnntv/index.html.而是因為奉行“美國優先”的策略。也有研究表明,美國在一系列國際制度中的退出行為正是特朗普的人格特質在國際關系上的表現。(46)參見尹繼武、鄭建君、李宏洲:“特朗普的政治人格特質及其政策偏好分析”,《現代國際關系》,2017年第2期;王一鳴、時殷弘:“特朗普行為的根源:人格特質與對外政策偏好”,《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8年第1期,第98-127頁。
其次,國內外環境的變化會影響國內利益和偏好,使其在一定范圍內產生變動。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參與國際制度所產生的國內成本與收益會發生變化,從而導致國內權力資源重新分配和利益集團分化,基于這種變化,國家外交政策中的利益或者目標的組合就有可能變更,(47)[美]羅伯特·吉爾平著,宋新寧、杜建平譯:《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頁。國際制度行為偏好也會發生變化。這種國內—國際利益互動的變化,可能并不是通常所能觀察到的絕對收益或相對收益的變化,而是由于國家內部權力分配變化之后導致的利益認知的變化。國內權力資源分配變化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政府更迭。新總統上任等結構限制的松動為國家退出國際制度提供了良好的時機。(48)溫堯:“退出的政治:美國制度收縮的邏輯”,《當代亞太》,2019年第1期,第14頁。國家對待國際制度的偏好發生顛覆性的轉變通常與該國政府的交接同步進行,新一屆政府往往傾向于否定前任的外交政策。例如,美國決定退出《京都議定書》發生在2001年3月28日小布什政府上臺伊始,而特朗普政府退出的國際制度大多是奧巴馬政府的政治遺產,如跨太平洋合作伙伴關系(TPP)等,均在其上臺半年之內宣告退出。再如,2016年10月,岡比亞向聯合國發出了退出國際刑事法院的退約通知,2017年2月,新總統上臺僅一個月后,岡比亞就做出了撤回退約通知的決定。(49)Manisuli Ssenyonjo, “State Withdrawal Notifications from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South Africa, Burundi and the Gambia”, Criminal Law Forum, Vol.29, No.1, 2017, pp. 63-119.
最后,偏好具有大眾趨向性。國內偏好并不是固有的,也可能并不局限于物質狀況,而是受到他者偏好選擇的影響。不確定環境中的有限理性行為體經常從其他明顯成功的行為體曾嘗試過的解決辦法中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50)[美]瑪莎·芬尼莫爾著,袁正清譯:《國際社會中的國家利益》,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頁。當國家無法形成穩定的行為偏好時,模仿常常是一種理性的戰略選擇。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國際制度中退出行為(尤其是主導國退出)的外溢效應。例如,美國最早退出《京都議定書》后,加拿大也宣布退出,而日本和俄羅斯表示堅決不實施《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再如,南非、布隆迪和岡比亞向國際刑事法院遞交退出通知后,肯尼亞、納米比亞和烏干達等國也威脅退出。事實上,有些國家是在盟友或對手的壓力下參與和退出國際組織的,如非洲聯盟曾做出若干決定,呼吁非洲國家對國際刑事法院采取不合作態度,并支持成員國考慮退出國際刑事法院。(51)“國際刑事法院被質疑成西方干涉非洲國家內政工具”,《國際先驅導報》,2016年11月3日。
3.3 國際制度的約束力
國際制度對成員國的約束力作為一種外在激勵效用也會強化或弱化國家的退出偏好。這種約束力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成員國退出的機制約束力,即國際制度是否有退出機制或條款允許國家退出;二是,對成員國的道德約束力,這取決于國際制度自身的公正性、合法性等聲譽影響因素。國際制度對退出行為的約束力越強,國家退出的預期成本就越高;反之,約束力越弱,國家退出的偏好就越容易形成。
國家退出國際制度的一個主要前提條件是該制度在設立之初是否有退出條款的設計,即成員國是否有退出制度的合法權利。為協調條約的剛性承諾與國家對靈活性需求之間的緊張關系,條約通常允許國家在某種情形下退出先前已經批準生效的條約,或在國際組織章程中規定國家退出的條件。(52)韓逸疇:“退出,呼吁與國際法的演化和發展——基于阿爾伯特·赫希曼的理論視角”,《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第188頁。現今,大部分國際制度都有退出機制,能夠以明確清晰的退出程序防止退出的不確定性,如果程序設計得當,還能防止其他成員國對退出國實施任意的懲罰性制裁。(53)Andrew Shorten, “Constitutional Secession Rights, Exit Threats and Multinational Democracy”, Political Studies, Vol.62, No.1, 2014, p.102.若國際制度中有相應的退出機制,國家的退出就具有合法性依據,出現利益損耗的國家也就更容易產生退出的偏好。
然而,面對利益受損即退出國際制度的國家,仍可能被制度內的其他成員國視為非合作型行為體,對該國聲譽產生影響,需要承擔退出的聲譽成本。事實上,國家從國際制度中退出是否會產生聲譽成本與該制度本身的聲譽掛鉤。(54)Annika Jones, “Non-coopera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n Olympia Bekou and Daley Birkett eds., Cooper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Perspectives from Theory and Practice, Brill Nijhoff, 2016, pp. 185-209.通常認為,合法性和公正性是國際制度得以遵守的前提條件。國際制度的合法性往往取決于成員國的集體認同。(55)王瑋:“國際制度與新進入國家的相互合法化”,《世界經濟與政治》,2010年第3期,第79頁。而很多國際制度都帶有隱蔽的非中性特點,完全公正的國際制度很難實現。盡管如此,具有明顯歧視性和傾向性的國際制度的社會認同度仍會大大減弱。(56)李明月著:《國內規則與國際規則的互動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87頁。
國際制度的合法性和公正性越高,其國際聲譽就越好,國家不合作或退出所帶來的聲譽成本就越高。(57)Stef Vandeginste, “The ICC Burexit: Free at Last? Burundi on Its Way Out of the Rome Statute”, Analysis and Policy Brief N°20, October 2016, p. 3.其他國家如果認為退出國的行為違背先前承諾、有損多邊主義精神,則可能在未來的互動中采取相應措施,對這種行為實施報復和懲罰。(58)溫堯:“退出的政治:美國制度收縮的邏輯”,《當代亞太》,2019年第1期,第11頁。對于聲譽較差的國際制度,國家的退出不僅不會產生聲譽成本,反而還會帶來聲譽收益。例如,自2009年初蘇丹總統巴希爾被起訴以來,非洲國家對國際刑事法院的批評越來越強烈,普遍認為其指控喪失公信力,僅僅針對非洲國家,《羅馬規約》也與國際法義務相沖突。(59)如《羅馬規約》迫使包括南非在內的國際刑事法院締約國“逮捕根據國際習慣法可能享有外交豁免權但被法院通緝的人”。Manisuli Ssenyonjo, “State Withdrawal Notifications from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South Africa, Burundi and the Gambia”, Criminal Law Forum, Vol. 29, No. 2, 2017, pp.10-33.因此,布隆迪退出國際刑事法院在其他堅持自力更生和反對新殖民主義政治干預的非洲國家中具有良好聲譽。它的退出可能會得到國際社會中那些將主權置于人權保護和刑事司法全球化之上國家的同情,最終甚至會帶來經濟收益。(60)同⑥。一般而言,在國際聲譽較好的國際制度內,國家即使出現利益損耗也會謹慎選擇退出;在國際聲譽較差的國際制度中,國家則更容易形成退出偏好。
國際制度中的利益損耗并不必然使得國家形成退出的行為偏好,但會使國家內部出現調整國際制度行為的需求。國家在國際制度中的實力地位對國家的退出策略(實質性退出或威脅退出)產生影響。若國內利益主體力量對比發生了有利于“退出”的變化,如傾向于改變體系的領導人或執政黨上臺,而國際制度對于退出行為的約束力較弱,那么國家就可能形成退出偏好。
四、國內—國際互動與國家的退出決策
退出偏好并不必然形成退出決策,只能對國家行為進行趨勢性解釋,但無法判斷特定國家在特定時間的具體行為。國家退出國際制度既是國際體系層面的問題,也是國內政治博弈的結果。作為一種對外決策,退出某一國際制度也并非簡單地由國家決策者主觀決定,而要受到國際體系壓力和國內政治框架的共同束縛。國家與國際制度的相互依賴程度是判斷國家退出在國際層面成本收益函數的重要指標,國內決策結構的集中與分散程度高低則是國家退出能否在國內獲得“批準”的重要因素。退出偏好轉化為外交政策實踐也是國內—國際互動的結果。
4.1 國家與國際制度的相互依賴程度
國際制度中權力結構的變化會對國家的退出偏好產生影響,但并不是國家退出國際制度的決定因素,無論是強勢國家還是弱勢國家都有可能在利益受損時選擇退出。但是,不同國家的退出成本和退出前景是不同的,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家與國際制度的相互依賴程度。
一方面,國家對國際制度依賴程度越低,說明國際制度所涉議題領域同國內事務聯系的緊密程度越低,國家退出的可能性就越高。國家之所以愿意參與國際制度并接受國際規則的約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家對國際制度及其主導國提供的市場、技術、資本、政治支持和安全保護等存在依賴性,不遵守相關規則的機會成本很高。(61)潘忠岐等著:《中國與國際規則的制定》,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6頁。國家對國際制度依賴程度較高,意味著國家退出國際制度的成本較高,當國際制度不能滿足國家需求時,國家可能會通過呼吁變革或威脅退出策略來改變自身在國際制度中的不利處境,而不會貿然選擇實質性退出。相反,若國家對國際制度的依賴程度較低,說明國家在國際制度中的獲益有限或有其他替代選項,其退出國際制度的成本也較低。因此,當國際制度無法再滿足國家需求時,國家極有可能直接退出。
國家對國際制度的依賴程度可以作如下衡量:一是,入會條件的高低。加入一個群體的條件越嚴格或費用越高,說明加入時投入的成本較高,人們就越發認為該群體具有較強的吸引力。(62)[美]艾伯特· O. 赫希曼著,盧昌崇譯:《退出、呼吁與忠誠:對企業、組織和國家衰退的回應》,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5年版,第122頁。國家加入國際制度的成本不僅包括國家在國際層面的談判努力,做出的國際承諾,還包括國家內部的政治博弈,相應的國內制度變革等。高成本說明國家對加入國際制度的預期收益較高,對國際制度的依賴性越強,退出的成本也越高。相反,加入國際制度時的成本越低,說明國家投入的成本越低,那么退出的成本也相對較低。二是,競爭性國際制度存在與否。競爭性國際制度的存在或多或少會降低國家對某一國際制度的依賴程度。(63)Scott Kasner, Margaret Pearson, and Chad Rector, “Invest, Hold Up, or Accept? China in Multilateral Governance”, Security Studies, Vol. 25, No. 1, 2016, pp. 142-179.制度的非中性和非唯一性(即在同一個議題領域或同一個區域可能存在多個國際制度)為國家在國際制度之間的選擇創造了空間,(64)李巍、羅儀馥:“從規則到秩序——國際制度競爭的邏輯”,《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第4期,第38頁。即國家在退出后不至游離于國際制度之外,而是可以加入其他競爭性的國際制度。即使不存在競爭性國際制度,對現行國際制度不滿的強勢行為體,也可通過機制轉換和創建競爭性機制的方式建立可信的外部選項。(65)See Julia C. Morse and Robert Keohane, “Contested Multilateralism”,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Vol.9, No.4, 2014, pp.385-412; [美]羅伯特·基歐漢:“競爭性的多邊主義與中國崛起”,《外交評論:外交學院學報》,2015 年第6期,第20-27頁。因此,無論是在同一領域或同一區域存在多個國際制度,還是強勢國家在外部創建新國際制度的預期,都會降低退出國對當前國際制度的依賴程度,因為還有其他選擇。
另一方面,國際制度以及制度內的其他成員國對退出國的依賴程度越高,退出國越有可能通過內部呼吁或威脅退出來達到目標,而不必實質性退出。這樣的退出國往往是國際制度中的主導國或關鍵成員,其他成員國不愿意承受其退出帶來的巨大損失,往往會選擇盡力滿足其需求。因此,國際制度中的主導國或關鍵成員在制度談判中的議價權力較大,可以通過威脅退出來呼吁制度改革,這種呼吁的成本較低,且很容易得到制度內其他成員的回應,從而達到目標。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美國威脅要退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和《美韓自由貿易協定》之后,相關國家都同意開啟重新談判并達成了新的協定。制度內非關鍵成員的威脅退出卻很難達到預期效果,因為制度內的其他成員國往往對其依賴程度較低。非關鍵成員在國際制度內部進行改革呼吁,不僅成本頗高,也很難得到積極的回應;更為弱勢的國家甚至會在國際制度中被邊緣化。
4.2 國內決策結構的集中與分散程度
決策者和執政黨對國際制度的消極態度并不一定導致國家退出國際制度的行為,只會增強決策者在推動國家退出過程中的主動性。國家的政治體制不同,利益分配方式也不同,決策者做出退出決策時面臨的國內制約因素也不一樣。國家并不是單一的理性行為體,國家退出國際制度的決策很少反應單一或一致的國家利益計算,國內不同政治和社會力量對國際制度的態度可能并不完全相同,最終做出退出國際制度的決策還取決于退出國的國內決策結構。決策結構越集中,意味著參與決策的人數和機構越少,決策者受到的國內限制就越少。例如,一個專制或獨裁的政府,國內政治對對外政策的影響和限制總體上是有限的,領導人的決策余地很大。(66)張清敏著:《對外政策分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62頁。因此,當決策者偏好退出且國內決策結構更為集中而不是分散時,國家更有可能退出國際制度。
決策結構越是分散,意味著參與決策的人數和機構越多,考慮的要素也就越多,國家關于退出國際制度所受到的國內政治競爭影響就越大,甚至會出現制衡情況。國家退出國際制度的決策實際上就是國內不同政治行為體和社會行為體博弈的結果。例如,南非政府于2016年向聯合國提交了決定退出國際刑事法院的有關信件,并決定正式啟動退出該機構的程序。然而,在野黨向南非高等法院提起訴訟,即南非政府在未經議會批準和未向公眾咨詢的前提下發出了退出通知。(67)Manisuli Ssenyonjo,“State Withdrawal Notifications from the 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South Africa, Burundi and the Gambia”, Criminal Law Forum, Vol. 29, No. 2, 2017, p. 3.2017年2月,南非高等法院作出判決,南非政府退出國際刑事法院的決定違憲。(68)“南非高等法院判決南非政府退出ICC的決定違憲”,中國新聞網,2017年2月22日,http://www.chinanews.com/gj/2017/02-22/8156904.shtml。最終,南非政府正式撤回了退出國際刑事法院的申請信件,提前終止了退出該國際組織的程序。雖然南非政府終止退出程序是因為“程序不正確”,但也反映出南非國內對于國際刑事法院的不同態度。
國家在國際制度中成本上升和收益減少的變化,首先會反映在普通民眾而非政治精英身上。在他們看來,退出國際制度的確會帶來國內政治收益,并卸掉參與的負擔。雖然民意和輿論并不會直接轉化為政治家的行動或國家的退出實踐,但民眾可以通過各種渠道影響外交政策,如在民意測驗中的表態、利益集團或社會組織的游說,以及對國會議員的影響等。民眾對國家國際制度行為影響最直接的渠道是針對特定問題的公投,之后國家根據公投的結果做出決定。例如,英國的“脫歐”公投,支持“脫歐”的結果為英國國內長期以來具有爭議的政策做出了最終決定。而美國民眾在2016年選出了奉行“美國優先”的總統,關注國內改革和重建,在國際上表現為減少責任和退出國際制度。(69)Randall Schweller, “Opposite But Compatible Nationalisms: A Neoclassical Realist Approach to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1, No.1, 2018, p. 15.
對于不同的國內行為體而言,退出國際制度所需要付出的代價越低或收益越高,其支持退出的可能性就越大。在分散的決策結構下,國內反對退出和支持退出群體之間的力量對比,最終可能影響國家退出國際制度的決策。國際制度所涉議題領域的性質及其同國內事務聯系的緊密程度,會對國內行為體退出國際制度的分歧程度產生影響。在涉及諸如國家領土、主權和安全等同質問題時,國內反對力量同政府總體上是一致的,這種情況下領導人往往具有更大的主動權;對于一些國內存在不同意見和主張的異質問題,如涉及眾多國內利益攸關方的對外經濟政策,受到國內政治影響的程度就更深。(70)張清敏著:《對外政策分析》,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143-144頁。
國際制度與國內事務的聯系越緊密,國際制度所涉的國內行為體就越多。不同的行為體會采取措施影響政策朝于己有利的方向發展,對于國家是否應該退出該國際制度的分歧就越大。即使決策者和執政黨已經形成了退出的偏好,最終可能無法形成退出決策。反之,與國內事務聯系松散的國際制度所涉的行為體較少,利益分歧也較少,對于國家是否應該退出國際制度更容易達成共識。
國家退出國際制度的決策實踐不僅要考慮國際層面的成本和收益,還要考慮國內層面的成本和收益。其中,國際層面的主要變量是國家與國際制度之間的相互依賴程度。國家對國際制度的依賴程度越高,退出成本越高;依賴程度越低,退出的成本也就越低,退出的可能性更高。國際制度對國家的依賴程度越高,國家通過威脅退出來呼吁制度內改革的成本就越低,而無需實質性退出。同時,通過政府間會議達成的重大制度變化都必須得到國內批準。國內決策結構越集中,獲得國內批準的成本就越低,國家的退出偏好越容易形成退出決策;國內決策結構越分散,國家的退出決策就越容易受到國內不同行為體利益分歧的影響,而這種國內分歧又受到國際制度所涉議題及其與國內事務聯系緊密程度的影響。
五、結 語
國際制度是不斷發展演變的,國家在國際制度中的收益也不斷變化。理性主義者認為,當國家參與國際制度的成本大于收益,即出現利益損耗時,國家就會退出國際制度。實際上,即使出現利益損耗,無論是絕對或相對收益的損耗,還是利益認知的變化,國家在國際制度中面臨的并非只有“退出”這一種選項。國家之所以選擇退出,主要是出于對短期內退出成本和收益的衡量以及對退出前景的預期。國家的國際制度行為是一個復雜的國內—國際互動過程,退出的偏好和決策正是在這種互動中形成的。國際制度中的權力分配、國內利益與偏好、國際制度約束力等因素都會對國家的退出偏好產生影響。然而,退出的偏好是否會產生退出的決策和行為,其關鍵在于成本與收益是否平衡及國內“批準”與否。
在國家主權原則下,各主權國家均享有退出國際制度的權利。國家選擇退出某一國際制度框架,即對該領域的國際合作選擇消極甚至背叛的態度,通常被認為是其對該體制表明不滿的一種信號。如果賦予國家在必要時退出國際制度的權利,就能顧及國家行使主權的需要,并提高其參與國際合作的積極性,最終提升國際制度的運行效率。(71)韓逸疇:“退出,呼吁與國際法的演化和發展——基于阿爾伯特·赫希曼的理論視角”,《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第192-193頁。國際社會不同于市場和企業的制度環境,國家雖然可利用退出機制增強在世界舞臺上的發言權,但不可能完全退出國際制度而單獨存在。(72)Laurence R. Helfer, “Exiting Treaties”, Virginia Law Review, Vol. 91, No.7, 2005, pp. 1579-1648.國家退出國際制度并不意味著國家徹底與該制度或相關問題領域割裂,而是對國際制度的反向參與。(73)“反向參與”的概念參見史明濤:“國家正向和反向參與國際制度:一個國際—國內制度互動的解釋”,《國際觀察》,2009年第2期,第57-64頁;韋進深著:《決策偏好與國家的國際制度行為研究》,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4年版。事實上,“退出”也是各國政治博弈的手段。特朗普政府在聲明退出或威脅退出國際制度時仍然表示會推動新的國際談判開展,或者要求相關國際制度進行重大改革,國際制度作為大國政治工具本身還沒有被完全拋棄。(74)溫堯:“退出的政治:美國制度收縮的邏輯”,《當代亞太》,2019年第1期,第30頁。
國家加入國際制度是為了加強某一方面的合作,但是國際制度并不總能為國家帶來制度紅利,有時甚至是負擔。因此,國家在必要時采用“退出”手段來維護國家利益。當前的國際體系處于深刻變化的過程之中,也涌現出一些國家退出國際制度的現象。尤其是主導國的退出,實際也為新興國家提供了制度參與和構建空間,若能利用機會加大對國際制度的投入和參與,將大幅提高自身在國際制度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并進一步推動國際制度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