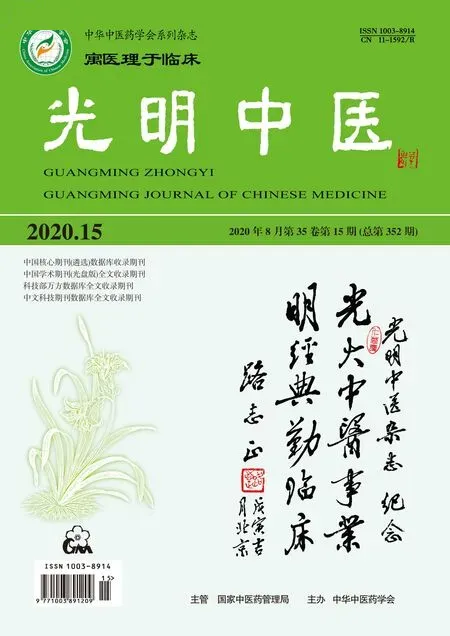淺析《千金方》對中醫婦科學的貢獻*
李 璇 付姝菲 王 彭
漢末唐初,戰亂頻發,孫思邈“痛夭枉之幽厄,惜墮學之昏愚,乃博采群經,刪裁繁重,務在簡易”[1]著成《千金方》。《千金方》是《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的總稱,“人命至重,有貴千金”,故孫氏以“千金”二字為本書命名。將婦人卷置于緒論之后的卷首位置,充分體現了孫氏對婦人病的重視,對后世中醫婦科學的獨立分科具有重要意義。本文從月經病寒溫并用,帶下病祛風補腎,妊娠病治養并重、產后病調養為先以及雜病巧治等方面論述《千金方》對中醫婦科學的貢獻。
1 月經病篇
1.1 寒溫并用月經病常以溫經活血為治療大法,而孫氏則采用寒溫并用法來治療月經病,寒涼藥與溫熱藥配伍使用,一方面去性存用,另一方面防止藥物與病勢相互格拒。如大黃與干姜配伍常用于寒邪積聚所致的月經后期、月經先后不定期等疾病。“大黃[2]主下瘀血,推陳致新,通利水道,安和五臟”。“干姜[2]主溫中止血。”孫氏將大黃與干姜配伍用于月經先后不定期的當歸丸(以干姜、附片、細辛、桂心、吳茱萸等溫熱藥配伍大黃、黃芩、牡丹皮等寒涼藥),月經不通結成癥結的桂心酒(以干姜、桂心、吳茱萸等溫熱藥配伍大黃、黃芩、牡丹皮等寒涼藥)以及雞鳴紫丸(以干姜、桂心等溫熱藥配伍大黃、赭石等寒涼藥),婦人經年月水不利,胞中風冷所致的大黃樸硝湯(以干姜、細辛等溫熱藥配伍大黃、牡丹皮、赭石、芒硝等寒涼藥)達破血下癥之效。
1.2 多用牛膝月經病篇孫氏使用牛膝頻次極高,體現了孫氏對于肝腎的重視,如在大黃樸硝湯、桃仁湯、桃仁散等多首調經方劑中應用牛膝以奏補益肝腎、引血下行之效;更有直接以牛膝命名的用于產后經量異常,腰重身痛的牛膝丸。女子以肝為先天,而腎為先天之本,肝主疏泄,腎主閉藏,重視肝腎二臟,對于防治月經不調等疾病有重要意義。
2 帶下病篇
2.1 風能勝濕“帶不離濕”,濕邪為患,病程長且難以痊愈,在《備急千金要方·赤白帶下崩中漏下》中孫氏多次使用細辛、藁本、防風、白芷等擅祛風之藥,風能勝濕,促進帶下病痊愈,以防濕邪為患日久困脾,“則脾土受傷,濕土之氣下陷,是以脾精不守,不能化榮血以為經水,反變為白滑之物”[3]。
2.2 祛邪扶正并舉帶下病篇所涉及的36病,分別是三痼不通、五傷、七害、九痛、十二癥,主要因外感寒濕、溫熱之邪,內傷情志,陰陽不和,兼有飲食勞倦,子戶損傷,血氣乖戾所致。帶下病孫氏多用黃連、黃芩、黃柏等清熱燥濕之藥以祛邪,輔以灶心土、鹿茸、川芎、白術、甘草等甘味或溫性藥以達補益、滋腎填精培元之效,予赤石脂、禹余糧等收斂固澀之屬,阿膠、鱉甲等血肉有情之品以奏填精補腎之功。
3 妊娠病篇
3.1 妊娠病中治未病
3.1.1 未病先防“治未病”一詞最早見于《黃帝內經》,包括未病先防、既病防變、瘥后防復。男女的氣血運行規律基本相同,但女子因胞宮、產道等獨有的生殖臟器,月經、帶下、妊娠、產褥與哺乳等生理及病理特點,氣血尤易失調,故而治未病理論在婦人病應用方面必與男子有所差異,也更值得重視。妊娠期間胞胎依賴于母體氣血滋養,所以孫氏認為當“飲食精熟”“飲醴食甘”“宜食大麥”“酸美受御”“其羹牛羊,和以茱萸”,戒 “辛燥”“腥辛”之品,未病先防,以防小產、滑胎、胎萎不長等[4]。
3.1.2 瘥后防復孫氏針對不同妊娠時期傷胎再孕提出逐月養胎之法,以防再次傷胎,損傷母體與胎兒的氣血陰陽,具體治則與方藥見表1。

表1 孫思邈《千金方》妊娠病篇傷胎再孕逐月養胎治則方藥表
3.2 治養并重孫氏主要從產難、妊娠惡阻、養胎以及妊娠諸病四大部分論述妊娠病。濕邪為患是妊娠病的重要病因之一,母體脾虛,氣血生化乏源,釀濕生痰導致胃氣不和,胃氣上逆,發為妊娠惡阻,繼則導致胎動不安等病癥。然究其本源,肺為氣機升降之樞紐,肺氣失司,則脾胃失于運化。所以孫氏在《千金方·妊娠惡阻第二》中使用生姜、細辛、葛根等大量肺經藥,從根源上解決本類疾病的發生。妊娠期間血聚下元以養胞胎,母體呈現出一種陰血虛的狀態,此時若母本陰虛,極易出現陰虛陽亢,故孫氏在應用人參、白術、阿膠、麥冬等大量補虛藥的同時加用黃芩等部分清熱藥,防止出現子暈、子癇等疾病。
3.3 豐富妊娠脈象關于妊娠脈象,自《脈經》提出“往來前卻,流利輾轉,替替然與數相似”之后,人們大多認為妊娠之脈即滑脈,然孫氏在《備急千金要方》中明確提出,脈象平和虛緩亦為妊娠之脈象,極大地補充了人們一直以來對于妊娠則脈為滑脈的認識,對于后世婦產科學以及脈學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4 產后病篇
4.1 產后病之未病先防產后病指婦人在新產后及產褥期內發生與產褥或分娩有關的病證[5]。孫氏認為本病的發生與元氣大虛,分娩之時耗傷津血,感受虛邪賊風密切相關。產后多虛多瘀,瘀而日久則化熱,所以在治療本類疾病時,孫氏在羊肉、鯉魚、鹿肉、牛乳等血肉有情之品與黃芪等補虛藥中配伍知母、淡竹葉等清熱類藥物,以防瘀久化熱。
4.2 一藥多用,提出食養,調養為重產后病篇所用藥物多為肺腎二經藥物,其次為肝胃兩經。金水相生,乙癸同源,“胃為水谷之海”,此四臟腑兼顧,環環相扣,體現了孫氏嚴謹的用藥思維。婦人產后,氣血驟虛,易受外邪,孫氏在治療產后虛損類疾病時以溫陽散寒為治療大法,選用藥物最多者為桂心(肉桂)[6],其味辛、甘,大熱,利肝肺氣,溫中,通血脈,導百藥,主治心腹寒熱、冷疾,頭痛、出汗、腰痛等[7]。另一方面,肉桂藥食同源,可以作為調味品去除羊肉等的膻味,一藥多用。同時孫氏在治療產后虛損等疾病時選用了羊肉湯、獐骨湯、乳蜜湯等大量的食養方,以奏補益之功。
5 婦人雜病篇
5.1 氣為生之本婦人雜病篇所涉及疾病種類較多,主要包括婦人求子、盜汗、遺尿、斷產以及婦人積聚等多種疾病。該篇大量運用黃芪、人參、白術等補氣藥,氣是人體生命活動的基本物質,氣旺則血生,氣行則血行,氣耗則血散,氣血驟虧則生命危。
5.2 男女同調求子孫氏認為“凡人無子,當為夫妻俱有五勞七傷,虛羸百病所致,故有絕嗣之殃”,這在當時社會是一種突破性的認識。孫氏以女子調經養血,男子填精補腎為基本治療原則提出“男服七子散”“女服紫石天門冬丸”等為治法,以先攻邪再安正的序貫療法治療婦人求子。該思想在當時獨樹一幟,對后世治療不孕不育具有重要意義。
5.3 妙用丸劑《千金方》全文出現劑型最多者為湯劑,然而在婦人雜病篇中使用丸劑頻次最高。婦人雜病篇共有30余首方劑,以婦人求子為例,孫氏采用樸硝蕩胞湯迅速逐邪,外用法局部作用之外,其余18首方劑中包括15首丸劑和3首散劑。這與無子病情復雜,難以迅速痊愈密切相關,丸者緩圖,藥效綿長,適于本病。同時孫氏十分注重劑量,由少到多,隨時調整,療效較佳則繼用前量,若已孕則及時停藥,防止藥效峻猛,損傷母體與胎兒。
6 小結
孫氏將婦人疾病列于全書之首,為后世中醫婦科學的單獨分科奠定了理論基礎。在《千金方》中重視脾胃二臟,注重肝腎二經、調理氣血,同時善用血肉有情之品。其蘊含眾多臨床經驗之精華,如未病先防、瘥后防復的治未病思想;寒溫并用、風能勝濕理論的巧妙運用;妊娠病治養并重;產后病調養為先;一藥多用,藥食同調;牛膝等藥物、丸劑等劑型運用繁雜奇巧,不拘古法,靈活多變;豐富補充切診知識;男女序貫療法求子等內容對中醫婦科學有重大意義,值得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