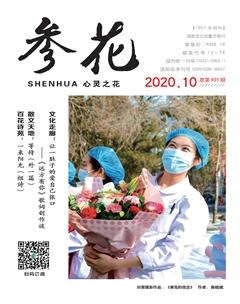海外讀者視野中的莫言小說特質
聶英杰 周景輝
摘要:莫言的小說縱橫恣肆、恢宏灑脫,不僅受到國內讀者的關注和喜愛,也引起海外讀者和研究者的重視和悅納,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莫言創作中傳統、現代、后現代藝術手段的綜合運用拓寬了小說的敘述場域,層出不窮的敘事革新為小說提供了強烈的藝術張力;其次,小說深植于古老雄渾的華夏文明,其中所蘊含的具有神秘色彩的東方傳奇引發了海外讀者對華夏文明的向往;再次,小說立足于樸素的民間世界,呈現美與丑、善與惡、愛與恨、生與死等人類共同情感和共性問題,具有普適性價值;最后,小說以深沉的悲憫和熱誠的祈愿禮贊生命、謳歌愛情、審視人性、沉思歷史,以灑脫的情懷書寫深刻的主題。
關鍵詞:莫言小說 敘事革命 東方傳奇 海外接受
自上世紀80年代從事創作以來,莫言就以其素樸溫情的創作格調引起了文壇老作家的稱贊。1985年開始,先后發表《透明的紅蘿卜》《金發嬰兒》《球狀閃電》《秋水》《紅高粱》《高粱酒》《爆炸》《歡樂》《十三步》《天堂蒜薹之歌》《豐乳肥臀》《酒國》《檀香刑》《月光斬》《生死疲勞》等作品,更以其先鋒前衛的書寫技巧和雄奇瑰麗的敘事風格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伴隨莫言小說在世界范圍內的廣泛傳播和頻繁獲獎,海外對莫言的研究與接受也全面升溫,其小說敘事的現代氣質、神秘的東方傳奇、變幻的時空之維、深邃的主題意蘊無不令人嘆為觀止。
一、敘事的現代氣質
莫言作為中國當代文壇先鋒作家中的一員,特別是1985年進行敘事革命以后,更以濃墨重彩的敘述,雄奇恣肆的風格而獨樹一幟,這與他大膽使用魔幻、戲仿、解構、拼貼等藝術手段展開小說創作密不可分。莫言敘事技巧的現代性特征不僅拓寬了小說敘事場域,給敘事革命提供了多種可能,也令海外讀者感到新奇和震撼。
莫言作品的英文譯者葛浩文認為:莫言是一位寓言與幻想的行家,多重敘事與文本轉換的高手。[1]荷蘭翻譯家馬蘇菲指出,“我喜歡那些敢于實驗創新的作者,如小說家莫言。莫言的小說技巧和結構非常多樣化,讀者仿佛可以看到、聞到、吃到、聽到和感受到書中所寫的東西。”[2]無獨有偶,意大利學者芭芭拉也認為莫言的敘述能夠特別精細地描繪日常生活,通過顏色、光線、味道、聲音和感知活動的描寫,帶給讀者身臨其境之感。莫言一直在試驗敘述的新形式,敘述者的不斷變化,不僅使意大利讀者關注表象的形式,而且更被其實質內容所打動。[3]
美國批評家托馬斯·英奇在《西方人眼中的莫言》中指出:“莫言最大的魅力在于小說技巧上的革新。”[4]他認為《紅高粱》采用全新的現代敘事方法,弱化傳統小說的情節關聯,引領讀者將小說各部分建立聯系。[5]其中不同人稱的交互使用,也給小說的敘事風格注入了活力。[6]《酒國》則將事實和虛構混融敘述,寓言般呈現了宏大主題。[7]《紐約時報》書評贊賞《酒國》的敘述風格,認為這部小說“從功夫小說、偵探小說、中國神話、美國西部小說和魔幻現實主義小說中借鑒多種敘述元素而形成了一個迷人的后現代大雜燴”。[8]法國讀者也認為《酒國》匯集怪誕想象、諷刺寓言和偵探小說為一體的敘述風格體現了世界各國文學思潮與流派的融合,彰顯了對社會風尚與潮流的審視和思考。[9]《酒國》于2001年獲得法國儒爾·巴泰庸外國文學獎,其頒獎詞指出:《酒國》這一實驗性文本,思想大膽,結構新奇,情節迷幻,人物魅惑,業已超出了大多數讀者的閱讀經驗。這樣的作品不見得被廣泛閱讀,但必定為刺激小說的生命力而持久發揮效應。[10]
上述評價贏得了莫言本人的認同,談及作品在法國受歡迎的原因時,莫言說:“法國是文化傳統較為深厚的國家,非常注重藝術創新。而創新也是我個人的藝術追求,我每部小說都在藝術形式上有新的嘗試和探索。《天堂蒜薹之歌》是現實主義寫法,《十三步》在形式探索上走得很遠。可能這種不斷變化符合法國讀者求新求變的藝術和審美趣味,也使得不同的作品引起不同層次、不同趣味的讀者的興趣。”[11]
莫言幾乎每部長篇小說都采用了獨特的敘事風格。《天堂蒜薹之歌》從三個角度講述同一個故事:瞎子張扣、敘述者和官方報紙分別以各自的方式和視角講述蒜薹事件。如同三個聲部的交響,多維度完整呈現了事件的全過程。[12]《生死疲勞》在保留中國古典章回體小說傳統的基礎上,大膽采用充滿野性想象和黑色幽默的民間敘事,通過西門鬧幾次三番生死輪回的悲歡故事,探尋和叩問荒誕歷史進程中生命的堅韌、人性的復雜以及存在的悲感。[13]哈佛大學王德威教授認為,《十三步》的表達方式更為不同,書名的“十三步”在書中并沒有明確指涉,它或許代表了生命中的不可測變數,又或許代表敘述邏輯上的逆反。讀者被籠中講述者拉進了故事之中,與他共同編織故事。在傾聽敘述及重述的過程中,讀者與籠中人撕扯、拉鋸……或欲言又止,或意猶未盡,或言不及義,而就在種種語言難盡其妙、而又不知所云的時刻,“歷史的味道,涌上心頭。”[14]
美國衛斯理學院宋明煒副教授認為:莫言縱橫恣肆、天馬行空的自由書寫,給中文小說帶來了驚喜。他的語調看似氣定神閑、悠然自得,卻又怪誕玄妙、變化萬端,仿佛一個被置于現實和敘述之間的神秘透鏡,令歷史和現實中荒唐、悲慘、尷尬的情境在小說中恍若奇幻境界,異人異境,如醉如癡。[15]
誠然,敘事革命與敘事的現代性彰顯了莫言對小說藝術創新的嘗試和探索,而莫言小說的形式創新絕非炫耀技巧、博取關注,其作品中深沉的文化歷史內涵、對社會人生的普適性思考、對人性問題的揭示和挖掘無不昭示著作家深沉的社會責任感與人道主義情懷。
二、神秘的東方傳奇
莫言作品中神秘的東方傳奇與悠久的華夏文明所構成的文化沖擊令海外讀者驚訝贊嘆、駐足流連。應該說,本土經驗與民族文化正是莫言千變萬化的小說形式下始終如一的堅守和秉持,而這份堅守與秉持在小說創作中又幻化成引人入勝的無窮風景。也許可以說,莫言作品的世界性影響和無窮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深植其中的深厚民族文化內涵。
2005年,莫言榮獲意大利諾尼諾國際文學獎,頒獎詞是:“作品植根于古老深厚的華夏文明,想象空間無限豐富而又科學嚴密,寫作思維獨特新穎,語言激烈澎湃而又柔情似水,表現了中國在近現代歷史進程中經歷的歡樂與憂傷,和平與戰爭,展現了愛、苦痛、團結、友善。”[16]頒獎詞聚焦莫言作品的四方面特色,即古老深厚的文明、豐富嚴密的想象、新穎獨特的思維、激情澎湃的語言。無疑,居于首位的“古老深厚的文明”既引領了后續諸種特征,又為之提供了營養和可能。
莫言小說法語版翻譯、普羅旺斯大學中國語言文學教授諾埃·杜特萊曾經指出,莫言即使在寫作中或多或少地融入了西方理論及思想,然而毋庸置疑,作品中最本質、最核心的部分是出自于中國本土。這種融匯中國民族文化和地方色彩的作品經過歲月沉淀,必將在世界文壇嶄露頭角,獲得屬于自己的一片領地。[17]
意大利學者芭芭拉認為,在莫言的文學世界中,讀者感受到了他曾經所經歷的、所感悟的生活及中國的傳統文化生活。莫言使用的材料引起了讀者對中國的歷史、地理、生活習慣、傳統故事、家族等中國獨特性的興趣。[18]莫言作品的意大利文譯者李莎指出,作品的異域風格與特色會帶領讀者感受一個不同以往的新鮮世界,接觸從未接觸和了解的東西能夠讓讀者產生興趣,豐富閱歷,增長見識,促進成長。“莫言小說能夠引領讀者快速進入角色,邁入非同凡響的時空領域,并從中發現個人獨特的領悟和感受。我認為這就是很多外國人喜歡莫言作品的原因。”[19]
越南學者阮氏明商認為,莫言小說民族性和世界性適切融合,使得莫言的作品超越國家疆域,獲得世界各國讀者的歡迎與喜愛。如《豐乳肥臀》中的上官魯氏,這一母親形象受到了東西方讀者的認同,而這一形象正是中華民族無私高尚而又堅韌倔強的母親形象的表征和凝華。[20]
莫言在談到其作品何以打動評委榮獲諾獎時說:“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作品中的文學素質。我的作品是中國文學,也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我的作品表現了中國人民的生活,表現了中國的獨特文化和民族風情。”[21]意大利翻譯家李莎也認為諾獎授予莫言最本質的原因在于,其作品能夠令讀者身臨其境,通過小說這扇大門真正進入中國這個東方國家,并且在閱讀過程中獲得頓悟和驚喜,產生共鳴:原來大家都是一樣的。[22]
從《民間音樂》到《爆炸》,從《豐乳肥臀》到《生死疲勞》,無論是古老神秘的東方故事還是靈異傳奇的中國式魔幻,無一不呈現華夏民族的文化基因和遺傳密碼,莫言將民族色彩、中國風格與文化魅力巧妙融合,以玄幻的故事和深邃的思想贏得了本土讀者的喜愛,也征服了海外讀者及研究者。
三、素樸的民間世界
自1985年發表小說《白狗秋千架》以來,莫言便將“山東高密東北鄉”作為其小說的文學地理,這個熟悉又親切的名字仿佛一下子打開了靈感的閘門,源于兒時的記憶及據此記憶所引發的想象源源不斷噴涌而出,素樸的民間風情裹挾著瑰奇玄幻的想象,席卷起深沉雄渾的歷史記憶,一路狂歡著傾瀉而來。
“高密東北鄉”承載了莫言對兒時鄉村生活的記憶,對此,莫言小說的英文譯者葛浩文說:莫言的所有小說都以其類似虛構的高密家鄉為場景。孩提時從祖父和親戚處聽來的故事為其豐富的想象添加了燃料……[23]莫言小說日文譯者之一吉田富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回憶起與莫言的交談:“莫言說自己是農民,我也是農民,我們出身一樣。我在日本農村長大,從小務農。我父親是打鐵的,莫言《豐乳肥臀》里就有打鐵的,小說里母親的形象和我母親的形象完全一致。” [24]
日本東京大學教授、著名翻譯家、莫言小說日文譯者之一藤井省三評價說:中國作家中,“描寫農民情感和倫理的作者當推莫言為翹楚。”[25]
“高密東北鄉”激發了莫言的原鄉想象。正如吉田富夫所言,“我到過莫言的故鄉山東高密,那里是一片一望無際的平原,既沒有小說中寫的斷壁懸崖和大河,更沒有漫山遍野的紅高粱,這些完全出自作者的想象,如此絢爛瑰麗的、自由自在的想象力真是令人拍手稱奇。”[26]
越南學者在全面閱讀莫言小說后指出:莫言作品中的故事大多發生在高密鄉,然而可貴的是莫言已經把這個有跡可循的鄉村,幻化成玄想中的抽象文學王國。高密鄉的故事和人物遭際,牽涉著全人類的整體性和共性問題。[27]
杜邁克以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為例,指出小說形象地再現了農民生活的復雜性,是上世紀最具想象力和藝術造詣的作品之一。作品系統深入地進入到中國農民的內心,引導讀者感受農民的感情,理解他們的生活。[28]
“高密東北鄉”這一神奇的地域承載了莫言太多的情感和記憶,也激發了他的靈感和想象,從這個意義上說,“高密東北鄉”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地域概念,更是莫言敘述動機的發源地,是作者心心念念的精神家園,是他發現世界的窗口,認知社會的突破口,傾瀉情感的爆發口,在這里,過去與現在、鄉村與城市、落后與進步、精致與粗糙、原始與文明相互碰撞、抵消、轉化、融合,他是莫言的童年記憶,更是凝結了他無限想象的原鄉,這里熱情似火,激情澎湃,敢愛敢恨,敢闖敢拼,勇武良善的鄉民何嘗不是華夏兒女的化身和寫照,這塊土地上發生的傳奇故事何嘗不是華夏歷史的微縮景觀?
“高密東北鄉”凝結了莫言的家國情懷和“人民作家”的使命,俄羅斯著名翻譯家葉果夫曾經指出:莫言是“人民作家”“中國人民的靈魂”,“他不必走入人民中間去了解人民,他的作品中包含了所有的民族特征……”[29]
莫言本人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接受采訪時也曾經表示,自己的作品表現了中國民族風情和獨特文化。[30]莫言說:“我的作品是中國文學,也是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我的文學表現了中國人民的生活,表現了中國獨特的文化和民族風情。我一直是站在人的角度上立足于寫人,超越了地域、種族的局限。”[31]
四、深邃的主題意蘊
如若單純追求藝術技巧的革新,或為傳奇而傳奇,可能會給讀者帶來一時的驚喜,但絕不會引發深入的思考和持久的關注。莫言小說的厚重絕不僅僅取決于藝術技巧的革新,也不完全在于其作品中的東方傳奇和家國鏡像,因其小說主題的深邃幽渺,導致閱讀的過程并不見得愉快流暢,但是當讀者合上小說的最后一頁,往往會產生一種審美上的愉悅和滿足,深入斟酌研討的熱情和興趣。
莫言小說的敘事風格千變萬化,故事情節千姿百態,作品的主題卻無不以深沉的悲憫和熱切的祈愿展現對生命的謳歌、對人性的審視、對歷史的沉思。這一切都深植于作者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人文關懷意識,而這也正是古今中外文學殿堂里經過時間洗禮、歲月沉淀、千淘萬漉仍然歷久彌新、綻放永恒光芒的經典之作所共有的特征。
莫言自陳,其作品是站在人的角度,立足于寫人,[32]不是為老百姓寫作,而是作為老百姓寫作。[33]正像所有跨越時空仍歷久彌新的經典著作的偉大創造者一樣,莫言豁達地站立于高密東北鄉蒼茫雄渾的土地上,以其深沉的悲憫情懷探看人性的幽微復雜,洞悉惡濁與良善、鄙俗與高貴、丑陋與美麗的更迭嬗變,表現普通人的善與惡、愛與恨、生與死,表達人類存在的悲或喜,無可奈何或春風得意,他的書寫酣暢淋漓、汪洋恣肆,看似橫無涯際,實則無不立足于人,以其強烈的人道主義情懷和氣度禮贊生命、審視人性、甄別善惡、表達祈愿。作為老百姓寫作的莫言,同情普通人生存的苦難和艱辛,并挖掘造成悲劇或困擾的性格局限和弱點,直擊人物的靈魂,引領人們正視自我的丑與人性的惡,實現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救贖。
莫言作品既有如《紅高粱》般對壯麗血性生命的引吭高歌,如《生死疲勞》般對個體生命與歷史沉浮緊張關系的深沉追問,如《檀香刑》般對生命內在的強悍與悲壯的狂歡抒寫,如《蛙》般對生命倫理的深層探論,如《酒國》般對人類生存的虛無與荒誕的叩問與思考,如《透明的紅蘿卜》般對美好生活和純凈理想的執著追求,如《白狗秋千架》般對故鄉的逃離與復歸,如《民間音樂》般對自我存在價值的找尋,也有如《豐乳肥臀》般對堅韌生命的熱情謳歌和對生命更迭與代際傳承的感喟與吟唱。他的小說不僅直面生命的蓬勃,謳歌生命的強力,也敢于正視生命的枯萎凋零,如《美麗的自殺》中的表妹、《歡樂》中的魚翠翠和齊文棟、《天堂蒜薹之歌》中的金菊,即便書寫生命的早謝也并不凄婉悲涼,而是以如打翻了調色盤般絢爛至極的書寫表達生命存在的價值和對生命隕落的深摯思考。他筆下的人物打破了善惡、甚至沖出了任何疆域、任何界限,更跨越了生與死。即便離開、故去、死亡,也仍然頑強地綻放生命的美感,借此引發人們對生命展開深刻的體認,而這種體認必將超越愛與恨,生與死。
參考文獻:
[1]Howard Goldblatt & Shelley Chan,Author Mo Yan earns praise for historical perspectives[OL].CHINADAILY,http:// www.chinadaily.com.cn/cndy/2012-10/10/ content_15805479.htm.
[2][荷]馬蘇菲.莫言小說荷文翻譯隨想——從《蛙》談起[J].吳錦華,譯.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1): 32-35.
[3][18]芭芭拉.在意大利看莫言[J].海南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27(06):29-31.
[4]M.Thomas Inge.Mo Yan:Through Western Eyes.[J]. World Literature Today,Vol.74,No.3(Summer,2000),pp.502(501-506).
[5]寧明.簡評莫言海外研究之熱點[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4):95-100.
[6][12][13]姜智芹.西方讀者視野中的莫言[J].當代文壇,2005,(05):67-70.
[7]寧明.西方文化視野下莫言作品的美國研究[J].理論學刊,2013,(12):122-126.
[8]張晶.框架理論視野下美國主流報刊對莫言小說的傳播與接受[J].當代作家評論,2015(3):166-179.
[9]劉海清.法蘭西語境下的莫言文學[J].當代作家評論,2017(2):194-200.
[10][16]趙麗萍,董國俊.從頒獎詞看莫言小說的域外接受[J].甘肅社會科學,2013,(04):234-237.
[11]莫言,李銳.“法蘭西騎士”歸來[N].新京報,2006-11-11.
[14]王德威.千言萬語 何若莫言[J].讀書,1999,(03):95-102.
[15]楊聯芬,孫郁,許紀霖,張閎,宋明煒,張莉,蔡元豐.名家談莫言[J].中國圖書評論,2012,(11):7-11.[17]鄭娜.莫言小說在海外的傳播與接受[J].重慶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26(01):105-110+116.
[19][22]莫言作品意大利文譯者談“外國人為什么喜歡莫言”[OL].搜狐新聞,http://news.sina.com.cn/ o/2012-11-01/114525487925.shtml.
[20][27] [越南]阮氏明商.論莫言小說對越南讀者的感召[J].南方文壇,2016(03):53-60.
[21][32]《南方周末》主編.說吧,莫言[M].南昌:二十一世紀出版社, 2012.
[23]葛浩文,吳耀宗.莫言作品英譯本序言兩篇[J].當代作家評論,2010(02):193-196.
[24]專訪莫言作品日文版翻譯吉田富夫:愿莫言獲獎后多多保重[OL].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 n/2012/1119/c1002-19623145.html.
[25][26][日]藤井省三.寄語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朝日新聞.2012年10月16日.轉引自王俊菊,主編.莫言與世界 跨文化視角下的解讀[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4.01:54-55.
[28]杜邁可,季進,王娟娟.論《天堂蒜薹之歌》[J].當代作家評論,2006,(06):55-61.
[29]王俊菊,主編.莫言與世界 跨文化視角下的解讀[M].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4.01:8-9.
[30]是我作品的文學素質打動了評委[OL].鳳凰網,http://culture.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2_10/12/181 93579_0.shtml .
[31]莫言獲獎感言:我的故鄉和我的文學緊密相關[OL].http://news.sohu.com/20121011/n354691234.shtml.
[33]王堯.“我是作為老百姓在寫作”[N].文匯報,2001-11-09(015).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5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后現代視閾下的莫言小說與海外接受研究”(項目編號:15BZW041)的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聶英杰,女,碩士研究生,大連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漢語國際教育系,副教授,研究方向:比較文學;周景輝,男,碩士研究生,大連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研究方向:英語語言學)
(責任編輯 王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