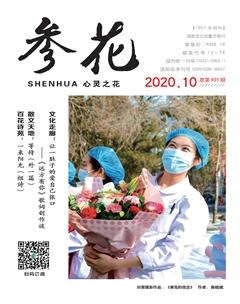“迷茫”還是“不迷茫”
摘要:許多學者從不同角度探討了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的“迷茫”主題。但是,小說的主題并非一直都是“迷茫”。本文借用認知詩學中圖形—背景理論,對《白象似的群山》中圖形與背景的動態轉換進行分析,推出小說主題并非一直是“迷茫”的,而是由“迷茫”轉為“不迷茫”,也展現了女性在理想和現實掙扎中的自我成長的過程。
關鍵詞:圖形—背景 迷茫 不迷茫
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寓意深刻,內涵豐富,其主題一直是文學評論界的焦點。國內學者從零度結尾的寫作手法、冰山一角的敘事風格、認知隱喻、概念整合、語用策略,以及倫理困境等角度分析了這部作品“迷茫”的主題。然而,真的“迷茫”嗎?筆者借助認知詩學中的圖形—背景理論對該小說進行分析,試圖通過動態的圖形—背景轉換來分析小說的圖形化,重新探索小說主題的意義。
一、《白象似的群山》中圖形—背景的刻畫
該小說圍繞著一個美國男人和女孩而展開,講述了他們在火車站候車的一段經歷。他們悠閑地喝著酒,聊到了“白象”,還因為“手術”而情緒失控。小說最后戛然而止,無聲的結尾卻蘊含了有聲的態度。
(一)小說對話的圖形化
圖形—背景理論源自心理學,由丹麥心理學家Edgar Rubin提出,并被格式塔心理學家們進一步發展形成。該理論提出:我們看到的東西都是由背景和圖形共同構成,容易辨認、引人注目的事物被當作圖形,不容易辨認、不引人注目的事物則被當成背景。熊沐清認為圖形的突顯和背景的弱化實現了積極而動態的文本閱讀過程。米衛文也認為:閱讀文學作品是讀者不斷地調整自己的注意焦點,在圖形與背景之間做出選擇并緊跟圖形的認知過程。這種認知有選擇性,會隨著故事的發展、敘事的方式和關注點的變化而變化。讀者就是通過不斷地構建圖形來實現對信息的感知和對小說的理解。
小說《白象似的群山》構建了男女主人公、白象、酒、手術和周邊環境等圖形和背景交替的畫面。縱觀整個小說,小而具體的男人和女孩之間在火車站的對話充當了小說的圖形,大而泛的周圍環境則成了小說的背景。那么,男人和女孩的對話是如何實現圖形化的呢?
首先,筆者以海明威的英文小說為研究文本,采用文體統計的方法對小說篇幅進行了統計。該小說總共1576字,而對話內容(直接引語)卻占到了1000字。那么,對話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整篇小說的圖形,達到了引起讀者注意的目的。對話是動態的,那么小說的圖形也就隨著對話內容而變化著。
其次,“河谷”“山崗”“車站”“房屋”等是大而泛的周圍環境,形成了圖形—背景理論中的背景,突顯了美國男人和女孩聊天的相對小而具體的動態完整特征圖形。
(二)“白象”和“手術”的圖形化
男人和女孩談論了天氣、山、酒、白象、手術等,但提到最多的是“白象”和“手術”。那么“白象”和“手術”也就依次突顯出來,作為對話中的圖形,其他則隱為背景。為什么提“白象”?什么“手術”呢?
起初,女孩心情不錯:她遠眺白雪延綿的山,說群山看上去像一群白象。女孩的動作和話語作為圖形聚焦了讀者的注意力,圖像化了女孩的美好希望。男人和女孩第一次提到“白象”時,男人漫不經心的回答在女孩心中種下了不滿的種子。他們第一次因意見不合而起了爭執。女孩選擇忍讓和退步,她轉移話題停止了爭論。可是,他們很快又因品酒而不悅,女孩第二次提到了“白象”。男人只是簡要地認可了女孩,而女孩卻自我否定起來。女孩想得到男人肯定的回答便第三次提到了“白象”。從女孩的自信,到疑惑,到自我否定,體現了女孩從抱有希望,到不確定,到逐漸屈服。“白象”到底代表了什么呢?為什么讓男人如此抗拒,讓女孩如此不知所措?
隨著故事的發展,讀者的注意力漸漸地聚焦在“手術”上。在第二次提到“白象”女孩自我否定后,男人終于表達了真實意圖:“那實在是一種非常簡便的手術,吉格”“甚至算不上一種手術”。讀者的注意力漸漸地聚焦在“手術”上。“手術”作為圖形突顯出來,其他的東西則隱身為背景,讓讀者不禁思考:這到底是什么手術呢?圖形化的信息讓讀者在閱讀時對故事進行了重新的梳理,為什么他們會在車站,為什么作者會寫到白象,為什么他們會產生矛盾,為什么他們要做“手術”。
接下來,女孩沒有回應,她只是看地板很長時間地思考該怎么辦。男人則喋喋不休地誘勸著女孩做“手術”。越是極力勸說,越是突顯焦急情緒。女孩猶豫不決,幾經勸說還是沒能下定決心,男人因此說: “我以為這是最妥善的方法,但你本人不是真心想做,我絕不勉強。”然而,他卻未打消自己的念頭,他心中并不迷茫,繼續強調“手術”的必要。女孩顯然沒被說服,她質疑如果她去做了,男人會不會像從前那樣愛她。即便男人給出了承諾,女孩還是不確定。接下來,女孩終于打破了沉默,一度想要尖叫,不愿意再繼續對話。男人和女孩矛盾的不斷升級得到了聚焦。其實女孩心里已有了主意。海明威沒有給出明確的故事結局,不知道最后“手術”做了還是沒做,他們何去何從,可女孩終究心里面認識清楚了男人和現實,而只有在清楚了的前提下才能做出改變。
二、“迷茫”轉向“不迷茫”的主題探究
結合認知詩學中的圖形—背景理論,筆者對《白象似的群山》進行了動態的圖形化分析。分析表明,小說中所謂的“迷茫”主題并不是貫穿始終的。
首先,從對話的內容來看,圖形從女孩隱晦地說著讓人費解的“白象”轉移到男人明確地提出“手術”上,故事情節由起初的不清晰變得越來越清晰。
其次,女孩從疑惑到自我否定到失望生氣,再到最后的坦然,也體現了女性心理成長的過程——變得越來越通透和堅強。最后能夠強顏歡笑實屬不易。她明白:企圖改變別人、寄希望于別人是沒有出路的,唯有改變自己和從容對待才是出路。不管結局如何,女孩已經下定決心要坦然面對。與之對比,男人對待“手術”的態度從未迷茫,他一直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想讓女孩干什么。
再次,小說開始并未提及男人和女孩的身份信息,而是簡單地稱他們為“男人”和“女孩”,但隨著故事的發展,我們知道了女孩叫“吉格”,這個名字在故事中突顯出來,緊緊抓住了讀者的眼球,讓人猜想這名字代表了什么,為什么開始不提及,既增加了故事的神秘感,又讓讀者有了更清晰的畫面感。從無名到有名,女孩的身份從背景轉化為圖形,同樣也是體現了從不明朗到明朗的轉換。
最后,小說開頭提到了等火車,結尾再次提到火車即將到來。火車終是要來,這毫不含糊,從最開始四十分鐘的等待到最后只剩下五分鐘,從猶猶豫豫到該走就走的決然,都體現了小說的主題由“迷茫”向“不迷茫”的轉換。
三、結語
以上探討是運用圖形—背景理論分析《白象似的群山》的動態圖形轉換過程,進而得出該小說的主題并不是一直“迷茫”的,而是從“迷茫”向“不迷茫”轉變,同時也展示了女性在理想和現實中掙扎成長的過程。
參考文獻:
[1]陳潔.解析《白象似的群山》中的“零度寫作” [J].鞍山師范學院學報,2010(3): 56-58.
[2]丁麗軍.《白象似的群山》與“冰山原則”——海明威小說藝術特色探析[J].南昌航空工業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3): 79-82.
[3]海明威短篇小說集[M].陳良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4.
[4]郎曉娟.評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的敘述視角[J].鞍山師范學院學報,2007(1): 84-86.
[5]米衛文.從認知詩學視角看海明威《一個干凈、明亮的地方》的主題[J].外國語文,2010(10): 22-25.
[6]倪麗萍.解讀《白象似的群山》中的倫理困境[J].湖北文理學院學報,2013(7):62-65.
[7]唐景春.概念整合理論對《白象似的群山》的解讀[J].外國語文,2013(3):51-53.
[8]熊沐清.認知文學研究最新成果薈萃——《牛津認知文學研究指南》述要[C].外文出版社,2018(7):21-46.
[9]熊沐清.語言學與文學研究的新接面[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4(4):299-305.
[10]熊沐清.從解釋到發現的認知詩學分析方法——以The Eagle為例[J].外語教學與研究,2012(5):448-459.[11]徐婷婷.《白象似的群山》視點差異解讀 [J].外國語文,2014(2):39-43.
[12]葉思琪.《白象似的群山》中的荒原式美學主題——以“象”“山”隱喻為載體[J].信陽農林學院學報,2018(3): 8-10.
[13]張婷婷.皚皚冰山,只露一角——談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的敘事策略[J].牡丹江教育學報,2014(5): 17-18.
[14] Rankin, P. Hemingways 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s. Explicator[J].2005(4): 234–237.
[15]Rizkiyani, F., & Lutfiyana, F. Darkness of Love as Portrayed in Hemingways Hills Like White Elephant [J]. The Journal of English Language Studies,2017(02) :132–140.
(作者簡介:唐珍珍,女,碩士研究生,海南外國語職業學院,講師,研究方向:英語教學、應用語言學)(責任編輯 劉月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