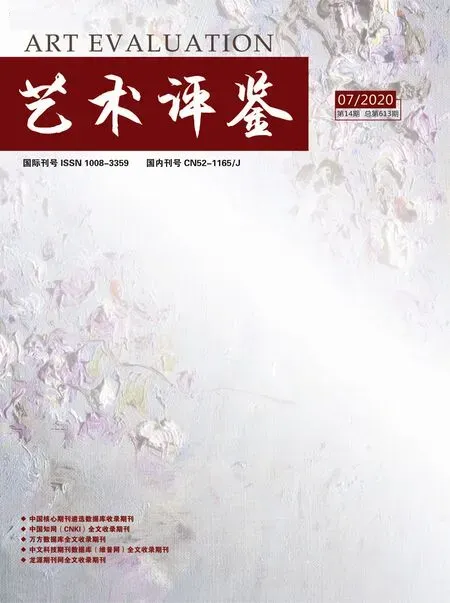江文也鋼琴作品《北京萬華集》的和聲調性特征
陳柏呈 華東師范大學
一、作曲家與作品概述
(一)江文也的生平
江文也(1910-1983)祖籍為福建永定,出生于臺北。1923 年赴日本求學,求學期間,因喜愛音樂,課余時間前往上野音樂學校選修聲樂與音樂基礎理論課程,曾受到齊爾品的贊賞和指導。1932 年在武藏高等工業(yè)學院畢業(yè)后,棄工學藝,專攻音樂,師從日本著名作曲家山田耕筰,并參加了日本新興作曲家聯(lián)盟,期間以自己名字的日語發(fā)音Bunya Koh 在日本出版了一些早期作品。1936 年跟隨恩師齊爾品到北平、上海訪問考察,接觸了大量的中國傳統(tǒng)音樂,遂對中國傳統(tǒng)音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38 年4 月,江文也受聘回到北平執(zhí)教,繼續(xù)創(chuàng)作大量作品。1983 年10 月,江文也在北京病逝。2001 年,江文也入選《新格羅夫音樂與音樂家辭典》(第二版,第13 卷)作曲家名人錄。
(二)江文也的創(chuàng)作分期
筆者參照于俞玉滋編訂的《江文也年譜》,將江文也的創(chuàng)作分為三個時期:
創(chuàng)作初期(1934-1938)為東京時期,江文也的音樂風格受到了20 世紀現(xiàn)代樂派和民族樂派尤其是德彪西、巴托克等作曲家的影響,以標題性音樂為主,常采用多調性或無調性,和聲大膽、織體簡潔,又自由地、創(chuàng)造性地融合了一些民族素材,個性鮮明,雖然有些作品間接利用民族音樂材料,但這時期所表現(xiàn)出的“國際性前衛(wèi)”仍然強于“民族性”。1934 年江文也創(chuàng)作的《臺灣舞曲》(Op.1),是其早期器樂代表作。它沒有墨守西方傳統(tǒng)作曲技法,而是在西方現(xiàn)代樂派作曲技術的基礎上融入了東方因素,刻畫了一個詩一般的境界。
創(chuàng)作中期(1938-1948)為北平時期,江文也轉向為對中國音樂風格的探索,作品大都以祖國的風土人情、唐詩宋詞為題材,樂風端莊含蓄,強調五聲音階線條結構,富有傳統(tǒng)音樂氣息。1938 年回到北平后,江文也陸續(xù)創(chuàng)作了多部交響樂、歌舞劇及鋼琴作品,可說是其一生創(chuàng)作生涯的頂峰,作品的風格也由早期的“國際性前衛(wèi)”改變成完全的“民族性”,以簡練的手法表現(xiàn),曲子呈現(xiàn)出簡潔、寬大、端莊、含蓄的效果,完全脫離第一個時期“標新立異”的色彩,更加成熟。1940 年他創(chuàng)作的大型音樂《孔廟大晟樂章》(Op.39),由迎神、初獻、亞獻、終獻、撤饌、送神六個樂章而組成,音樂風格和色彩都具有中國雅樂特征、配器手法則用現(xiàn)代作曲技巧,成功地做到了用西洋樂器再現(xiàn)中國古樂的精神。
創(chuàng)作后期(1949-1983)為北京時期,江文也的音樂風格轉向了中國民間音樂風格,創(chuàng)作素材多取用于民間音樂,曲調旋律以五聲音階為主,作曲風格返璞歸真,手法簡練。1950 年他創(chuàng)作的鋼琴套曲《鄉(xiāng)土節(jié)令詩》(Op.53)是他規(guī)模最大的一部鋼琴作品,它由表現(xiàn)農歷十二個月的不同節(jié)令風俗的十二首獨立樂曲構成,反映了作曲家樂觀向上的情緒,樂曲風格上追求鮮明的民間音調,帶著一種粗獷、雄強的氣質。1978 年他創(chuàng)作的《阿里山的歌聲》因為病癥突發(fā)而成為了他的遺作。
本文所研究的鋼琴作品《北京萬華集》為江文也創(chuàng)作中期(北平時期)的第一部作品(Op.22,1938 年)。
(三)江文也的鋼琴音樂風格
從以上提到的江文也的生平與創(chuàng)作分期來看,他的一生十分復雜坎坷,而這些經(jīng)歷也在他的音樂風格上留下了演變的痕跡。
江文也在東京時期時的鋼琴音樂風格,反映出臺灣、日本、西方現(xiàn)代音樂等多方元素的融合。到了創(chuàng)作中期,伴隨著他離開日本回到祖國,他的鋼琴音樂風格也發(fā)生轉變,明顯表現(xiàn)出一種回歸、尋根的意識,他盡量去回避和消除以前作品所受到的日本音樂的影響,而去探求有特色的中國民族音樂風格,邁出了較為堅實的一步。他創(chuàng)作后期的音樂風格,是繼續(xù)發(fā)生轉變的,其體現(xiàn)在中國民族音樂的風格正在不斷加深,返璞歸真,而原有的西方風格與日本風格相結合的特征則在迅速減少。
(四)鋼琴作品《北京萬華集》的創(chuàng)作背景及風格特點
在江文也的創(chuàng)作初期,他在日本成名,獲得了豐碩的成果,也得到很高的聲譽。但是1938 年,江文也放棄了在日本獲得的一切,毅然選擇回到中國大陸。他回到祖國之后,創(chuàng)作的第一部作品就是《北京萬華集》。相較江文也之前的作品,這部鋼琴作品明顯地表露出了追求中國音樂風格的意識,可以說,這部作品是他在音樂創(chuàng)作中尋找民族根脈,探索中國音樂風格的源頭。
鋼琴作品《北京萬華集》由十首帶標題的鋼琴小品組成。這十首小品的標題清楚明晰,表達了江文也初回祖國故土、深受北京風土人情的感觸,也表現(xiàn)出他的創(chuàng)作風格從追尋20 世紀的新寫作手法向探求中國傳統(tǒng)手法的轉變。
二、《北京萬華集》和聲調性特征
構成一部作品性格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和聲調性。和聲就像文章中的標點符號,能夠劃分音樂的句法以及段落,在音樂作品中是至關重要的;不同的和聲結構能夠表現(xiàn)不同的樂思,不同的和聲排列方式也能夠在音樂作品中形成不同的感覺。而調性則規(guī)定了一部作品旋律中各音的主次地位以及穩(wěn)定程度,同時也能表達一部作品的情緒。和聲的功能與調性密切相關,一旦離開或者取消了調性,和聲也就會失去它的功能意義。
江文也在《北京萬華集》中使用中國的民族式的旋律,與西方的調性及和聲語言融合在一起,使得這部作品的和聲調性十分特別。他使用的和聲基本上是非三和弦,并且大多數(shù)是非功能和弦。他的和弦用法,大多數(shù)是為了音響的模仿或音響的效果設計的,他偏好八度、五度、四度構成的和弦。而雖然他像很多20 世紀歐洲作曲家一樣不使用調號了,但是他對調性的觀念還是存在的,并沒有完全消失在他的作品中。
第一首小品《天安門》的調性為C 宮五聲調式,旋律極具歌唱性,在高聲部旋律的基礎上,配上平行四、五度“連續(xù)疊置”和聲,音樂雄偉而莊嚴。持續(xù)低音C 貫穿全曲,強音記號的添加及持續(xù)低音拍數(shù)的改變使得重音位移,與高音聲部形成了“重音異步對置”,這可以自由地產生東方的音響及節(jié)奏,描繪出極具印象派色彩的中國的大型鐘鼓聲。
第二首小品《紫禁城下》的調性非常多變,在G 徵五聲調式與C 宮五聲調式之間靈活轉換。縱觀全曲,平行四度的旋律進行幾乎貫穿了全曲。四度音程是中國音樂風格的典型音程之一,在作品中常常被用來表達東方的色彩。在A 樂段(1~30 小節(jié))的最后,此處是全曲的高潮,和聲分成了兩層:低音是宮音C 的分解八度,中聲部則是G 四五度和弦的持續(xù)。到B 樂段(31~54 小節(jié)),因出現(xiàn)了若干變化音,構成了德意志増六和弦。結尾的和聲與《天安門》遙相呼應,調性回到C宮五聲調式。
第三首小品《子夜,在社稷壇上》使用了復調的手法創(chuàng)作,是一首二聲部自由對位的五聲性音樂,調性為d 商五聲調式。傳統(tǒng)的功能關系——d 小調的屬七和弦到主和弦的正格進行體現(xiàn)在此曲的低音線條上,貫穿全曲。雖然此曲的低聲部是一條單線條旋律,但江文也將屬七和弦的小三音與大三音連著在裝飾音中使用,使得五聲調式的外音只出現(xiàn)在裝飾音里,這也使得功能和聲進行得到了“軟化”,因而低聲部的旋律仍然是五聲調性化的。
第四首小品《小丑》整體的調性是d 商五聲調式,中間出現(xiàn)了一些變化音,使得調性暫時轉到了#d 都節(jié)調式,在該曲的最后又回到了d 商五聲調式。從橫向來看,高聲部的G 音和A 音以銳利、明亮的二度關系來代替了偏音,低聲部的E 音和D 音也形成了尖銳的二度關系;從縱向來看,能夠發(fā)現(xiàn)該曲低、高兩個聲部交錯,形成了若干四度、五度音程,增添了民族和聲的色彩。進入A1 樂段,由于調性轉到了#d 都節(jié)調式,所以也構成了一些銳利的增、減音程,音樂風格變得荒誕、詼諧,而這也恰好與小丑的形象相符。
第五首小品《龍碑》的調性是C 宮五聲調式,主要是通過旋律的圍繞、強調并且最終結束在C 音所建立的。像這首小品一樣的依靠旋律建立調性在江文也這個時期的鋼琴小品中非常普遍,而很少使用和弦及和聲進行。
第六首小品《柳絮》的京劇旋律濃郁,旋律聲部是a羽五聲調式,低音聲部則一直持續(xù)d 音,總體調性為d商五聲調式。該曲以D、A 為支柱音,加之多次出現(xiàn)的倚音與多連音,類似于京劇的“緊拉慢唱”,京韻十足,在和聲與調性上都體現(xiàn)出民族風格的意蘊。
第七首小品《小鼓兒,遠遠地響》的調性以e 羽五聲調式為主,低聲部持續(xù)在E 音上模仿小鼓的聲音,而這個持續(xù)的E 音也是建立這個調性的主要音。并且,第5、6 小節(jié)加入了兩個變化音#F 和F,使得調性產生微妙的變化,產生了兩種西洋調式——e 自然小調與e 弗里幾亞調式。在這首小品的結尾,低音聲部變成了持續(xù)的D 音,而旋律聲部以一個長音E 結束,D、E 兩音組成一個大二度音程,這是傳統(tǒng)民歌所常用的和聲。
第八首小品《在喇嘛廟》無調性,是一首十二音風格的樂曲,富有玄幻的宗教色彩。江文也用低音區(qū)的持續(xù)低音A2以及中音區(qū)和高音區(qū)充滿大二度和小二度的和弦,來模仿東方鐘鑼鈴鼓等高低不一的打擊樂的聲音,充滿了縹緲、神秘的意境。
第九、第十首小品《第一鐮刀舞曲》《第二鐮刀舞曲》取材于一首江蘇民間小調。A 樂段的調性是C 徵五聲調式,B 樂段是A 樂段的變化反復,加入了兩個變化音#F 和#C 來代替了原調的宮音F 和徵音C,這使原調產生了變化,從旋律的感覺上,具有一定的都節(jié)調式風格。《第二鐮刀舞曲》的連接部是A 樂段的7一個倒裝再現(xiàn),旋律出現(xiàn)在低音聲部,出現(xiàn)了變化音,調性為e都節(jié)調式。從和聲方面看,這兩首小品大量地使用了五度疊置和弦來模仿打擊樂器的效果,頗有舞曲之感。這兩首小品在主題樂思的展開中,仍然偶爾會出現(xiàn)一些江文也早期鋼琴創(chuàng)作中帶有的日本調式的音調,以及西方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中運用增減半音自由改變主題音調的作法,這與他早期在日本的經(jīng)歷及受到的影響密不可分,但是這兩首小品的和聲調性整體上還是具有中國風格的。
通過以上的分析,將《北京萬華集》十首鋼琴小品的和聲調性列表如下:

根據(jù)上表可以看出,鋼琴作品《北京萬華集》除了第八首小品《在喇嘛廟》,絕大多數(shù)都使用了飽含中國民族風格的和聲與調性,旋律單純且富有歌唱性。這表現(xiàn)了江文也向探求有特色的中國民族音樂風格邁出了堅實的一步。
三、結語
江文也是一位極具個性的作曲家,他的音樂創(chuàng)作歷程與他曲折的人生經(jīng)歷是息息相關的。本文通過介紹作曲家江文也的概況以及鋼琴作品《北京萬華集》的創(chuàng)作背景及風格特點,并對鋼琴作品《北京萬華集》的和聲調性特征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從而進一步地了解江文也創(chuàng)作中期的創(chuàng)作風格與特點,也更深入地認識到這部作品的演奏風格以及演奏價值。
鋼琴作品《北京萬華集》是江文也回到祖國后創(chuàng)作的第一部作品,與他之前創(chuàng)作的作品相比,風格上出現(xiàn)了轉變。《北京萬華集》是一部結合了中西方和聲調性特征的鋼琴作品,表達了作者江文也對北京生活的感受。日本風格的旋律進行,在這部作品中已經(jīng)明顯減少,但也并不是完全消失;而且西方20 世紀的現(xiàn)代音樂創(chuàng)作技法仍然影響著他當時的創(chuàng)作。通過對《北京萬華集》和聲調性特征的分析可以看出,江文也對創(chuàng)作中國民族風格的音樂進行了初步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