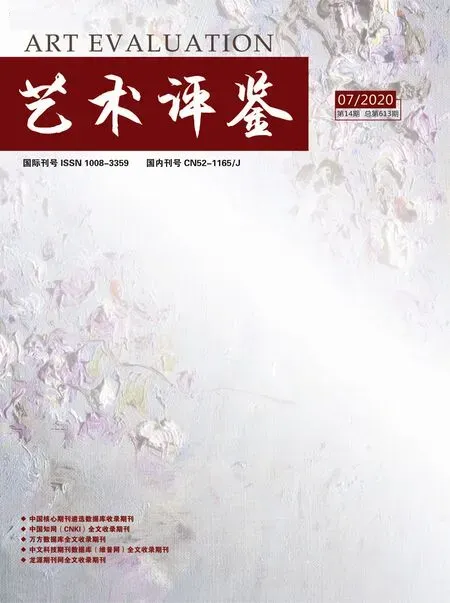泰國宮廷戲劇Khon 與中國戲曲的異同研究
楊琛 云南師范大學音樂舞蹈學院
“Khon”,是以泰國宮廷生活為基礎,在宮廷禮儀、婚喪嫁娶、宗教儀式中演出的,以印度敘事詩《羅摩衍那》中的《拉瑪堅》(羅摩王子之冒險)為題材改編創作的大型宮廷戲劇。該劇目前在泰國皇家宮廷劇院(Chalermkrung Royal Theatre)長期演出,是泰國最具特色的代表劇目。作品體現了印度史詩對泰國戲劇深刻的影響,也是印度史詩題材與泰國傳統藝術相融合的典范之作。它的產生經歷了漫長的發展歷程。
一、從《羅摩衍那》到《Khon》的發展歷程
公元1 世紀初,印度古代隱士瓦爾米克(蟻垤)的著名長詩《羅摩衍那》完成,據泰國人考證,在泰國開始有文字的13 世紀前后,從出土的碑文中有羅摩(拉瑪)大帝和拉瑪山洞名稱出現。《羅摩衍那》在泰國和東南亞各國流行甚廣,最先傳入爪哇、馬來亞,后又傳入柬埔寨、泰國、緬甸、菲律賓等國。開始都是用口頭說唱的形式流傳,后逐漸成為家喻戶曉、老幼皆知的作品。
到了曼谷王朝處于極盛時期的18 世紀前后,當政的泰國國王拉瑪一世正式把這一史詩翻譯成泰文;之后的拉瑪二世國王又根據印度的《羅摩衍那》、中國的《封神榜》《西游記》等神話故事,創作了具有泰國民族風格的歌舞劇《拉瑪堅》(Ramakien)。[1]《拉瑪堅》的內容和《羅摩衍那》相似,但其中場景移植到了當時的大城王國,人物名稱也都變成泰國式的。主人公成為大城國王的太子。只有神猴哈努曼保留了原來的名字。突出了猴子的形象,最終是大團圓結局。
拉瑪堅的故事體現了君主制的威嚴力量,它強調仁與德,也提出了“善良必將戰勝邪惡”的社會最高理想,并反映在誠信方面,信仰和價值觀、忠誠、謙虛、對長輩的尊重、堅持真實、感恩和勇氣等極富“正能量”的內容。而宮廷假面舞劇Khon 正是以這些腳本為基礎逐漸形成的。
(一)Khon 的詞源
Khon 是由阿育塔雅時代泰王國的古典宮廷假面舞劇發展而來。至于這個詞的詞源,目前還沒有明確的證據,只是在泰國著名的文學作品《Lilit Phralo》[2]中曾提及一個“Khon”的表演,這可以被認為是泰國歷史上“Khon”的最早記載,但是Khon 具體表示什么,目前沒有明確的結論,一般認為有四種可能的說法:
1.它源于印度一種膜鳴樂器的名字,它的出現和形制與鼓非常類似;
2.Khon 這個詞在印度泰米爾語中源自Koll,并與“goll” 或“golumn”非常接近,其含義與性別或從頭到腳的服飾和裝飾有關,這就與Khon 的表演形式相類似;
3.Khon 在伊朗源于“Zurat Khan”一詞,其含義是用于一個特定地域或為之歌唱的手持木偶或玩偶演出,這種表演形式也與Khon 起源時期的皮影戲形態的表演形式類似;
4.Khon 在高棉語詞典中有角色扮演的含義。[3]
這四種說法都是從世界不同國家對這一詞匯的詞源去研究和解釋的。筆者認為,后兩種的可信度相對更高,綜合起來,即可認為,Khon 是一種在特定地域通過玩偶或傀儡戲演出的有角色扮演的表演形式。這至少可以說明Khon 這一宮廷戲劇形式的起源形態。
(二)Khon 的起源
伴隨著對婆羅門教和印度教的信仰,Khon 作為宮廷戲劇的演出經歷了與泰國歷史和皇室的長期交融發展,它在贊頌和表達對君主的忠誠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它象征著國王的至高無上的力量。因此,所有的表演成分都與傳統的儀式有關,它類似于中國的儺 (有歌唱的)和日本歌舞伎的假面劇。故事冗長,全劇上演需要300—400 小時,通常只演片段。

圖1:Khon 的由來——泰國Nang Yai 皮影戲
泰國人普遍認為“Khon”是Nang Yai 皮影戲的分支,Nang Yai 皮影戲是泰國的傳統藝術形式,它一般都是運用一張牛皮,通過繁復的設計來做成《拉瑪堅》中的一個人物或一個場景的剪影,表演時,藝人們在白色幕布后面,一邊操縱影人,一邊用泰國流行的曲調講唱故事,同時配以泰國傳統的樂隊合奏。隨著故事的展開,皮影人物和場景越來越多。和我國北方傳統的皮影戲相比,泰國的Nang Yai 皮影戲特色在于,其皮影規模比我國的皮影相對較大,但是人物相對較單一,且每個皮影人物不像我國皮影可以細化到每個關節的活動,泰國皮影的活動狀態不夠靈活,這些都對后來Khon 的舞蹈動作造型產生重要影響。
Nang Yai 皮影戲基本的表演模式持續了較長的時間后開始有所發展。首先,為了能夠在白天演出,皮影由單一的色彩發展為彩色人物;其次,為了體現制作者高超的制作工藝,皮影人物也從“幕后”轉移到“前臺”;最后,皮影人物被真人替換,他們身著與皮影人物相似的服裝,并配以和古代書籍插圖與壁畫圖景相似的布景,模仿皮影人物的常規動作,最終促進了Khon 的基本舞臺造型和動作的形成。
Khon 的角色選擇主要包括四種:男性演員,需要有適宜的身材,手臂、腿、頸部、臉型都具有良好的比例;女性演員,則需要具有優雅的身軀和美麗的臉龐,其主要特征是手勢和體態都應當細膩而優美;惡魔,是角色中邪惡勢力的象征,具有強壯、勇敢和暴力傾向的特征,演員的身體應當相對普通人更高大,其手勢和體態更為夸張;擔當猴子的演員是劇中最重要的角色,雖然其手勢和體態源于自然,具有動物性,但是依然需要細膩和藝術化的表演,這也是泰國最復雜最難以駕馭的角色形象,演員應當具備敏捷的特點。
因此,Khon 的真人表演版本的誕生,重建了幾個世紀以來人類、惡魔、猴子的藝術表現形式。精致的服飾,尤其是面具,創造了古代文獻中描述的各種角色。經過一個時期的發展,一些系統性的習俗和規范最終形成。通過面具,連同絢麗多彩的服裝造型來辨別每一個角色。即使是年齡最小的觀眾也能依據服裝造型來分辨出強大的神猴哈努曼。程式化的布景也往往遵循傳統泰國繪畫的風格特征。
二、Khon 的表演形式與中國戲曲的異同之處
(一)角色扮演
Khon 的角色扮演形式采用面具和人臉相結合的形式,面具種類豐富,主要角色都采用套頭式的球形,其勾勒的色彩都具有嚴格規定,每個色彩都具有嚴格的意義。其中有三種最主要的面具:王子面具形制為假面,頭上戴著華麗的、珠光寶氣的尖頂金冠,而主人公拉瑪王子的面具色彩為代表泰國國色的、象征英雄、正義、力量的墨綠色,今天的Khon 中王子和王后的面具已取消,猴子面具頭部有象征猴毛的云圖頭飾,張嘴欲吼的面部刻畫,以及紅、藍、金、綠的繽紛裝飾與勾勒,表達了人們對大智大勇的神猴哈努曼的熱愛之情;羅剎面具眼圓睜、嘴齜裂的面容,則盡情表達著人們對惡魔的憎惡之情。戴著各異面具的演員在舞臺上表演,不同年齡、性別、身份、性格的人物特征便更加鮮明凸顯,人物表現則更加游刃有余。[4]一些動物(如鹿、拉戰車的馬等)則直接通過頭飾的方式加以呈現。面具根據角色不同而形制顏色各異,這與中國的京劇臉譜有著異曲同工之妙,但區別在于,中國京劇的臉譜是直接勾在臉上,這樣可以充分表現演員即刻的表情,尤其是眼神,而套頭面具則難以做到這一點。
(二)說白
今天的Khon 是一種面具舞劇,屬于啞劇的范疇,演員并不開口,男演員大都帶面具,由舞臺邊上的兩位演員代為說白,演員根據說白內容通過舞蹈和肢體動作來完成,不會刻意對口型。扮演者僅以身軀和四肢,通過巧妙的形體塑造和象征姿態所表達出來的肢體語言,把全部故事描述出來。演員通過不同的手勢表現不同的情緒,如愛情、害羞、傷心、生氣、拒絕等。這一點和西方舞劇有相似之處,西方的芭蕾舞也可以通過一些舞蹈動作來敘述故事情節或表現某種情緒。而中國戲曲(尤其是文戲)也具有這種特征,但中國戲曲的唱腔是戲曲中最重要的內容,具有相當復雜的門派體系,絕不會通過對口型的方式由其他演員代為吟誦或說白。可見Khon 并未以唱腔作為他們戲劇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伴奏樂器
Khon 的伴奏樂器和我國戲曲相似之處在于,都采用本國傳統樂器合奏的形式,而區別在于,Khon 的伴奏樂隊——皮帕特樂隊一般只有5—7 人,以氣鳴簧管樂器篳吶管、旋律性體鳴樂器高音木琴、低音竹排琴、低音圍鑼、高音圍鑼以及膜鳴樂器長鼓、手鼓、雙面桶鼓組成,可見體鳴樂器和膜鳴樂器占據了樂隊的主體,所以樂隊音樂的顆粒性就體現得十分明顯。樂隊的樂器基本涵蓋了所有音域,尤其是低音鼓和低音圍鑼強化了樂隊低沉的低音效果。
而我國戲曲樂隊的編制比較復雜,是根據演出的位置、場地和性質而定。“大樂隊”編制齊全,樂手多達五六十人,“小樂隊” 則只有十余人。戲曲樂隊又分為“文場”和“武場”,也就是現在的民族管弦樂和打擊樂。“文場”是為人物的唱腔音樂服務,“武場”則服務于人物的身段表演。因為兩者均為“服務性質”,因此,它們就必須以“伴”為主,不能喧賓奪主。[5]以京劇為例,以京胡等拉弦樂器作為主體旋律樂器,形成色彩鮮明的音響特征,以異常豐富的打擊樂器作為強化節奏的工具,再加上彈撥樂器作為伴奏,拉弦樂所體現出的持續的橫向旋律得以強化。樂隊樂器的演奏總體處在中高音區,形成了表現力異常豐富的樂隊形態。
(四)舞臺布景與音效視效
Khon 的舞臺布景基本采用寫實與寫意相結合的方式。寫實方面,今天的Khon 會搭建出森林、王宮等虛擬布景,在樂器伴奏的同時穿插了部分音效 (雷電交加)和視覺效果(光線變化);寫意方面,戰爭場面采用舞蹈和象征性的類似小雜技的形式表現雙方將領的打斗和糾纏的場面,這時舞臺布景就不存在,而以藝術化的打斗方式來實現。
這一點和我國戲曲區別較大,我國傳統戲曲在舞臺布景方面相對較為簡單,沒有虛擬的布景,也沒有音效和視效,完全依靠戲曲表演藝術家的能力來完成演出。而武生的打斗方面雖然也強調寫意,但是我國戲曲武打寫實性要遠遠高與Khon 的打斗,所謂“好拳師不如爛戲子”,要表達的就是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