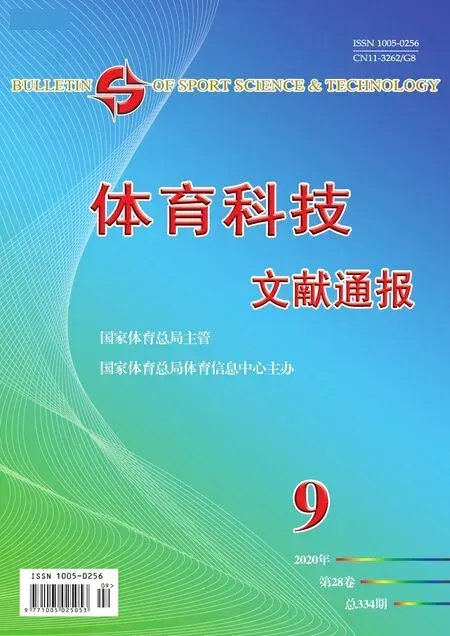新時代貧困代際傳遞消弭路徑的選擇
——基于民族傳統體育發展視角
梁巨志,張鐵雄
前言
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民族居住狀況呈現大雜居小聚居的形式[1]。新時代國民經濟穩態增長,但仍存在區域分布不平衡等問題,中東部和沿海地區經濟總量占據國民經濟的主體地位,西部和偏遠地區發展相對落后,貧困問題仍然存在。民族傳統體育原始的傳承模式是在血緣關系或者模擬血緣關系中進行,這種原始的傳承模式與貧困代際傳遞在傳承主體與文化等規律上呈現一致性。加之經濟發展區域分布的不平衡,貧困代際傳遞現象更容易在民族聚居地和偏遠地區產生。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在脫貧攻堅全面沖刺的關鍵時刻,應重視少數民族聚居區域與偏遠地區的優勢與特長,充分發揮自然資源和民俗文化價值,以助于經濟建設和扶貧工作的開展。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是我國體育強國戰略順利實施的重要推動力[2],通過合理運用契約關系傳承;挖掘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底蘊;細化產品服務等方法,推動民族傳統體育的發展,為我國創新發展提供持續動力,從而帶動少數民族聚集地和偏遠地區經濟、社會、人文的發展,為阻斷貧困代際奠定堅實的基礎。
1 民族傳統體育與貧困代際傳遞內聯性
如圖1所示,民族傳統體育與貧困代際傳遞在傳承機制、文化觀念及經濟領域存在內聯性,民族傳統體育大多以血緣關系和模擬血緣關系為基礎,在家庭和宗族中進行傳承,思想觀念及經濟屬性也隨之繼承人中得以延續;代際傳遞同樣是以血緣關系為指向,貧困屬性在家庭和區域中進行代際傳遞[3]。

圖1 民族體育傳承與貧困代際傳遞的內聯
1.1 機制內聯
我國民族傳統體育的傳承體系根源于農耕文明為主體的社會生產方式,主要是以血緣關系為主體,以家庭和宗族關系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傳承體系,這種血緣關系或模擬血緣關系傳承具有很強的內聚力,而貧困代際傳遞機制則同樣是在家庭和宗族成員間進行傳遞。新時代,隨著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血緣關系傳承逐漸顯現其弊端,在經濟較為落后的西部偏遠地區和少數民族聚集地,血緣關系的傳承模式成為區域發展的阻礙因素,繼承者或傳承人隨著身份和社會地位的繼承,貧困屬性也隨之復制,由此產生貧困代際傳遞。
1.2 文化內聯
中華民族傳統體育既是中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亦是我國體育事業的重要內容[4]。它不僅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人類社會珍貴的文化財產。但是受“巫術文化”、“宗族文化”等封建落后亞文化影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仍然停留在小范圍小區域間傳播。新時代,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地區貧困保護主義大行其道,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深厚內涵向外界滲透與傳播面狹窄,據此,封建落后的亞文化給貧困代際傳遞創造思想文化條件。
1.3 經濟內聯
體育產業是我國近年來的新興產業,其經濟價值在推動我國經濟建設的道路上是不可忽視的潛力因素。但民族傳統體育經濟在我國目前還存在“孤島”效益式的困境,多數民族傳統體育項目仍是附屬旅游等產業進行表演的形式,其經濟形式和成分單一。受地理限制和開發深度等因素影響,民族傳統體育仍停留在自娛自樂階段。關閉門戶,在封閉區域傳承和發展的民族傳統體育很難實現其經濟價值,繼承人僅僅依靠簡單的表演和運行模式,很難改變現實的生活狀況,貧困父輩的人力和經濟負資本通過代際傳遞累積形成子代的人力和經濟負資本,從而導致貧困代際傳遞[5]。
2 現存困境:民族傳統體育發展中貧困代際傳遞本質
2.1 貧困的潛匿代際主體
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在新時代背景下逐漸得到重視,而受我國民族傳統體育的原有傳承模式限制,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發展緩慢,甚至一部分傳統體育項目逐漸失傳。這種原有的傳承模式就是依據血緣關系或是模擬血緣關系進行傳承,傳統的傳承模式往往會保留具有民族特色的習俗,形成一種不成文的鄉規民俗和文化基因,如代際傳遞。這種傳承模式實質是隱匿的代際傳遞遺傳劣變,與貧困代際傳遞產生的機制相契合,都是地位的再生產[6],父輩的社會地位很大幾率上會復制在子代一輩,形成巨大的傳承慣性力。
2.2 貧困的代際亞文化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源于田野生活,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傳承下來的寶貴財富,是中華民族文化自信思想價值理念的基石。新時代,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穩定高速發展中,民族體育文化逐漸體現其價值,但與之相應的遺傳基因劣變的亞文化如:“巫術文化”、“宗族文化”等亞文化也在肆意傳播[7]。亞文化其本身的封建性和封閉性為貧困代際傳遞創造思想基礎,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在地域保護主義的籠罩下,向外界延伸傳承受阻,傳統體育文化未得到有效的繼承和發展,具有珍貴價值的傳統體育文化資產面臨失傳窘境。
2.3 貧困的代際經濟孤島
具有民族特色的傳統體育項目是推動我國經濟建設的新鮮血液,但是受經濟孤島效應影響,少數民族聚集地與偏遠地區呈現區域經濟產業結構低水平同構狀態,要素流動受阻、市場發育程度低、地區市場承受能力薄弱,是阻礙區域共同市場的形成并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障礙[8]。目前,更多的傳統體育項目是附屬旅游產業進行開發,是以表演和觀賞性進行開發和發展,其淵博的經濟價值功能未得到充分開發,在某種程度上將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項目發展置于新的生態經濟孤島困境之中[9]。
3 消弭路徑:發展民族體育阻斷貧困代際傳遞
3.1 革新傳承機制,共建民族繁榮
受社會環境變遷和民族傳統體育自身發展需求等因素影響,民族傳統體育傳承從血緣關系轉換為契約關系的傳承是必然趨勢[10]。這一觀點著名法學史家梅因認為:從身份依附關系到契約關系變更的完成,是社會運動的進步前提,建立權利和義務關系是推動人類文明發展的內生動力。在社會環境的變遷中,民族傳統體育項目逐漸由血緣傳承模式轉換為民族體育賽會、民族體育產業、學校教育、社團組織等契約關系的傳承。民族傳統體育傳承從血緣關系到契約關系的轉變,實質上是民族傳統體育自身發展的需要。
新時代,為規范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弘揚民族體育精神,以政府主導的體育賽會制定了相關法律法規,對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項目賽會轉型和傳承有了明確的規定,為少數民族傳統體育的傳承構建了必要的制度保障[11]。其次,體育賽會推動下傳統體育項目傳承同學校教育的結合,促進了民族體育傳承人從社會培養到學校培育的轉變,并以制度性的規定確立,比如基層教育機構對民族傳統體育項目以校本教材和大課間活動的形式在學校開展等。
契約關系是一種理性的精神選擇,基于法律強制性,學習者有義務和責任發展民族傳統體育。契約關系傳承方式從傳承制度和觀念意識方面進行創新,使得有機會接觸和學習民族傳統體育的人口基數增加,拓寬了傳統體育繼承人選擇途徑,能有效規避貧困代際的主體選擇。原始的血緣關系傳承模式的繼承人有機會脫離世俗壓力,根據自身特長和環境因素更科學的規劃發展方向,同時傳承競爭壓力的增大,使其必須不斷提升自身能力,這樣將更有利于自身綜合素質的提升,從代際主體本身的綜合素質提升上,阻斷貧困代際傳遞。與此同時,傳統體育項目賽事的開展,能夠為傳統體育項目繼承人或宗族帶來一定經濟效益,為阻斷貧困代際傳遞奠定經濟基礎。
3.2 挖掘文化底蘊,構造文化共贏
面對貧困亞文化的制約,我們需要提升民族傳統體育文化自身影響力和拓寬傳播途徑,激發脫貧內生動力。首先,在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本身影響上,加強民族體育文化傳播內容的深度發掘,整合傳播信息,使少數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為公眾所能帶來的價值和功用能夠清晰完整地展現在公眾面前,激發民眾對少數民族體育文化的興趣,建設大眾喜聞樂見的民族體育文化信息[12]。
其次,在傳播途徑方面,應充分運用社會傳播媒介。例如通過網絡等方式積極拓寬合作路徑,大力宣傳我國少數民族體育文化。把握經濟全球化帶來的發展機遇,合理處置全球化帶來的文化沖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學習其創造經濟價值的經驗與運作模式,同時,切合文化自信的思想價值理念,應該秉持對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認同與尊崇,深度發掘傳統體育文化的深厚底蘊。
第三,推進民族傳統體育活動服務體系進展。根據大眾對健身的需求,建設民族傳統體育健身指導服務體系,合理地進行科學健身指導,不斷提高大眾參與民族傳統體育健身的人數。還要定期不斷培養城鎮社區的社會體育指導員、體育志愿者隊伍,有效發揮他們在開展民族傳統體育健身時的指導和文化宣傳方作用。
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經歷幾千年的傳承和發展,已是世界體育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通過對民族傳統文化價值的再挖掘和傳播途徑的合理利用,契合全面健身服務體系建設的推進,使民族傳統體育文化影響力延伸,進一步發展民族傳統體育文化,激發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內生力動力。推進民族傳統體育文化的發展,將為世界體育文化大繁榮締造新輝煌。
3.3 打破消費“孤島”,共享民族經濟
打破消費“孤島”效應,根據消費心理特點細化民族傳統體育經濟發展具體要素,促進民族傳統體育產業發展和實現民族經濟共享。首先,提高民族傳統體育項目開放度,減弱孤島效益影響對區域經濟增長至關重要。貧困地區經濟的整體發展,應先考慮到生產要素的價值化,扶貧攻堅政策的著力點要進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地發展民族傳統體育價值,將民族傳統體育產業鏈打通、拉長,實現民族體育產業與市場的對接[13]。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推動其內部市場的相互開放,形成區域共同市場,是提升區域經濟競爭力、實現繁榮的保證。
其次,根據消費學相關理論知識,在產品開發營銷等方面做出針對性調整。充分考慮消費者的消費需求,調整體育產品的開發設計方案,促進體育購買行為和參與度的經濟價值實現。加強對產品的設計、包裝和運營策略調整,完善和創新體育產品營銷策略,刺激消費者對民族傳統體育的消費欲望,開發各種合適的參與性體育項目,迎合消費者的興趣愛好,開發不同的體育產品,滿足不同人群的興趣愛好,促進消費者對民族傳統體育產品的消費。
新時代民族傳統體育產業發展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新興動力源,剖析孤島效益與消費規律特點,提升民族傳統體育本身內涵,加速民族傳統體育產業的發展,必將打破民族傳統體育消費“孤島”效益的局限,為推動民族傳統體育經濟價值的實現與共享提供具體的實踐路徑,為阻斷貧困代際傳遞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
4 結語
總而言之,新時代賦予我們新的時代使命與歷史機遇,把握歷史機遇發展民族傳統體育,是阻斷偏遠地區和少數民族聚集地貧困代際傳遞的具體路徑選擇;亦是弘揚民族文化價值,堅持文化自信的具體實踐表現;更是維護民族團結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偉大夢想的具體策略指引。從民族傳統體育發展視角入手,某種意義上整合了阻斷貧困代際傳遞的多元困境,一定程度上為扶貧工作從體育扶貧領域拓寬路徑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