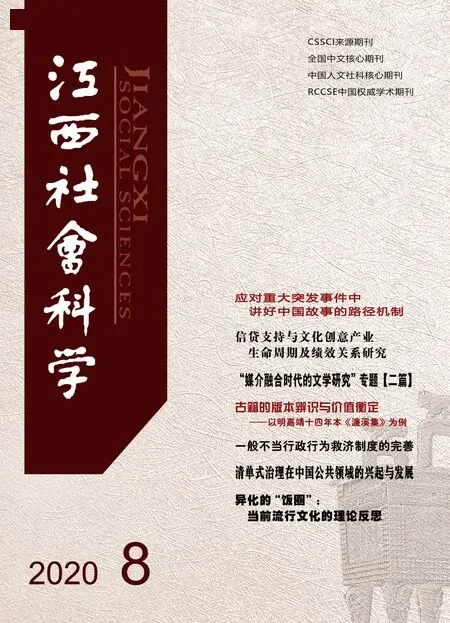唐代河湟地區的道路交通
■張弘毅
河湟地區位于青藏高原東北部,是連接中原地區與邊疆的中間地帶。在這一地區,漢代以來逐漸形成羌中道、湟中道、河南道。東晉之后南北分立,戰亂頻仍,傳統絲綢之路由于河西走廊閉塞而失去功能,此時羌中道、湟中道、河南道等數條道路一度承擔起溝通東西方交流的功能。隋代,特別是唐代以來隨著全國統一,傳統絲路得以暢通,河湟地區道路作用也隨之降低。伴隨吐蕃政權的崛起,以及唐蕃關系的深入,經行河湟的道路載體則主要轉變為唐蕃古道。唐蕃古道河湟段承載了唐蕃之間的雙向交流,尤其在政治交往、宗教傳播、地理分界、軍事戰略、文化交流上發揮重要影響。
我國西北河湟地區四通八達,東起關中,西至西域、中亞,南達青藏高原、南亞次大陸,北通大漠,形成了數條國際商道。漢代以來形成的羌中道、湟中道、河南道三條道路均經行河湟地區①,并曾在較長時期內代替傳統絲綢之路,承擔起中西方之間的往來與交流。唐代,吐蕃政權崛起,唐蕃接壤,唐蕃古道開通,河湟地區道路交通產生巨大變化。本文試圖以唐代河湟地區為中心,以羌中道、湟中道、河南道、唐蕃古道為載體,對河湟地區道路的緣起、形成、轉變進行研究,并進一步論述唐代河湟地區道路的價值影響,如有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唐以前河湟地區道路交通的形成與演變
據文獻記載史前時期河湟地區就已經存在道路交通,國內著名考古學家裴文中曾提出,“湟水兩旁地廣肥沃,宜于人類居住;況湟水河河谷文化發達,由史前至漢,皆為人類活動甚盛的地方,史前遺物,到處皆是,與渭河及洮河流域相類似”,因此他推斷“漢以前的東西交通,是以此為重要路線”,而且“是主要之道”。[1]
史上關于經行青海境內最早的道路記載見于先秦時期的《穆天子傳》:
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剞閭氏。天子乃命剞閭氏供食六師之人于鐵山之下。壬寅,天子登于鐵山,乃徹祭器于剞閭之人。……丙午,至于鄄韓氏。爰有樂野溫和,穄麥之所草,犬馬牛羊之所昌,寶玉之所□。丁未,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乃命六師之屬休。……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天子乃樹之竹,是曰竹林。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天子于是休獵,于是食苦。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黃鼠之山,西□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2](卷二,P12-13)
其中的鐵山、鄄韓氏、平衍、玄池、苦山等地均位于現今青海省境內,據任乃宏考證,周穆王所行經的鐵山就是柴達木盆地西北部的錫鐵山,鄄韓氏即平衍,在今天的青海格爾木市烏圖美仁鄉西北部的臺吉乃爾湖南岸,玄池就是今天青海省的尕斯庫勒湖,苦山就是阿爾金山以西的噶斯池。最終目的地西王母之邦位于今新疆和田市東南。[3]這條道路又被稱為“穆天子道”,也就是最原始的青海路雛形。西周立國于關中,該條道路途經柴達木盆地,前往南疆,其勢必要先通過河湟谷地,因此穆天子道為先秦時期首條途經河湟的道路。編撰于這一時期的《山海經》中也存在青海境內相關地名記載,間接襯托出青海路的存在。②此外,先秦時期羌人祖先害怕秦國的勢力,離開河湟地區,遠遁西方。對此,吳焯認為這支羌人部落向西遷徙數千里,一部分留在了青海柴達木盆地,一部分定居于新疆塔里木盆地,還有一部分甚至西遷至蔥嶺以西的帕米爾高原地區。[4]由此可見,先秦時期經行于河湟的交通要道已初步形成,為漢代羌中道與南北朝時期河南道的雛形。
漢代在穆天子道的基礎上衍生出羌中道,據史書中記載:“(張騫)留歲余,還。并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為匈奴所得。”[5](卷六十九《張騫傳》,P2689)張騫第一次出使西域返回中原時,為了躲避北方匈奴,而放棄經行河西走廊的傳統絲綢之路,選擇繞行西羌部落返回中原,這里的南山一般是指西域的昆侖山,其具體路線為沿昆侖山麓進入羌地,羌地就是指青海境內的河湟及附近地區,再從河湟地區東行進入關中,這條道路國內學界稱為“羌中道”③,源自于其通過河湟地區羌人聚集區。
東晉時期,河隴一帶政權林立,互相攻伐,征戰不斷,導致河湟地區道路不通暢。這一時期從關中地區前往西域的傳統絲綢之路時斷時續,因此人們多選擇經行河湟地區的“湟中道”④,該路最早開啟于漢代,為漢羌之間的交通要道,在漢代只是作為羌中道的輔道,實際作用并不明顯。東晉隆安三年(399),僧人法顯等人從長安出發前往天竺尋求戒律,他們經行河湟前往西域所行走的便是湟中道的北線。《法顯傳》中對此的記載是:“初發跡長安,度隴,至乾歸國夏坐。夏坐訖,前行至耨檀國。度養樓山,至張掖鎮。張掖大亂,道路不通。張掖王殷勤,遂留為作檀越。”[6](P2-3)這里的乾歸國是指西秦(其統治區域大致在甘肅西南、青海東部一帶),耨檀國是南涼(其統治區域就是青海東北河湟地區以及甘肅武威),養樓山位于今西寧市北部的土樓觀,由此可見法顯等人所選擇的道路就是湟中道東線(從隴西到西寧)、北線(由西寧至張掖)。此外,劉宋初年僧人法勇(曇無竭)等一行二十五人經河湟前往西域求經也選擇湟中道,《高僧傳·曇無竭傳》對此有記載:“曇無竭……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入流沙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蔥嶺、度雪山……進至罽賓國。”[7](卷三《曇無竭傳》,P93-94)這里的河南國便是河湟地區的南涼,海西郡便是王莽所置的西海郡(今青海湖一帶),流沙一般是指青海省境內的柴達木盆地。可見曇無竭一行人所選擇的是湟中道的東線、南線。
南北朝時期,南北政權對峙,南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受到阻礙,由此而衍生出了“河南道”⑤。河南道最初被稱為羌氐道(因其沿線均為羌、氐兩族聚居地),又稱雍涼道(因其溝通雍、涼兩州),最早見于史書記載是在《后漢書·西羌傳》:“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種人附落而南,出賜支河曲西數千里,與眾羌絕遠,不復交通。”[8](卷八十七,P2875-2876)河湟地區羌族祖先為了躲避秦人的兵鋒,向黃河以南遷徙,遠離湟水谷地。關于河南道的具體分段,陳良偉在其著作《絲綢之路河南道》中將其劃分為西蜀分道、河南分道、柴達木分道和祁連山分道四條主道,并且細分成岷江支道、白龍江支道、河源支道、隆務河支道、洮河支道、柴達木南支道、柴達木北支道、扁都口支道、走廊南山支道九條支道,羌人選擇的遷徙路徑就是河南道中的白龍江支道。關于河南道的具體走向,學界對此有許多詳細的考證。筆者將河南道具體路線歸納為如下:從成都北上,抵達甘肅天水,過秦安、渭源,到達臨洮,再從臨洮往西行,到臨夏,然后向西北方向行走,進入青海東部,經西寧,一路入北川,經門源縣老虎溝、祁連縣扁都口,進入河西走廊;另一路則去青海湖、柴達木盆地至南疆。其中河湟谷地為河南道西、北兩路分道前的主要地區。
西晉末年崛起于河湟地區南部的吐谷渾政權在南北朝時期一直充當了河南道上的向導、保護者以及貿易中介人的角色,例如,《魏書·吐谷渾傳》記載“蠕蠕(即芮芮)、嚈噠(即滑國)、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犄角相接”[9](卷一百三,P2310)。《梁書·諸夷傳》記載滑國“與旁國道,則使旁國胡為胡書,羊皮為紙……其言語待河南人譯而后通”[10](卷五十四,P812)。吐谷渾最初建國以“河南”為號,此處“河南人”即吐谷渾人,可見吐谷渾在當時南朝與漠北、西域諸國的交往過程中扮演了中介人的角色,同時吐谷渾人在各國商業貿易中擔任翻譯與向導這些工作。這一時期,河南道也為北朝所使用。《洛陽伽藍記》中記載北魏時期胡太后遣宋云、惠生等人赴西域,其中明確提及河南道走向:“初發京師,西行四十日至赤嶺……發赤嶺西行二十三日,渡流沙,至吐谷渾國。路中甚寒,多饒風雪,飛沙走礫,舉目皆滿,唯吐谷渾城左右緩于余處……從吐谷渾處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從鄯善西行一千六百里至左末城。”[11](P169-171)由此可知北朝使用的河南道東段與南朝的不同,北朝是從中原地區西向抵達河湟北部湟水谷地,與羌中道走法相似,南朝則是從西川成都北上穿越松潘高原與甘南地區抵達河湟南部黃河谷地,而雙方在西段上的行經路程基本一致,均是從河湟以西穿越柴達木盆地,翻越阿爾金山,抵達西域。見圖1。

圖1 羌中道、湟中道、河南道走向
由以上所述可知,西周時期開辟的穆天子道是以河湟為中心的西北地區道路交通的原型,此后發展為漢代的羌中道,南北朝時期又逐漸形成湟中道與河南道,在傳統絲綢之路因戰亂而閉塞的情況下,這些道路溝通中原與西域的往來,同時河湟地區也發揮了西北地區交通樞紐的作用。
二、唐代河湟地區道路交通的演變
隋唐統一南北,經行河西走廊的傳統絲綢之路得以暢通,此時經行河湟的諸條道路的交通功能隨之減弱,成為輔助性道路。此后隨著吐蕃崛起,以及唐與吐蕃交往的深入,唐蕃古道河湟段得以形成,成為唐代河湟地區的主要道路。
隋煬帝時期吐谷渾為隋朝吞并,隋在吐谷渾故地設郡置縣,遷徙輕罪徒居住,史書記載:“大業五年,(劉權)從征吐谷渾,權率眾出伊吾道,與賊相遇,擊走之。逐北至青海,虜獲千余口,乘勝至伏俟城。帝復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12](卷六十三《劉權傳》,P1504)“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12](卷八十三《西域傳》,P1845)劉權所選擇的道路便是漢代的羌中道,而遷徙輕罪徒的道路則是湟中道。可見,這一時期兩條道路分別發揮了行軍與遷徙的作用。
唐初吐谷渾政權再度建立,貞觀九年(635)唐伐吐谷渾,深入河源與西域,羌中道與湟中道再次發揮了行軍作用:“貞觀九年,詔特進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兵部尚書侯君集為積石道行軍總管,任城王道宗為鄯州道行軍總管,仍為靖副;涼州都督李大亮為且末道行軍總管……李大亮又俘其名王二十人,雜畜數萬,至且末西境。或傳伏允西走,渡圖倫磧,欲入于闐。將軍薛萬均率輕銳追奔,入磧數百里,及其余黨,破之。”[13](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傳》,P5298-5299)羌中道、湟中道在唐初再次發揮了軍事作用。但此后隨著河西走廊與傳統絲綢之路的極度繁榮,一度成為輔助道路,影響下降。
在羌中道等道路作用減弱與轉變的同時,唐代出現另一條經行河湟地區的道路——唐蕃古道。“唐蕃古道”最初源于唐代中后期人們對于唐與吐蕃間交通往來所經行道路的命名,而唐初由于河湟地區存在著吐谷渾政權,因此唐蕃之間的交往通常需要假道吐谷渾,直至唐高宗龍朔三年(663)吐蕃徹底吞并吐谷渾,唐與吐蕃才全面接壤,成為事實上的鄰邦,唐蕃兩地之間的交往才得以暢通。但據國內學者考證,在長達數千里的唐蕃邊界上,雙方相互交通往來的道路并非只有一條,筆者歸納目前學界對于唐蕃古道的考證,主要有兩條,一條為唐代的官馬大道,即從唐都長安出發,途經甘肅、青海、藏北,到達吐蕃都城邏些。另一條也從西安出發,即唐代長安,途經今天的寶雞、天水、文縣、松潘、金川、丹巴,沿魚通河谷,經康定、木雅,到達金沙江河谷,再經鄧柯、玉樹,過通天河河谷,穿越唐古拉山口,經過黑河,抵達拉薩。其中最為當前學界所認可的則是通過河湟地區的唐代官馬大道,《新唐書·地理志》鄯州鄯城條下特別注明的唐代官馬大道西段走向,其與當今青藏線走向大致符合。該條道路全程三千公里,其中有將近一千七百公里的路段在今青海境內,尤其是以河湟地段經行的道路為主線。而鄯城以東線路,均在大唐境內,實際上是臨洮以東的唐代涼州道連接河湟古道而成,與漢代羌中道的東段基本一致;鄯城以西路線主要在吐蕃域內,是由河湟境內道路連接邏些至河湟道路而形成。
唐蕃古道的東段,即長安至鄯城段,自漢代以來就為人們所頻繁使用,西段鄯城至邏些段,最早源自于隋末唐初吐蕃與黨項、多彌、吐谷渾等政權的屢次交往過程。據《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大事記年》中記載:“贊普墀松贊巡臨北方,吐谷渾與漢屬之……與吐谷渾二地納賦。……此后三年,墀松贊贊普之世,滅‘李聶秀’……此后六年,墀松贊贊普升遐。”[14](P145)據此可知吐蕃贊普墀松贊(即松贊干布)去世前十年,約在公元639年左右⑥,吐蕃與河湟南部的吐谷渾政權有接觸,并且吐蕃贊普曾親臨北方吐谷渾。由此可見,西段早在唐貞觀十三年就已通行。另據《舊唐書·吐蕃傳》記載吐蕃第一次對吐谷渾的戰爭,“貞觀八年……弄贊遂與羊同連,發兵以擊吐谷渾。吐谷渾不能支,遁于青海之上,以避其鋒,其國人畜并為吐蕃所掠。于是進兵攻破黨項及白蘭諸羌”[13](卷一百九十六《吐蕃傳》,P5221)。可見早在貞觀八年吐蕃就利用唐蕃古道西段作為進軍路線兼并黨項、白蘭、吐谷渾等政權。在此之前吐蕃、吐谷渾等政權之間經行西段的記載并不見諸史籍,但兩地之間的往來是否早已存在,筆者推測可能性極大,據《雅隆尊者教法史》記載,“吐蕃第二十九代贊普仲年德茹與青木氏魯杰恩姆措所生王子是一盲童,取名穆隆貢巴扎,王子稍長,遵照父王遺言,請來阿夏(即吐谷渾)的醫生治好了眼睛”[15](P34),仲年德茹為松贊干布曾祖輩,生活于6世紀初。可見雅隆部落時期的吐蕃與吐谷渾之間已經互相往來,那么可以推測通行兩部落之間的道路就是最早的唐蕃古道西段,且早在唐代以前就為人們所使用。
關于唐蕃之間對唐蕃古道全程的首次使用可見史書記載:“貞觀八年,其贊普棄宗弄贊始遣使朝貢。……太宗遣行人馮德遐往撫慰之。”[13](卷一百九十六《吐蕃傳》,P5221)可知太宗時期,唐朝與吐蕃有了首次使臣往來,那么唐蕃古道勢必為其所經行,但其所行經的唐蕃古道是否為唐代官馬大道,抑或是川藏道,仍舊難以定論。直至貞觀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禮部尚書、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節送公主于吐蕃。弄贊率其部兵次柏海,親迎于河源。……及與公主歸國”[13](卷一百九十六《吐蕃傳》,P5221)。這是正史中記載的關于文成公主入蕃和親的事件,也是史書記載的唐人第一次全程行走唐蕃古道。
總之,唐代,由于河西走廊的暢通,傳統絲綢之路得以恢復,原先的羌中道、河南道、湟中道等道路作用減弱,成為輔助性道路。同時由于吐蕃政權的建立,唐蕃之間交往的深入,經行河湟的道路載體也由羌中道等道路轉變為唐蕃古道。
三、唐蕃古道河湟段形成的主要影響
唐蕃古道河湟段位于整條道路的中心位置,即從青海東部的龍支城(今青海民和縣境內)至西部赤嶺(今青海湟源縣日月山)一段,連接起原羌中道東段(自關中至河湟)與河湟南至吐蕃段。其不僅溝通了中原與羌、藏,乃至南亞各國間的交往,在宗教傳播、地理劃界、軍事作戰、文化交流等方面也有重要影響。
(一)溝通了中原與藏地、南亞地區的交往
據國內學者統計,自唐太宗貞觀八年至唐武宗會昌二年(842)的209年間,唐蕃之間使者交往共計290余次,吐蕃使者180余次,唐朝使者100余次。[16]其中,有名有姓的唐朝使者共計55人,吐蕃使者52人。[17]另一說唐朝有名有姓使者為15人,吐蕃為19人。[18]可見唐蕃官方交流頻繁,唐與吐蕃使者均頻繁經行唐蕃古道,平均每年就有1~2次唐、蕃使者往來于此道上。而唐蕃古道河湟段屬于主干要道,承接了古道東段與西段,唐穆宗時期劉元鼎入吐蕃就經過河湟,“明年,請定疆候,元鼎與論訥羅就盟其國,敕虜大臣亦列名于策。元鼎逾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隳。……至龍支城……過石堡城,崖壁峭豎,道回屈,虜曰鐵刃城。右行數十里,土石皆赤,虜曰赤嶺”[19](卷二百一十六《吐蕃傳》,P6104)。現今河湟當地留有大批唐代遺址,如青海民和縣境內的龍支故城,湟源縣境內的綏戎故城、石堡故城、克素爾城址等均為唐蕃古道河湟段沿線遺存。
唐蕃古道南向延伸為蕃尼道,即唐初吐蕃與泥婆羅之間的往來道路,唐初使臣不僅前往吐蕃使用唐蕃古道,而且去往泥婆羅等國也選擇唐蕃古道結合南向延伸的蕃尼道,同時這些國家派遣使臣前來朝貢也選擇此道。《舊唐書·泥婆羅傳》記載:“貞觀中,衛尉丞李義表往使天竺,途經其國。……永徽二年,其王尸利那連陀羅又遣使朝貢。”[13](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傳》,P5290)《舊唐書·天竺傳》記載:“貞觀十五年尸羅逸多自稱摩伽陀王,遣使朝貢。……太宗以其地遠,禮之甚厚,復遣衛尉丞李義表報使。”[13](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傳》,P5307)太宗、高宗時期王玄策出使泥婆羅、天竺等國也曾選擇該條道路。1990年6月在西藏自治區吉隆縣境內發現了一塊額題為“大唐天竺使出銘”的摩崖石刻碑銘,碑銘上有“屆于小楊童之西”一語,國內以陸慶夫、霍巍為代表的學者均認為此是王玄策行走蕃尼道的證據。可見唐代以河湟段為中心的唐蕃古道不僅承接了中原與藏區兩地聯系,而且溝通了唐朝與南亞各國之間的交往。
(二)方便東西方僧侶通行
唐蕃古道河湟段不僅為唐代官方交流頻繁使用,僧侶也經常經行此道。僧人道宣生活于唐初,其所編纂的《釋迦方志》成書于永徽元年(650),其中關于唐蕃古道及蕃尼道記載到:
自漢至唐往印度者,其道眾多,未可言盡。如后所紀,且依大唐往年使者,則有三道。依道所經,且睹遺跡,即而序之。其東道者,從河州西北度大河,上漫天嶺,減四百里至鄯州。又西減百里至鄯城鎮,古州地也。又西南減百里至故承風戌,是隋互市地也。又西減二百里至清海,海中有小山,海周七百余里。海西南至吐谷渾衙帳,又西南至國界,名白蘭羌,北界至積魚城,西北至多彌國。又西南至蘇毗國。又西南至敢國。又南少東至吐蕃國。又西南至小羊同國。又西南度晅倉法關,吐蕃南界也。又東少南度末上加三鼻關,東南入谷,經十三飛梯,十九棧道。又東南或西南,緣葛攀藤,野行四十余日,至北印度泥婆羅國。[20](卷上《遺跡篇四》,P14)
文中關于唐蕃古道的記載雖沒有正史記載詳細,但大體上也反映出唐蕃古道西段的走向。道宣在《釋伽方志》中述及泥婆羅國時稱“比者國命并從此國而往返矣”,可見唐代出使泥婆羅的使臣均選擇唐蕃古道結合蕃尼道這條路線,說明該條路線道短易行⑦。《釋迦方志》中對于唐蕃古道經行河湟段的敘述過于簡略,但從文中的一些地名上可以看出與《新唐書·地理志》中古道西段路程基本符合,如漫天嶺指甘肅臨夏境內的小積石山,鄯州即青海樂都,鄯城鎮即西寧,承風戌據考證位于今青海化隆縣以西,清海則是今天青海湖,吐谷渾衙帳大致位于今青海共和縣、興海縣一帶,這幾處地名均位于河湟境內,其行程也與正史中記載的唐蕃古道西段走向一致。此外,《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與《大唐青龍寺三朝供奉大德行狀》中還記載了唐太宗時期的玄恪、慧輪,唐高宗時期的玄太,以及唐德宗時期的悟真四位新羅僧人通過此道進入天竺求法。可見唐蕃古道河湟段對于促進東西方宗教交流具有重要意義。
(三)間接促成唐蕃劃界
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733)唐蕃雙方訂立盟約,以唐蕃古道西段上的赤嶺為兩方分界處,嶺東屬唐,嶺西屬蕃:“開元二十一年……金城公主上言,請以今年九月一日樹碑于赤嶺,定蕃、漢界。樹碑之日,詔張守珪、李行祎與吐蕃使莽布支同往觀焉。”[13](卷一百一十二《李暠傳》,P3336)“詔御史大夫崔琳充使報聘。仍于赤嶺各豎分界之碑,約以更不相侵。”[13](卷一百九十六《吐蕃傳》,P5231)后世將開元年間唐蕃在此地所立分界碑稱為“開元分界碑”。而赤嶺位于河湟地區西南,是唐蕃古道必經之地。赤嶺以東的河湟谷地平均海拔只有二千米左右,氣候溫和,雨水較多,是青藏高原東北部適宜農耕的區域,唐代位于這片區域的古道沿線城址有龍支城、湟水縣、鄯城、臨蕃城、白水軍、綏戎城、定戎城、天威軍,均為唐朝控制;而赤嶺以西的青南高原平均海拔在四千米以上,氣候干燥,空氣稀薄,適合游牧民族畜牧,古道沿線驛站有王孝杰米柵、莫離驛、公主佛堂、那錄驛等,均屬于吐蕃勢力范圍。張力仁認為唐蕃赤嶺劃界是雙方經過一番政治、軍事較量之后,依據地理條件最有利原則進行的勢力范圍劃分。[21]可見唐中期以后唐蕃之間界限的設置是以古道經行的河湟地區為中心,按照實際地理條件最有利原則所進行的劃分,唐蕃古道河湟段的走向也是根據自然環境所形成,可以說是間接促成了唐蕃雙方界限劃分。
(四)影響唐蕃軍事交鋒
唐蕃古道的開辟使得河湟地區成為唐蕃交往必經之地,同時也成為雙方軍事交鋒的前沿。唐穆宗時期大理卿劉元鼎出使吐蕃時,對于唐蕃古道經行河湟段有過描述:“元鼎逾成紀、武川,抵河廣武梁,故時城郭未隳。蘭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戶皆唐人,見使者麾蓋,夾道觀。至龍支城……過石堡城,崖壁峭豎,道回屈,虜曰鐵刃城。”[19](卷二百一十六《吐蕃傳》,P6104)其中龍支城即位于今青海民和縣古鄯盆地北古城⑧,石堡城學界多認為位于今青海湟源縣日月鄉哈拉庫圖村北部的石城山⑨。劉元鼎通過唐蕃古道前往邏些,在河湟地區所見到的古城遺址在唐前期均屬于唐朝控制范圍內,安史之亂后為吐蕃所占據,唐中期以來雙方圍繞河湟地區進行了長達百年的爭奪,其中石堡城更是成為唐蕃之間四次爭奪的焦點。唐蕃古道河湟段在唐中期以前對唐蕃雙方而言,屬于軍事交通要道,雙方都極力爭取該片區域,河湟地區的戰爭基本上都是圍繞古道沿線進行,可見唐蕃古道河湟段在唐代發揮的軍事戰略作用非常明顯。
(五)促進文化交流
唐蕃古道開通后,唐蕃之間頻繁往來,“金玉綺繡,問遣往來,道路相望,歡好不絕”。唐蕃古道不僅是唐代漢藏、東西方來往的交通要道,也是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流通的主動脈,大量的使節、僧人、商人往來經行古道,不僅促進唐朝與吐蕃的經濟、社會發展,也雙向傳輸漢藏甚至東西方文化。貞觀十五年文成公主和親吐蕃,帶去了大批漢地文獻典籍,據《西藏王統記》記載公主嫁妝中包含有“經史典籍三百六”,“漢地告則經三百”[22](P68),足見數量之多。吐蕃對于漢文化表示出極度的喜愛,不僅在服裝上仿效,而且渴望學習漢文化,“弄贊……釋氈裘,襲紈綺,漸慕華風”[13](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傳》,P5222),并“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又請中國識文之人典其表疏”[13](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傳》,P5222)。唐高宗時期吐蕃向唐朝請求賜予各類工匠與蠶種,“高宗嘉之,進封為賓王,賜雜彩三千段。因請蠶種及造酒、碾、硙、紙、墨之匠,并許焉”[13](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傳》,P5222)。唐中宗時期吐蕃請求唐朝允準吐蕃貴族子弟入長安國子監學習,“神龍元年九月二十一日,敕吐蕃王及可汗子孫,欲習學經業,宜附國子學讀書”[23](卷三十六《附學讀書》,P667)。唐玄宗開元十八年吐蕃使臣來長安“請《毛詩》、《禮記》、《左傳》、《文選》各一部”[13](卷一百九十八《西戎傳》,P5232)。可見吐蕃對漢文化的渴望,唐朝基本上予以滿足。
唐蕃古道的開辟不僅使漢文化傳入吐蕃,吐蕃風俗也逐漸傳入內地。如唐中后期吐蕃“赭面”習俗傳入中原,在內地開始逐漸流行。白居易的《時世妝》中對長安婦女“赭面妝”有生動的描繪:“圓鬟無鬢堆髻樣,斜紅不暈赭面狀。昔聞被發伊川中,辛有見之知有戎。元和妝梳君記取,髻堆面赭非華風。”詩中出現的“斜紅不暈”樣式,與吐蕃“赭面”中面頰兩側涂抹對稱的斜條形紅彩幾乎完全相同,陳寅恪認為:“白氏此詩所謂‘面赭非華風’者,乃吐蕃風氣之傳播于長安社會者也。”可見唐代中期吐蕃風俗經由唐蕃古道傳至長安,并為時人所接受。據考證,天竺的制糖技術也通過唐蕃古道傳入內地,并得到改進。
四、結論
漢代在先秦穆天子道的基礎上逐步形成了羌中道,此后又逐漸衍生出湟中道、河南道。南北朝時期由于戰亂導致河西走廊閉塞,傳統絲綢之路河西道不通,人們一度采取羌中道、湟中道、河南道進行替代,逐漸形成了以道路為載體,河湟地區為樞紐的交通體系,溝通中原與西域等地區之間的聯系。其中位于河湟南部的吐谷渾一度扮演了貿易中介人和向導的角色。
隋唐以來隨著全國的統一對河湟道路產生雙重影響,一方面因為河西走廊的暢通,傳統絲路得以恢復,河湟境內各條道路的功能相對降低。另一方面因為西北地區的統一,隋唐兩代先后與吐谷渾接壤,從而產生摩擦,羌中道、河南道均經行吐谷渾境內,因此無法暢通,而湟中道的功能則由于傳統絲路的恢復而失去,故而這一時期河湟境內道路主要發揮著行軍、遷徙作用。
唐太宗時期吐谷渾政權的臣服與唐蕃古道的開辟,使唐朝與西部少數民族政權的交往趨于頻繁,其中河湟谷地成為唐蕃古道的中心地區,主要承擔起溝通唐與吐蕃交往的功能,而原河湟境內的諸條道路功能為傳統絲綢之路所替代,唐代河湟地區的道路交通載體由羌中道、湟中道、河南道演變為唐蕃古道。
唐蕃古道的開通不僅方便了唐蕃之間的接觸,而與南部蕃尼道的連接,更是溝通了唐朝與南亞各國間的往來。其中唐蕃古道河湟段發揮了重要影響,首先該段成為唐代各方使節、僧侶通行的區域,尤其成為唐蕃雙方使節頻繁往來的地段。其次河湟段所處地理位置間接促成唐蕃雙方劃界,成為雙方按照實際地理條件最有利原則劃界的依據。再者河湟段是唐蕃戰爭的主要地區,雙方圍繞這一具有特殊軍事戰略作用的區域展開近百年的爭戰。最后唐蕃古道的開通不但使漢文化傳入藏區,也使吐蕃風俗甚至南亞文化傳入內地,河湟段作為古道中心起到了一種雙向交流作用。總的來看河湟地區交通結構在唐代發生了重大轉變,由漢代以來多道路的東西往來演變為唐代的單條道路南北交通。
注釋:
①本文中的河湟地區一般指青海東北部湟水谷地與南部的黃河谷地。
②任玉貴在《〈山海經〉與青海地域文化的新發現》(《中國土族》2014年第4期)一文中認為:“昆侖山就是青海湖東部的野牛山,日月山為青海湟源縣境內的日月山,積石山位于青海循化縣東北部,互市國位于今天青海互助縣,皇水就是湟水河,另外文玉樹、不死樹、五彩斑斕的玉樹均指青海玉樹地區。”從以上這些古地名所對應今青海省境內的各處地點,可見先秦時期河湟地區已經有羌族先民活動,并且存在溝通湟水谷地與隴右、青南等地的道路。
③初師賓在《絲路羌中道開辟小議》(《西北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2期)一文中認為“羌中道”是從今甘、青交界的湟水區域西行,穿過古羌人聚集地,或北出祁連山,抵達張掖與河西道交接;或繼續西進,出柴達木西緣,抵達新疆若羌、且末連通絲路南道。該條道路為河西道的輔道。此外,我國考古學家黃文弼、夏鼐、馮漢驥等在民國時期和新中國成立后在此方面做過深入研究,黃文弼將此道稱為“吐谷渾道”,初世賓認為應該稱之為“羌中道”更為妥當。
④崔永紅等編著的《青海通史》中對此湟中道走向有明確記載:“從關中過隴西,渡黃河進入湟水流域,經鄯州(今青海樂都)抵達西平(今青海西寧),并向西、向南、向北輻射,西接羌中道,南連河南道,北面通過樂都武威道、西平張掖道至涼州。人們把湟水流域這條四通八達的主干道稱之為湟中道。”
⑤由于該條道路必經青海黃河河曲以南之地,故史稱“河南道”,又因為吐谷渾國又被稱作“河南國”,因此史書中將貫穿于吐谷渾的道路稱為“河南道”或“吐谷渾道”。據《南齊書·芮芮虜傳》中記載“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同書同卷《河南傳》中記載:“遣給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并送芮芮使。至六年乃還。”
⑥據《舊唐書·吐蕃傳》記載“永徽元年,弄贊卒”。但根據王堯考證,漢地文獻所記永徽元年(650),當是由于道路阻滯,喪報到達時間較晚,致有此誤差。墀松贊實際去世年份當為公元649年。
⑦宋人志磐在《佛祖統紀》一書中又提及此道:“東土往五天竺有三道焉,由西域度蔥嶺入鐵門者路最險遠,玄奘法師諸人所經也;泛南海達詞陵至耽么立底者,路差近,凈三藏諸人所由也;《西域記》云:‘自吐蕃至東女國,尼婆羅、弗栗恃、毗離邪為中印度,唐梵相去萬里,此為最近而少險沮。’且云:‘比來國命率由此也。’”
⑧陳小平在《唐蕃古道》中根據《元和郡縣圖志》《太平寰宇記》所稱龍支“西南有龍支谷,因取為名”,“唐述窟(即炳林寺石窟)在縣南龍支谷”,今青海民和故鄯盆地北段的一座古城(青海文博部門命名為北古城)出土的唐代遺物與挖掘的夯土層,判斷此城為唐代的龍支城。
⑨此說最初來自于民國時期吳景敖《西陲史地研究》,以王忠、周偉洲、陳小平為代表的學者多同意此說。民國初期的周希武先生與日本藏學家佐藤長,以及后來的曾毅、溫彬、永吉等國內學者認為石堡城位于青海湟源縣哈拉庫圖村東南的營盤臺。包壽南、李振翼、孫顯宗等人則認為石堡城位于甘肅卓尼縣羊巴村。現國內學界多認可第一種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