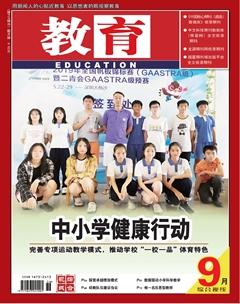2020高考:新素質教育解讀
宋亮

2020年高考成績公布后,老牌名校南京一中引起部分家長指責。細心的家長發現,南京市二十九中的中考入學成績只有589分,遠不如一中的631分,但二十九中的2020年高考高分段人數竟然是一中的兩倍還多。家長認為一中教學強度不夠,過于強調素質教育而導致孩子應試能力不足。但是,也許他們并不知道,新時代素質教育已將來臨,高考改革已經明確:不再一考定終身。
“小鎮做題家”
與此事相對應的,是最近火起來的一個詞:“小鎮做題家。”
2020年夏季,上海媒體出現一篇文章《我是小鎮做題家:當年市狀元考入復旦,如今可能是同屆中薪水最低》。這位畢業于復旦大學的女生,這樣回憶自己的經歷:大一的時候,我發現大學里學的內容和高中完全不是一個套路。高中時,我的數學成績很好,但心里清楚我并不擅長數學,數學成績好,純粹是因為做題。我做的題量是別人的二至三倍,高考時每一道題,我看一眼就知道題目的原型,或在哪本習題集里做過。我會做,并不是因為我知道背后的原理,而是因為我把答案背下來了。
到了大學,我也試圖這樣做,但根本行不通,因為題海戰術的前提是:別的啥也不做,就只是做題;而大學里要做的東西太多了,時間太少了;不像高中時,高二就把課程上完了,剩下一年半就是做題。高中時我曾經熟悉的題海戰術,在大學里完全失敗——高數、概率論與數理統計等課程一塌糊涂,多次掛科。我讀的專業其實是“專業大類”,大一結束后會根據GPA細分專業,其中金融學、經濟學是最熱門的專業,而我被分到了沒人想去的公共事業管理專業。進了這個專業的都是大一時成績墊底的學生,我二點幾的績點成了全班第一,最差的績點大概只有一點零。
跌跌撞撞畢業了,完全沒有實習經歷的我,慌不擇路地進入一家比特幣公司給老總當秘書。大學時生活費雖然不多,但也不需要為生計發愁,所以看待這座城市時總帶著浪漫美好的濾鏡。開始工作后,才一下子看清殘酷的事實。后來我從公司秘書,變成了市場部專員,然后又跳槽去做新聞編輯,現在跳到留學中介做翻譯,薪水很低,但好在不是很辛苦。1月份好不容易漲薪,3月份因為疫情公司全員降薪,畢業后辛苦工作4年,一點一點漲薪,一夜之間又回到了剛畢業時的薪金水平。現在,我可能是復旦那一屆里薪金最低的畢業生之一吧。
認知與分歧
南京一中的這次高考,總成績其實并不差。差就差在高分考生數量上輸給了“小鎮做題家”。南京一中公布的喜報中,一本升學率達95.34%,如果不考慮清北率或者985、211錄取率,這個成績其實也不算差,但是家長們把孩子送到一中,學生們一路拼殺來到一中,難道是為了一本嗎?這個成績顯然沒有達到他們的預期。
問題的焦點在于:素質教育能否解決高考成績問題。
對此,成都市武侯實驗中學校長李鎮西認為:素質教育不會妨礙高考成績。他認為,第一,素質教育遠不只是活動,應體現于課堂教學過程中,以為素質教育只是吹拉彈唱、蹦蹦跳跳,那是極大的誤解;第二,素質教育的學科教學——包括沖刺高考,需要時間,但絕不只是時間的堆積,也不是“題海戰術”的濫用,而是效率的提高,更是以一當十的“精題巧練”。這對教師的專業素質和教學智慧是極大的挑戰。所以,素質教育對教師的要求更高。
李鎮西初從教時,所帶的第一個高三畢業班,搞了大量改革與探索,開展了一系列豐富多彩的活動,班級生動活潑,孩子們開心快樂。然而,高考成績下來后,的確沒有考好,“素質教育”成了“罪狀”。得到批評的焦點就是:正是那些所謂“改革”影響了高考成績。批評者的邏輯非常簡單卻無比雄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過多的活動必然占用學習的時間,高考成績焉能不受影響?
但無論如何反思和檢討,他都不認為是這些影響了高考成績。他堅持認為教育改革沒有錯,不過,他也清楚意識到,改革還有缺陷。在當地教育部門的支持下,他帶的第二輪高考班成績空前輝煌,也證明了素質教育沒有錯,素質教育只會提高而不會降低高考成績。
正如李鎮西所說:我們不可能廢除任何考試制度,而“以一當十的‘精題巧練”的真正素質教育,它本身就必然包括能應對各種各樣的考試,在注重學生全面發展的同時,自然會使不同層次的學生都能夠在學業上盡可能提升,幫助每一個孩子找到自己上升的通道。
素質教育大方向
北京人大附中2020年高考成績十分優秀,17班王淇穎,總分722分,奪得北京市高考狀元。700分以上考生全北京80人,人大附中獨占28人。多年來,這樣的成績已成人大附中的常態。
人大附中的學生們享受著海量的校本課程、興趣班,這些課程基本上都和高考科目無關。學校還經常有名家講座,學生可以經常聽到著名科學家、作家和各種社會名流的演講報告。這些活動都和高考科目沒有直接關系。
再對比2020年高考翻車的名校。山東“全省前50名高中”的考生集體“翻車”,而且很多學生分數普遍比往年低,令山東高中的“名校”備受爭議。家長同樣認為,作為當地“名校”,中考錄取分數線都是最高,孩子們通過拔尖而來,結果3年后,高考成績卻沒有達到預期,他們感到難以接受,建議這些學校“好好反思”“認真反省”。
比如,臨沂一中高考成績一出來,便被推上了風口浪尖,遭遇了僅次于南京一中的口誅筆伐。
這表明,這些傳統上單靠高考成名的學校,還沒有看清國家推行素質教育的大方向:平民化的素質教育與“三位一體”綜合考評選才。
今天的素質教育,是建立在幾乎100%普及義務教育的基礎上。全面發展的素質教育,是全國每個學生的全面發展。所以素質教育是培養合格社會公民的教育,不是為了培養與眾不同的精英。當年李鎮西和人大附中用以一當十的“精題巧練”證明素質教育高考升學率不差;今天,名師網課已經通過三個課堂網校傳到每所學校、每個學生面前。這個時候再玩一考定終身,對于強調素質教育的名校就太不公平了。不少名校開始用新的方法來證明自己。
當下,一個已經被北大等名校和教改先鋒浙江省嘗試多年的錄取制度,為學生適應素質教育新時代,指明了方向。這個制度就是“三位一體” (綜合評價招生)制度。“三位一體”是2011年開始,浙江率先啟動的高校招生改革舉措,是高考綜合改革試點方案四種選拔模式之一,即省內高校拿出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額,錄取依據由高中學業水平測試成績、綜合素質測試成績和高考成績按一定比例合成的綜合成績,具體比例要求由試點高校根據學校培養目標和學科專業設置確定,但高考成績原則上不低于50%。
在這個制度下,按照“三位一體”標準考入清華北大的學生占比一半以上。這些學生靠高考前數年來穩定的各項考試成績,以多年平均高分的優勢,成功進入清北或者其他名校。2019年,浙江通過“三位一體”招生的高校達到49所,包括北大等多所名校。2020年北大“強基計劃”在浙江省投放了64個名額,浙江省是除北京地區以外,招生人數最多的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