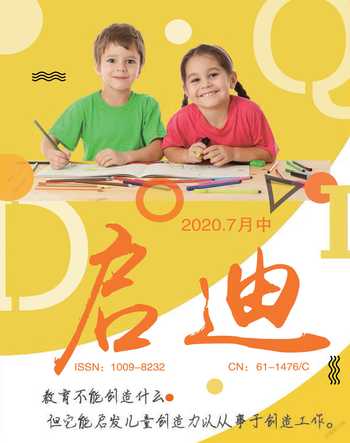民族文化旅游產業化的內在邏輯
摘要:本文以云南省丘北普者黑仙人洞彝族村為例分析民族文化旅游產業化的內在邏輯。本文首先探討了仙人洞村所具備的旅游產業化的條件,包括自然地理條件以及社會文化條件等。將這些資源轉化為旅游資源的途徑有很多,而現階段仙人洞景區的旅游開發則是由企業主導,這一方面促進了旅游產業的規劃建設,另一方面也帶來了一些問題,例如文化失真以及社會參與度低等。在此情況下,保護當地彝族文化以及構建旅游消費的邊界體系成為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所需遵守的重要原則。
關鍵詞:彝族文化;文化產業;旅游產業
作為少數民族特色村寨,云南省丘北縣普者黑仙人洞彝族村寨的旅游業發展迅速。其旅游輻射范圍從省內逐漸擴展至全國甚至全球,旅游業的發展給當地居民帶來經濟紅利的同時,也在解構著當地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而這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旅游業,并不同程度的阻礙著旅游業的繼續發展。
一、仙人洞彝族村旅游產業化的背景
仙人洞村之所以能夠開發成為名氣較大的景區,與其自身的特質不無關系。彝族文化之所以能夠產業化其背后有著深刻的現實原因。
(一)自然地理環境
仙人洞村具有獨特的喀斯特地貌,其中,仙人洞為典型的喀斯特溶洞。這種地貌使得仙人洞村具有觀光旅游的自然優勢。此外,仙人洞村由于長期交通不便,形成了相對封閉的自然文化環境,這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當地的自然環境,這也是旅游業得以存在的重要基礎。
(二)大眾傳媒宣傳造勢
仙人洞村作為普者黑核心景區的一部分,其發展與普者黑景區的發展關系密切。普者黑最初的旅游發展依托于云南省旅游業的整體發展,但其旅游業發展的巔峰時期是離不開大眾傳媒的推動。2013年,現象級綜藝節目《爸爸去哪兒》將普者黑作為其第三站拍攝地,這次拍攝借助平臺以及節目本身的收視率,將普者黑介紹給了全國觀眾甚至全世界的觀眾,大家追隨節目中明星家庭的腳步紛紛來到普者黑,這也是普者黑旅游業發展的黃金階段。
(三)民族符號消費
對于旅客來說,初級階段看山水,中級階段看文物,高級階段看文化。沒有文化內涵的旅游目的地,只會使絕大多數游客“來也匆匆,去也匆匆”,感到“不去是遺憾,去了也遺憾”。[1]仙人洞彝族生態村,之所以能夠成為普者黑核心景區,除了其仙人洞景區的觀光價值外,其民族文化也是吸引物之一。仙人洞村村民以彝族撒尼人為主,其獨特的文化體系對于非本民族的游客來說有著強烈的吸引力。從某種程度上說,少數民族地區的旅游是以民族符號消費為其主要特征的。
加之政府的扶持,大力發展節慶旅游,如每年的火把節、花臉節等,助推了普者黑的旅游發展,尤其是節慶旅游的發展。
(四)大眾旅游時代的到來
2016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落實帶薪休假制度,加強旅游交通、景區景點、自駕車營地等設施建設,規范旅游市場秩序,迎接正在興起的大眾旅游時代。”[2]
根據國際規律,人均GDP超過300美元,旅游消費開始起步;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時,觀光游快速增長;人均GDP高于3000美元時,旅游需求呈現爆發式增長,消費升級趨勢顯現;人均GDP高于6000美元時,步入休閑旅游時代。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2013年我國人均GDP數值為43684元人民幣,[3]超過了人均GDP6000美元的指標,中國的旅游業發展迎來了新的階段,良好的經濟社會環境。利好的國家政策這些都為仙人洞村的旅游業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
二、仙人洞村彝族文化旅游產業化的途徑
對仙人洞村的文化旅游產業化的路徑,村民及當地有關政府部門進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最初,一些學者專家提出建設“仙人洞彝族文化生態村”,但這一過程并不十分順利,王國祥認為這一建設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1999年起,是民族文化生態村進展比較順利的時期,但重開發輕保護的思想已經萌芽,專家們作了警示。第二階段,從2000年起,開始兩種思想的斗爭。在此階段的3年多里,建設項目組一貫堅持建設民族文化生態村的初衷,把保護生態環境和民族文化放在第一位,同時重視社區經濟的發展,謀求優秀傳統文化與時代精神、現代文明相結合的和諧的發展模式,使旅游業發展與文化遺產保護相得益彰,仙人洞村沿著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前進。”但是在兩方力量的博弈中,專家小組終于在勸阻無效后退出了。
經過了一段時間的發展后,當地人發現重視經濟的階段性發展并不利于其長期發展,反而損害了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旅游態勢出現了下滑。然后就進入了文化生態村建設的第三階段,“2002年,村民派代表上昆明,請求專家組繼續支持,共同建設民族文化生態村……專家組回到仙人洞村,制訂了仙人洞彝族文化生態村下一步的發展方案,設計民族文化傳習館和村中“運河”橋梁,引導村民處理好以旅游帶動地方經濟發展,以經濟增長加強文化和環境保護的關系,全面推進整個社區持續發展。”[4]
2013年,隨著綜藝節目《爸爸去哪兒》的開播,普者黑景區進入旅游發展的一個高峰,作為核心景區的仙人洞村,其旅游業也水漲船高,呈現井噴式發展。瞬間的發展對仙人洞村旅游業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據當地人回憶,2013年仙人洞村的旅游發展存在諸多亂象。以住宿為例,極端的情況下在仙人洞村兩三千元只能買到一個床位。類似的旅游業井噴式發展帶來的亂象還有很多,而此時的仙人洞村其旅游業是直接受政府管理。
據當地人介紹,政府此后開始招商引資,將普者黑景區的開發管理權轉讓于云南普者黑旅游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而這家公司的性質為云南省文山州丘北縣國有獨資經營有限公司,當地村民反映,自從這家公司接管了旅游后,做了諸多規劃,景區也確實比以前更加具有吸引力,村里的路更好走了,橋梁也增多,村民生活也更便利了。
政府將景區的管理經營權劃歸給企業,并由企業進行統一規劃建設,這一方面使得景區規劃更加專業化,但另一方面也存在諸多的弊端。企業以營利為目的,其所有規劃建設都是以獲取經濟利益為其首要目標,在這個過程中,彝族文化的喪失似乎并不是企業首要考慮的問題。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企業過分挖掘并促使游客消費民族符號,使得旅游“前臺”得到強化,而村民生活的“后臺”文化受到忽略,從長期發展的角度看,這并不利于旅游的持續發展。
三、旅游產業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
(一)存在問題
1.文化失真
旅游者體驗或多或少是建立在旅游客體的存在之上的。[5]過度的關注經濟價值必然導致文化價值的忽視,尤其是在兩者產生沖突的時候,作為旅游開發公司將會首先選擇經濟利益,這將進一步消散文化的價值,盡管政府及開發公司有意打造民族符號并宣傳節慶旅游,但其節慶旅游多帶有展演的性質,雖然是展示民族文化的一個窗口,但確是本真民族文化的異化,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會造成游客對于彝族文化的誤解,產生負面影響。
因此,在旅游開發過程中,文化失真是其面臨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一旦文化展演脫離了彝族文化本身,與其他景區展演內容出現同質化現象,那么景區將失去其文化靈魂。
2.社會參與度較低
參與式發展的思想是在對傳統發展思想反思的基礎上確立的,參與式發展理論強調通過社會成員的積極、主動的廣泛參與,來實現公眾計劃項目可持續的、成果共享的、有效益的發展。[6]這與前旅游部部長李金早提出的“全域旅游”概念有異曲同工之處。只有群眾參與到自己所在社區的旅游中來,成為旅游地的主人,才能更好的實現旅游者與當地居民的和諧共處,實現旅游目的地生態環境與文化環境更好的呈現。
在仙人洞村,旅游公司成為旅游收入的主要控制者,旅游收益并未直接返利于民,當地居民作為文化持有者,卻只能通過擺攤或成為旅游公司的員工等方式參與旅游,而沒有以一種東道主的主人姿態出現。
(二)旅游產業開發中的策略
1.保護當地彝族文化
保護仙人洞村彝族文化是旅游產業開發中應當遵守的首要原則。文化旅游實踐過程是旅游者離開日常熟悉的工作與社會實踐,進入東道主的文化生態空間消費“異文化”,旅游者都希望看到真實的旅游吸引物,體驗真實的目的地的社會生活,從而完成旅行的經驗積累和對目的地的認識。所以,具有地方性的真實的文化遺產都是旅游者選擇目的地的主要吸引物。雖然旅游者消費的地方性文化遺產不可避免地遇到“景觀符號化”和“遺產舞臺化”,但是真實性的遺產仍是吸引游客的地方性旅游資源,“原真”文化符號是“失真”文化符號存在的基礎。[7]因此,保護彝族當地文化是十分必要的,只有彝族文化“后臺”的存在,才能保證“前臺”展演的存在。在開發中,只有辨別清楚旅游地的旅游吸引物并加以保護才能實現旅游地產業的可持續性。
2.建構旅游消費的邊界體系
在文化旅游中,常常出現權力行為體主導、商業行為體放縱、旅游者隨性、文化原生主體讓渡、文化符號化等社會現象,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化遺產旅游消費過程中,各類行為體以利己主義為指導而進行的占有式消費。[8]在這種情況下,引導并建構旅游消費的邊界體系是十分必要的。
在仙人洞村旅游開發過程中,不同的行為體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權力越界行為。首先,權力行為體主導村落整體發展,商業行為體在開發過程中較多的考慮經濟價值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文化的存續性。將一些節慶或活動常態化,使其具有民族文化的形式,卻失去了民族文化的內涵。對于游客來說,旅游過程就是消費的過程,除了對物質產品的消費外,也存在對于旅游目的地文化的過度消費。而彝族文化的持有者——當地居民,則在一定程度上讓渡了其文化,將文化變身為旅游“前臺”的展演,滿足游客的旅游需求。
因此,在仙人洞村旅游開發中應該明確各方的邊界體系,旅游活動中所構建的社會關系是一個基于“利他主義”的合作共享關系,不同行為體各自遵循“善”的倫理道德,在旅游消費過程中恪守行為邊界。[8]
四、結論
民族文化旅游產業化是旅游話語下的一種趨勢,旅游產業有利有弊,在民族文化式微之時,旅游產業能夠幫助民族文化存續發展,并保持活態傳承。但同時,旅游產業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旅游產業使得民族文化發生異化,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文化的“原真性”,因此,在對民族文化進行旅游開發過程中要盡量避免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首先,民族產業之所以能夠產業化離不開其自身的特質,而這些特質符號化后便成為仙人洞村旅游吸引物,在符號化建構過程中有多種方式,例如打造仙人洞村彝族文化生態村等,而現階段仙人洞村在彝族文化旅游產業化的過程中主要遵循經濟原則和文化原則等兩個原則,這兩個原則不可避免的會產生一些問題,如文化失真以及社會參與度不高等。因此,在文化旅游產業持續發展的愿景下,應更多的保護當地文化,并且在旅游過程中構建旅游消費的邊界體系。
民族文化旅游產業化有其內在的邏輯,只有遵循其邏輯才更好的實現旅游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1]馬英.云南文化旅游產業的發展戰略研究[J].經濟問題探索.2009(06):126-131.
[2]國務院.2016年政府工作報告.2016.03.05.
[3]何瑋.社會參與視角下的鄉村旅游文化保護與發展研究[J].寧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2(05):94-97.
[4]吳興幟.文化旅游與遺產保護的平衡點探究[J].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07):133-137.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民族大學 宋蓉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