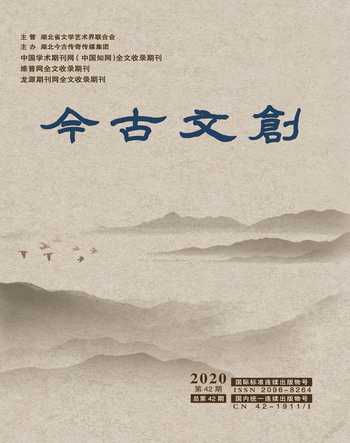謊言遮蔽下的澳大利亞民族創傷
【摘要】從立國之初的“自由定居者殖民地”到紀念一戰加里波利登陸的“澳新軍團日”,及至二戰中死亡鐵路集中營“鄧洛普千人團”的神話,澳大利亞主流話語擅長編織謊言來規避民族創傷,獲得某種暫時的安慰。當今澳大利亞文學界,“白澳神話”下的流放和殖民的創傷已經得到了一部分作家的關注,但是戰爭的創傷尤其是二戰的創傷依然書寫者寥寥。由此可見,澳大利亞的民族創傷從抑郁走向悲悼及至最終康復依舊長路漫漫。
【關鍵詞】澳大利亞;創傷;謊言;戰爭
【中圖分類號】I107?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42-0023-03
基金項目:本文系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澳大利亞作家群二戰創傷書寫研究”(18WWD003)的階段性成果。
澳大利亞對本國的歷史有著一種奇怪的認知。1988年全國舉行了盛大慶祝活動,紀念1788年英國運囚船隊首次登陸悉尼。這就是澳洲國慶日的由來,其時間節點不是1901年澳大利亞正式建國,而是紀念英帝國對澳洲的入侵。一戰加里波利一役中,數萬澳洲年輕人在英國將領的愚蠢指揮下,在土耳其盲目登陸,白白送命。這竟是后來澳洲的全國節日“澳新軍團日”(Anzac Day)的由來。更讓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2014年7月,當時的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在國會向到訪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致辭:日本是國際一等公民……即使澳大利亞不認同日本二戰期間的行為,也對日本人的戰爭技能和使命必達的榮譽感十分欽佩。此時離日本在二戰中轟炸達爾文港只過去了半個多世紀。
究竟用什么可以解釋這種比小說更魔幻的現實?施琪嘉在經典創傷文論《創傷與復原》中譯本前言中認為:群體在創傷的處理上,一方面會極度自戀,對異己和其他族群極具排他性和侵略性,另一方面會極度自卑,妄自菲薄,對他國盲目崇拜,類似于魯迅先生筆下阿Q的形象。(赫爾曼,2019:V)一部澳大利亞近代史就是一部創傷史,國家和個體都用謊言來規避創傷、自我神化以獲得某種身份認同,面對弱勢群體極度自戀,面對當年的加害者又極度自卑。這一點在澳大利亞作家的筆下可見一斑。
一、“自由定居者殖民地”的謊言
關于澳大利亞殖民(流放)時期的歷史,馬克·吐溫曾不無夸張地說:“它讀來不像歷史,而像編造得最美麗的謊言。”(黃源深,2014:5)在“白澳政策”影響下的民族身份敘事中,白人的到來揭開了澳洲殖民史的第一頁,也揭開了澳大利亞向歐洲啟蒙思想開化的第一步。在隨后的兩百多年中,澳大利亞人依靠堅韌勤勞、樂觀向上的“叢林友誼”,將這一塊蠻荒落后的大陸開辟成人間天堂,使澳大利亞成為歐洲啟蒙思想實驗成功的烏托邦。這個美麗的故事至今或隱或現地體現在澳大利亞主流話語中。
“自由定居者殖民地”的謊言主要表現在澳大利亞殖民時期的文學作品中。作者往往從宗主國的視角看待澳大利亞,將殖民地的叢林、牧場、冒險等元素融合進小說,以供19世紀倫敦上流階層茶余飯后的消遣。
較有代表性的有亨利·金斯利(Henry Kingsley)的《杰弗利·哈姆林的回憶》(The Recollections of Geoffry Hamlyn,1859)、馬庫斯·克拉克(Marcus Clarke)的《無期徒刑》(For the Term of His Natural Life,1874)和羅爾夫·博爾特沃德(Rolf Boldrewood)的《武裝行劫》(Robbery Under Arms,1888)。
這片土地上真正的苦難沒有得到真實的體現。被迫來到澳大利亞的流放犯被剝奪了行動自由,戴著腳鐐從事最繁重的無償勞動,苦難深重的他們無力也無權為自己發聲。土著在英帝國的殖民話語中被排除出人類的范疇,看作是與動物類似的野蠻人,他們更無從為自己發聲。
這種境況在20世紀中后期,隨著一部分作家意識到殖民和流放的創傷,并開始描繪這段歷史才有所改善。帕特里克·懷特(Patrick White)、托馬斯·基尼利(Thomas Keneally)、彼得·凱里(Peter Carey )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帕特里克·懷特《樹葉圈》(The Fringe of Leaves, 1976)的女主人公埃倫·羅克斯伯格在淪為土著人的奴隸后,被一名叫杰克·錢斯的流放犯所救,并與之共同生活了一段時間。
基尼利的小說《招來云雀和英雄》(Bring Larks and Heroes, 1967)描寫了在澳大利亞早期的殖民社會,主人公哈洛倫下士因不滿流放制度對流放犯的壓迫,最終加入了流放犯起義行列,后因被告密事發而被處以死刑。彼得·凱里逆寫了英國文豪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 1860-1861),以其中的流放犯馬格威奇為主人公創作了《杰克·邁格斯》 (Jack Maggs,1997),與另一部小說《“凱利幫”真史》(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2000)一起為流放犯翻案。作家弗拉納根的小說《欲》(Wanting,2008)刻畫了土著女孩瑪蒂娜在被白人殖民者收養以后走向沉淪和毀滅的痛苦故事,隱喻著土著文明被白人殖民者屠殺和毀滅的歷史創傷。
“1988年為慶祝反英兩百周年而出版了一大批歷史小說,有鼓勵人們回顧歷史、探究民族身份之意,尤其是鼓勵人們重新審視和評估對待女人、流放犯和土著人的歷史,而這些內容都折射在文學作品中。”(彭青龍,2013:59)但與此同時,鼓吹“自由定居者殖民地”神話的話語從未消失,土著和流放犯創傷的言說和最終走向康復依舊是未竟的事業。
二、戰爭英雄主義敘述的謊言
二十世紀的兩次大戰澳大利亞都積極地參與了。一戰的“澳新軍團日”二戰“鄧洛普千人團”戰俘營的神話至今仍是澳大利亞民族心理創傷的安慰劑。
一戰是澳大利亞追隨母國英帝國去世界各地作戰,希冀將帶著歷史原罪的流放犯的血液凈化成為母國盡忠的英雄的血液。結果是加里波利登陸的慘敗,數萬澳大利亞年輕的生命并不被英帝國的指揮官所珍惜。
二戰則更為慘烈,澳大利亞被母國拋棄后直接面臨著亞洲地理上的鄰國日本的入侵。隨著二戰中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推進,日軍飛機直接轟炸澳大利亞港口。最終二戰的結束并不是由于澳大利亞本土的頑強抵抗,而是因為外界的支援,澳大利亞民族心理層面上對日本的謙卑依然存在。因此,澳前總理阿博特匪夷所思的言辭就可以理解。
與此相對照的是,澳大利亞自19世紀中期便不斷掀起反華浪潮,用“白澳政策”排斥有色人種,排斥土著文化。華人勞工建設澳大利亞的貢獻,二戰中中國在正面的戰場牽制了大部分日軍南下的兵力的抗戰,一同在澳大利亞主流話語中被抹殺了。
這兩次大戰在文學作品、理論專著上都沒有得到足夠的表征。澳大利亞主流話語更愿意對此視而不見,用謊言來做安慰,建構一種戰爭英雄主義敘述,歌頌軍人為國捐軀的重大意義,自我神化,即使面對最難以啟齒的二戰死亡鐵路集中營,也塑造出了“鄧洛普千人團”的神話。
倫納德·曼(Leonard Mann)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后他創作了《穿盔甲的人》(Flesh in Armour,1932),將其中的人物吉姆·布朗特描寫成了理想主義的英雄人物。退伍士兵湯姆·漢格福德(Tom Hungerford)二戰后創作的《山脊與河流》(The Ridge and the River,1952)描寫澳大利亞士兵在熱帶叢林中克服常人難以想象的痛苦,最終成為平凡的英雄。澤維爾·赫伯特(Xavier Herbert)的邁爾斯·富蘭克林獎獲獎小說《可憐蟲,我的國家》(Poor Fellow,My Country, 1975)第三部分以日軍轟炸為描寫對象,著力刻畫了愛國主義。這種過于高大全的英雄人物描寫有時還夾雜著狹隘的民族主義,但是不如此的話,似乎便無以告慰亡魂。卡莉·塔爾(Kali Tal)認為受害者面對無法接受的創傷會發展出三種策略:疾病化(medicalization)、消失(disappearance)和神話化(mythologization)。(Tal,1996:6)面對摧毀主體自我認知的創傷,受害者用一種英雄主義的敘述策略建構起高大全的神話形象,在謊言中聊以安慰,使主體免于崩潰。
當然,也有一部分作家在試著戳破“英雄”“國家”“民族”等謊言的肥皂泡。基尼利的《懼怕》(The Fear,1965)中,主人公并沒有表現出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他對日本的戰機十分懼怕,甚至到了病態的地步。澳國內對涉及日本侵略的《懼怕》研究遠遜于基尼利的著名小說《辛德勒的方舟》 (Schindler’s Ark,1982)。大衛·瑪洛夫(David Malouf)創作的小說《偉大的世界》(The Great World,1990)中,集中營的日本兵日復一日的摧殘下,兩名澳士兵俘虜通過彼此的友誼而存活。理查德·弗拉納根(Richard Flanagan)參與編劇的電影《澳大利亞》真實再現了面對日軍的轟炸,普通澳大利亞人四散奔逃,大農場主之間互相傾軋,發戰爭財。弗拉納根的小說《深入北方的小路》(The Narrow Road to the Deep North,2013)解構了“鄧洛普千人團”戰俘營的神話,集中營沒有英雄,只有掙扎著活下來的可憐人。支撐著死亡鐵路集中營戰俘們的不是國家民族等“比肚子還要空”的觀點,而是彼此之間的友誼。對二戰中日本的入侵除了在一些小說和電影中有所涉及外,在主流話語中的表述不多,這表明了澳對戰爭創傷依然處于抑郁狀態,離公開發聲的哀悼為時尚早。
三、結語
雖然澳大利亞文學對立國之初的流放殖民之痛已有所觸及,其主流依然是亨利·勞森(Henry Lawson)筆下的叢林開拓者,是充滿男性陽剛氣息的“伙伴情誼”,這些是澳大利亞主流話語建構民族身份時所能接受的,歷史創傷污點是主流社會急于抹去的。與其清醒地面對摧毀自我認知的創傷,國家和民族都傾向于謊言中規避創傷,從此過上“美好、幸福”的生活。在懷特的代表作《沃斯》(Voss,1957)中,流放犯賈德是探險的唯一幸存者,他說“如果你在一個地方生活和遭罪的時間足夠長, 你不可能完全離開它。你的精神依然在那兒。”(White,1957:443)這暗含了懷特對澳辛辣評論,也可以看出近百年的民族創傷是澳大利亞無法否認的現實,它如毒瘤般潛伏在民族意識的深處,隱隱作痛。
澳大利亞主流意識形態對入侵國家表現出一種文化的崇拜,而對難民、土著和其他亞洲鄰國等異己族群表現出排他性和侵略性,盡管這些族群從未損害澳大利亞的利益,有的還對澳大利亞發展做出過巨大的貢獻。這種民族精神分裂癥狀可以用創傷理論來合理解釋。自英帝國入侵后,澳大利亞200多年的歷史就是一部創傷史,出于對民族身份正統性的焦慮,澳大利亞民族心理極度的自卑又極度的自大,他們面對給予自己創傷的加害者,無力進行反抗,因此下意識產生了一種“文化自卑”(cultural cringe);面對土著等較為弱小的群體時,又展示了內心深處的白人中心主義,認為自己是高等種族。謊言是以證偽的方式證明了創傷的存在,澳大利亞去殖民化、去創傷化的歷程,遠未結束。
參考文獻:
[1]Patrick White. Voss [M].London: Penguin Books,?1957.
[2]Kali Tal. Worlds of Hurt: Reading the Literatures of Trauma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3]赫爾曼.創傷與復原[M].施宏達,陳文琪譯.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19.
[4]黃源深.澳大利亞文學史[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4.
[5]彭青龍.澳大利亞現代文學與批評——與伊莉莎白·韋伯的訪談[J].當代外語研究,2013(02):57-60.
作者簡介:
施云波,女,漢族,江蘇常州人,常州工學院外國語學院,副教授,在讀博士生,研究方向:當代澳大利亞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