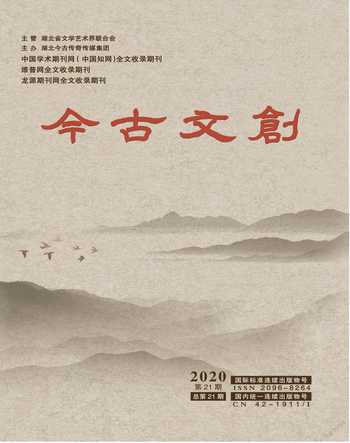文學視閾下的元結浯溪石刻析論
張津芝
【摘要】 元結寄居浯溪期間,先后刻六銘一頌于石上。這些石刻內容除了描繪山水自然和表達隱逸情懷之外,還充分體現了元結匡扶社稷的政治理想和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抱負。同時,石刻內容也具有高度的文學藝術性,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藝術形式古樸、藝術構思奇特、語言藝術新穎。通過這些石刻可以了解元結的儒、道思想。元結浯溪石刻在唐代和后世的文學史上產生了一定影響,圍繞著元結的石刻形成了浯溪摩崖石刻文學藝術群。
【關鍵詞】 元結;浯溪石刻;文學;思想
【中圖分類號】I206?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21-0028-02
基金項目:本文系2019年湖南省大學生創新訓練項目“元結浯溪遺跡考證、重構與開發”(項目編號:S201910551012)和湖南科技學院湖南省中國語言文學重點學科研究項目階段性成果。
元結生活的時代風云變幻,他一生既經歷過開元盛世,也經歷過安史之亂,元結特殊的經歷賦予了他無限的創作靈感和創作動力,他寄居浯溪期間創作了以《浯溪銘》《峿臺銘》《? ? ? 銘》《東崖銘》《右堂銘》《中堂銘》等為代表的多篇贊美浯溪、描寫隱逸生活的篇章,也寫下了《大唐中興頌》等愛國篇章,元結請書法大家把這些銘、頌書寫下來并刻于石上,從此以后,具有文學性和藝術性的浯溪石刻在以元結為代表的文人們的影響下熠熠生輝。
一、元結浯溪石刻內容
首先,元結所撰的石刻大多描繪了浯溪的山水自然景致,展現了元結對祖國大好河山的熱愛之情。比如在他的《峿臺銘》中所寫“石巔勝異之處,悉為亭堂,小峰歁竇,其間松竹,掩映軒戶,畢皆幽奇。” ①簡單的幾句四字短語就寫出了石巔亭堂附近竹木成蔭,交相掩映的清幽美麗景色。從元結的描寫中可以看出他十分喜愛這里獨特清幽的景色,并且稱之為“幽奇”,因為熱愛,所以元結所寫的文字才能讓人如見其景。他的《東崖銘》中也有類似的描寫。
其次,元結所寫的美麗景致寄托了他的隱逸情懷。他在《浯溪銘》中寫道:“浯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也,為自愛之,故命曰浯溪。” ②從這段描寫可以看出,元結因為愛浯溪的別致景色而“家溪畔”,其實是傳達了一種古樸自然的隱逸情懷,正如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中所寫:“富貴非吾愿,帝鄉不可期。”既然這樣,何不家居溪畔,做天地間一飄飄然的自在沙鷗呢?
當然,元結的隱逸情懷并不意味著他消極避世,恰恰相反,他愛國憂民,雖然身處江湖之遠,但是不忘個人高尚的志趣追求,保持了一顆既淡泊又愛國的初心。他在
《? ? ? ? 銘》中抒發胸襟:“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水聲松吹;霜朝厭者寒日,方暑厭者清風。”從中可以看出元結喜愛高山清流、清風水聲,而這些正是一個人淡泊心性和高潔品質的最好象征。這種樂觀豁達、隨緣自適的人生態度是元結個人高潔品質的最好體現。
最后,元結即使人生艱難,仕途不順,也依然心懷天下,憂國憂民。他在撰于上元二年(761年),刻于大歷六年(771年)的《大唐中興頌》中寫道:“邊將騁兵,毒亂國經,群生失寧。”元結因為百姓失去安寧而倍感憂心,他憂心的不是個人境遇,而是家國百姓,從中也可見得元結品性之崇高。
由此可見,元結浯溪石刻的內容大多與其個人經歷和心性品格分不開,主要是描繪美景、渴望歸隱、展示品性、抒發憂思這幾個方面。
二、元結浯溪石刻的文學藝術
元結浯溪石刻不僅具有深厚的內容,而且在文學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古樸的藝術形式。元結寄居浯溪期間,先后刻六銘一頌于石上。他所撰寫的文章大多采用了銘文和頌體這兩種古樸的藝術形式,比如《大唐中興頌》 《浯溪銘》《峿臺銘》等。而銘文和頌體這兩種藝術形式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時期。元結采用這兩種藝術形式,一方面是因為他創作的內容適合用銘文和頌體表達;另一個方面是因為元結是唐代古文運動的先驅,他用自己所寫的文章踐行著復古主義的文學理念。元結所寫文章顯得清靜自然,采用古樸的藝術形式進行創作也契合了其創作風格。
其次,奇特的藝術構思。元結所撰文章主要分為序文和正文兩個部分。他在進行創作構思時,將這兩個部分的內容、風格等做了明確分工,比如序文主要用來交代相關的人、事、物、創作背景等等,風格平實;而正文主要采用描寫和議論等相結合的創作方法,內容深厚,風格奇偉。他在《峿臺銘序》中寫道:“浯溪東北廿余丈,得怪石焉,周行三四百步。從未申至丑寅,涯壁斗絕,左屬回鮮。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從這一小段描寫中可以看出元結所寫序文內容以敘事描繪為主,交代清楚了相關的周邊環境,風格平實質樸、簡潔自然,這也是元結所寫序文的一般特色。元結所撰文章正文內容深厚、風格奇偉。這從他所寫的《大唐中興頌》可以看出。首先,《大唐中興頌》這篇文章“歌頌了唐朝平定安史之亂、收復兩京的中興業績,并以微言揭露了玄肅之際政治變局的真相” ③,從文章內容上來看,著重描寫了唐兵收復長安的功勛,歌頌了二圣的功德,透露出作者對大唐中興的渴望。文章內容涵蓋歷史、政治等多個方面,時間和空間跨度大,雖然字數不多,卻把從安史之亂到收復長安之間的每件事情的來龍去脈都交代得清楚明了。《大唐中興頌》正文仿秦始皇金石刻辭的體例,三句一韻,共十五韻。這樣的文學形式讀來節奏分明,給人以暢快淋漓之感,使得整篇頌文風格雄偉壯闊,大氣磅礴,讀來一氣呵成,雖然比不上盛唐時期的大氣開放,但也是中唐時期少有的蓬勃奇偉,讀完使人感到中興就在眼前、充滿希望。《大唐中興頌》內容上敘述唐朝歷史演變和政治變局,深厚有價值,配以節奏明朗的文學形式和奇偉磅礴的文學風格,使得這篇頌文毫無疑問地成了元結最得意的文章,融合顏真卿成熟圓渾的筆法,刻諸天然的摩崖石壁之上后,更是成為了浯溪石刻中一道最靚麗的風景線。
第三,新穎的語言藝術。元結浯溪石刻中的語言藝術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駢句和散句的有機融合。駢句是指具有相似的結構和相關的內容,行文相鄰并且字數相等的兩句話,而散句就是相對于駢句以外的句子。元結在浯溪石刻的撰文中,很好地融合了駢句和散句,使得文章張弛有度。比如在他的《? ? ? ?銘并序》中寫道:“西面在江口,東望峿臺,北臨大淵,南枕浯溪,? ? ? ? 當乎石上……”這簡單的一小段序文中,恰到好處地運用了駢句和散句兩種不同的句式,將? ? ? ? 的東南西北的地理位置交代得清晰明了,行文風格也樸實自然。因為其特殊的句式結構和行文模式等,駢句顯得簡潔明了,沒有贅余,但如果通篇文章都使用駢句,難免讓人感到單調貧乏,元結在浯溪石刻撰文中不著痕跡地融合駢句和散句,既不會因為句式太過統一而讓讀者感到乏味,也不會因為句式太過不一而顯得文章散漫不莊重。反倒因為元結在文章中有機地融合了駢句和散句,而讓文章錯落有致、張弛有度,也讓讀者看山似的“不喜平”而喜歡元結的文章。二,簡潔雅致的語言風格。從元結撰寫的多篇文章中都可以發現它們的語言風格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簡潔雅致、清新自然。無論是大氣磅礴的《大唐中興頌》,還是寄托了元結喜愛贊美之情的《浯溪銘》《峿臺銘》等,從語言風格上細細品析,都能發現它們質樸簡單又別有雅致,清新自然又不落俗套。如他在《浯溪銘》中有寫道:“湘水一曲,淵洄傍山。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巉巉雙石。”在這段簡潔的描寫中,元結主要運用了四字短語形容山水形貌,四字一句顯得簡潔,而用疊字如“潺潺”和“巉巉”分別形容溪流和山形,又顯得雅致大方,讓人仿佛置身于清新自然的浯溪山水間。
三、浯溪石刻與元結思想
浯溪六銘一頌是元結晚年作品,從這些石刻中可以看出元結思想:
首先,浯溪石刻體現了元結的儒家思想。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開始,儒家思想開始在我國古代社會思想中居于正統地位,影響著漢代和后世的無數文人墨客,元結當然也不例外。儒家思想提倡“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而縱觀元結一生,他在“達”時為官清廉,深受百姓愛戴,還帶兵抵抗史思明叛軍,保全了城池;他在“窮”時游覽浯溪山水,自得其樂,寫下了不少詩文,使得浯溪開始大放異彩,這些行為正是元結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表現。浯溪石刻也帶上了儒家“留名后世”的印記,比如他撰寫了《大唐中興頌》,并請顏真卿親書,最后刻于一整塊石壁之上以表達自己對國家中興的渴望向往,同時也做到了留名后世。歐陽修在評價其石刻時就以為“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為,惟恐不異于人,所以自傳于后世者,亦惟恐不奇而無以動人之耳目也。視其辭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誠恥于無聞,然不如是之汲汲也。” ④由此可見,元結受儒家思想影響之深。
其次,浯溪石刻體現了元結的道家思想。在元結一生中,“‘窮則獨善其身’的儒家人生原則影響他人生的一半,另一半浸染著道家道教色彩” ⑤主要表現在元結的處世方式和行文風格上。老莊的道家哲學思想強調清靜無為,并向人們描述了一個小國寡民、質樸簡單的世界。元結在任容管經略使期間,多次辭官,表達出了歸隱浯溪的愿望。他一生中深受道家思想影響,在浯溪石刻的撰寫中也有體現,比如他采用的古樸的藝術形式,主要是銘文和頌體這兩種較為樸實的藝術創作形式,而其語言風格更是簡潔雅致,行文樸素自然。正所謂“文如其人”,元結的文章正像他自己一樣高遠淡泊、自然質樸。可以說,道家思想內涵滲透在元結浯溪石刻所描繪的山水自然之中。
四、結語
元結生活的時代風云變幻、動蕩不安,他的個人經歷更是艱難坎坷、一波三折,然而正是因為時代的因素和個人獨特的經歷,使得元結的浯溪石刻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而受其影響的浯溪石刻藝術群在中國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至今仍有著珍貴的價值。
注釋:
①②元結著、孫望校:《元次山集》,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152、152頁。
③鄧小軍.元結撰、顏真卿書《大唐中興頌》考釋,《晉陽學刊》,2012年第2期,第125頁。
④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上海辭書出版社,第34冊,第260頁。
⑤蔣振華:《元結的道家道教人生與文學創作》,《湖湘論壇》,2019年第4期,第12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