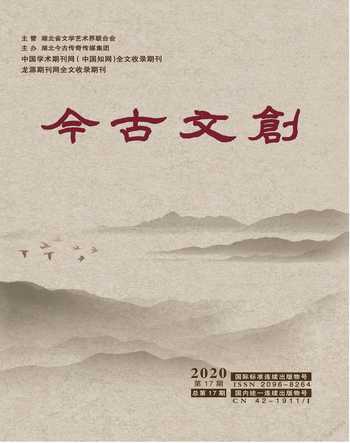從中國當代文學思潮角度解讀《人面桃花》
【摘要】 《人面桃花》是格非的轉型之作。作者在保留先鋒文學的創作風格的同時,更加注重人物的塑造,敘述的技巧和語言的優美性。本文從當代文學思潮的角度對作品進行解讀,多角度闡釋作品的深意。
【關鍵詞】 格非;人面桃花;文學思潮;革命
【中圖分類號】I207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文章編號】2096-8264(2020)17-0006-02
二十世紀初問世的《人面桃花》與稍晚發表的《山河入夢》《春盡江南》合稱為“江南三部曲”,是作家格非的代表作品之一。作為“江南三部曲”的開卷之作,《人面桃花》將故事背景設置在20世紀初的中國,天真少女陸秀米結識革命黨人,展開了一場關于革命與烏托邦的故事。作者在保持以往先鋒小說風格的同時,給作品注入新的內核。
一、作為主體的“人”的蘇醒——從啟蒙主義角度
分析
啟蒙作為現代化進程的一個重要方面,影響了二十世紀以來中國的歷史。早在新文化運動時期,“民主與科學”思想的提出就閃耀出啟蒙主義的光芒。隨著民族危機不斷加深,生存環境的動蕩不安,救亡圖存成為當時最重要的任務。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末,正如李澤厚在一系列的論述中指出,救亡壓倒了啟蒙。而后的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個人的解放和對自由的追求則被納入集體之中。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中國社會開始對極“左”思潮進行全面的反思。這一時期,人性、人情和人道主義等基本問題得到了更加深入的思考。1985年底,《論文學的主體性》一文在《文學評論》上發表,作者劉再復集中闡述了對“以人為中心”這一啟蒙思想的系統思考。
《人面桃花》一共包含六指、花家舍、小東西和禁語四章,以陸秀米為主人公,講述了主人公少年時期父親離家出走,結識張季元,出嫁時被綁架到花家舍,東渡日本后回歸普濟建設學堂,出獄后懲罰自己不再說話等一系列人生經歷。小說貫穿了“革命”和“性”這兩個關鍵詞。
從“革命”啟蒙方面來說,張季元、薛祖彥蜩蛄會等人企圖通過革命推翻封建社會的統治,建立自由、平等的新社會秩序,他們有進步的理想,并付諸實踐,最后甚至犧牲了性命,但是,革命卻是失敗了的。一方面,革命者自身有著致命的弱點,對革命沒有透徹的理解和堅定的意志。無論是張季元還是陸秀米,他們在從事革命事業之時更多的是受自己意愿的支配,從個人的精神需要出發。加之革命黨隊伍中混入了太多只為滿足一己私欲的烏合之眾,小說中出現了“樹倒猢猻散”的局面。另一方面,革命并沒有密切聯系群眾,無論是張季元制定的《十殺令》中將裹腳者列入其中,分不清迫害者和受害者,表現出對群眾的殘忍的一面,還是陸秀米自己都表現出對革命的困惑:“革命,就是誰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革命者對革命的認知的淺顯揭示了啟蒙的不徹底,隊伍的不純潔則注定革命的失敗。
從“性”啟蒙方面來說,無論是張季元日記里記錄的與蕓娘、翠蓮的不正當關系和對秀米的愛的欲望,還是秀米在花家舍被強奸時的生理反應,以及秀蓮對老虎的勾引等,作者毫不掩飾甚至凸顯了人的欲望,表現出人在欲望和意志之間的掙扎。相較于典型的高大全的革命者形象,《人面桃花》中對革命者內心隱秘的欲望的書寫凸顯出作為塵世之中凡人的一面,這無疑也是對傳統的一種反叛。
二、烏托邦的構建與幻滅——從文化尋根角度分析
在小說《人面桃花》中,作者塑造了陸侃、張季元、王觀澄、陸秀米等多個知識分子形象,這些知識分子都有著重新構建一個新的社會秩序的理想。以陸侃、王觀澄為代表的傳統知識分子向往的是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被罷官后的陸侃在回到普濟后設想建立能夠為普濟人遮風擋雨的“風雨長廊”,但他的想法并沒有實現,他把自己囚禁在閣樓里發了瘋,最終離家出走不知所蹤。王觀澄比陸侃多走出一步,建造了和桃花源般的花家舍,在這個村莊里每一個住戶的房子、庭院以及庭院的格局都是一樣的,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就連家家戶戶所曬到的陽光都一樣多”。然而在這一幅美好平和生活圖景下掩蓋著的是土匪的本質。為籌措資金建造這個世外桃源,王觀澄當起了土匪,最后花家舍也因為土匪頭子之間的爭斗和暗殺灰飛煙滅。
張季元和陸秀米則代表著主張革命的新知識分子。在《人面桃花》中,張季元因為蜩蛄會暴露被搗毀失去了性命,構建新的社會秩序的理想中斷。陸秀米通過張季元的日記得知這一理想并繼承下來。在東渡日本回到普濟后,陸秀米變賣家產,修建學校,企圖構建一個融合了她父親的大同世界觀和張季元的革命理想的像花家舍那樣的世外桃源。然而,陸秀米聚集起來的只是一幫自私自利的烏合之眾,這些人的行為也鋪墊了最后的結局。當然,小說的最后普濟饑荒時期,陸秀米將白米用以施粥,井然有序的隊伍也暗示著構建烏托邦的可能性。
發生在80年代的“文化尋根”思潮,“是新時期文學在現代意識觀照下重審核傳統文化、發掘本土精神資源的一次重要努力”,小說《人面桃花》中,陸秀米要構建的正是一個將“大同社會”的傳統思想和革命現代性因素融合的理想社會。小說中知識分子在經過現實的幻滅后對理想社會的追求與構建正是文化尋根思潮中的知識分子急迫尋求能走出當下精神困境的道路。格非在小說出版三年之后作的序中說“這部書是對自己心目中虛構故鄉的一種緬懷和想象之書”,格非通過小說暗示烏托邦構建的可能性警醒當代人不要失卻內心的精神指引,要努力構筑自身的精神家園,雖然理想的精神藍圖有可能無法實現,但也應該堅持尋找,走出困境。
三、欲望書寫與現代敘事技巧——從先鋒文學角度分析
欲望書寫是先鋒小說家的重要題材之一。在傳統的小說中,關于性的描寫受到極大束縛。作為對傳統文學的反叛,先鋒作家對于性愛給予了充分的描寫和思考。在小說《人面桃花》中,作者對性愛的書寫幾乎貫穿了整個作品。小說的主人公陸秀米和張季元,張季元和蕓娘,管家寶琛和孫姑娘……小說中幾乎每個人、每個章節都涉及性這一欲望的書寫。在格非的筆下,人保持著動物的本能,一方面,欲望書寫表現出愛情美好的一面,如張季元對陸秀米的克制的愛在日記中得到體現,另一方面,不受道德約束的性有其丑陋的一面,如文中的翠蓮勾引年幼的老虎導致的亂倫關系,甚至發現翠蓮的性與革命的失敗總是存在著某種聯系。
除了對性的關注,中國當代先鋒文學的發展主要立足于“文體革命”這一特殊的形式載體。《人面桃花》共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充滿了神秘,設置了一個懸念,頗有懸疑小說的風格;第二部分則描寫了花家舍的經歷,富有傳奇色彩的同時充滿了緊張恐怖的氣氛,尤其是花家舍土匪領頭人之間的爭斗充分展現了人性惡的一面;第三部分冷靜平淡地敘述陸秀米回到花家舍展開革命的情景,這一章通過一個普通的旁觀者視角,將進行得如火如荼的熱血革命淡漠化,展現的是沒有和群眾緊密聯系的革命圖景,在旁人看來,革命是無意義的,革命者則是“瘋子”;第四部分敘述的風格再一次發生改變,陸秀米再回到普濟時懲罰自己不再說話,對外的無言與內心的回顧和沉思形成對比,隨著陸秀米和喜鵲日常生活圖景的展開,情節回歸平靜,語言回歸平淡。除了敘述視角的不停轉換,小說中還出現了大量具有象征意義的夢境書寫,通過這些夢境的書寫來暗示事情發展的后續以及人物的精神狀態,如在小說第一章第七節中關于孫姑娘的葬禮的夢境出現陸秀米被綁的情節,與第二章陸秀米出嫁被綁至花家舍的情節前后呼應。并且,在這一節中出現了多次“奇怪……”這一句式的重復,在夢境的這一重復使敘述呈現出一種緊張感和荒誕感,現實與幻覺交纏,增強了敘述的張力。
四、脫離宏大敘事的革命——從新歷史主義角度
分析
中國當代文學中,無論是十七年文學還是新時期文學,關于革命英雄和革命歷史的書寫都追求宏大敘事和歷史的深廣度。《人面桃花》作為包含革命內容的小說,擺脫政治意識形態的限制,立足于革命中的個人,探討革命與人性的隱秘關系,剖析革命者的心理,對革命歷史的記載進行反叛。
首先,《人面桃花》將傳統敘事的大歷史還原為日常生活,小說人物具有了主體意識與隱秘心理。小說以主人公陸秀米結識張季元、被綁架到花家舍、從日本歸來回到普濟以及從監獄回來的四段主要人生經歷為主,通過張季元的隱秘日記了解到革命,陰差陽錯卷入蜩蛄會中,再加上花家舍的變故,陸秀米最終被裹挾到革命的洪流之中。她并不像傳統的革命者那樣對革命有一個清醒的認識,為革命犧牲的張季元占據了她的內心,對于張季元的癡迷讓她投身革命,她沒有所謂革命信仰的洗禮,只是一個由于歷史的偶然性而成為“瘋子”的人。在小說中,無論是陸秀米還是張季元,通過小說中細致的日常生活的描寫,可以看出他們都是有七情六欲的人,是有性的隱秘的人,是有著錯綜復雜的情緒的圓形的人,也是有缺點的人。
其次,小說對于革命歷史的敘述由紀實轉變為虛實相交。正如上文所說,《人面桃花》對革命黨的描寫虛實相交,創作者對于歷史記錄的空白做了很多想象性發揮,甚至有時候還會出現小說情節和歷史記錄有出入的情況,在小說里,歷史的客觀性被顛覆,革命的崇高性被消解。在《人面桃花》中出現了多次瓦釜中倒映出來的幻象,小說開頭離家出走陸侃的下落在結尾的瓦釜中得到暗示。瓦釜倒映出來的幻象和夢境一樣具有暗示功能,這一天馬行空的描寫與歷史記錄相結合,虛實相生,消解了歷史的真實性。
陳思和曾評論馬原“對傳統敘事的似真幻覺的破壞以及隨之而來的經驗的主觀性、片段性與不可確定性,打破了任何一種宏大敘事重新整合個體經驗的可能性,這使得充滿個人性與主觀性的現實凸現了出來”。格非亦是如此。
參考文獻:
[1]李玉巖,潘天波.大運河文化的媒介化傳播策略[J].戲劇之家,2019,000(006):208-209.
[2]姚璇.河南大運河文化帶與鄉村旅游融合發展思路研究[J].三門峽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9.
作者簡介:
王聆力,湘潭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現當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