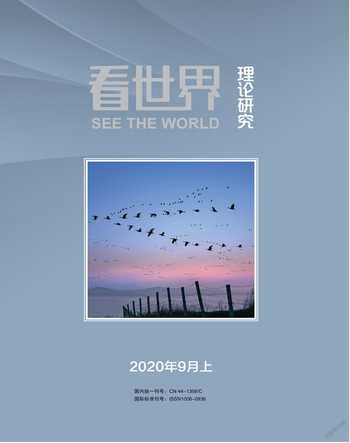從“三國”走進“水滸”的歷史性與社會性
盛海峰
摘要: 《三國演義》與《水滸傳》皆創作于元末明初之際,“三國”作者羅貫中又是“水滸”作者施耐庵的“門人”,由此可見二本名著之間雜糅緊密,在創作環境、創作者背景、歷史性和社會性方面共性很多,筆者從新視角出發,從“三國”的“忠”到“水滸”的“忠”探索文學作品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和歷史屬性。
關鍵詞:三國演義;水滸傳;歷史性;社會性
一、創作者:施耐庵與羅貫中
施耐庵與羅貫中命運極其相似,又都游歷于元末民初,羅貫中與施耐庵的關系密切[1],現存歷史表述中大都認為施耐庵年長于羅貫中,羅又是施的門人,他們的著作則是《水滸》在前,《三國演義》在后。
施耐庵出身藝術世家,有一定家庭知識和經濟背景支持,這對施耐庵的學識和創作帶來了極充沛的條件[2],元初期的水滸雜劇中的描寫和關鍵詞語也給施創作《水滸傳》奠定了借鑒的基礎。施耐庵是前人成果的集大成者和再創作者。他采用了《宣和遺事》的框架結構對“宋十回”加強了“忠義”強化,對“武十回”則保留了話本原貌,對楊志、魯智深、史進故事進行了加工,而著重點是突出了后面的征方臘情節。羅貫中是施耐庵的門人,他仰慕施,又和施亦師亦友,在施病逝前后,他對《水滸傳》進行了最后的加工和定稿以及傳播。這在后期學者對《三國演義》的情節和用詞考究上多有內證,這里筆者不作過多論述,這里著重凸顯施耐庵和羅貫中通過《水滸傳》和《三國演義》對“忠義”的貢獻。
在《水滸傳》中,王進遭受迫害,林沖被凌辱家破人亡,最終導致官逼民反,一定程度上被歷史和社會學者表述為了社會性的顯現,“三國”“劉關張”的忠和水滸“眾兄弟”的忠也存在其社會性基礎,與此同時,從三國諸葛孔明的光復漢業到宋江悲劇結局,也突出了理性的歷史教訓,二本著作都深化了作品的思想意義,并具有強烈的歷史和社會震撼力量,堪比中國歷史和社會的鏡子。
二、“三國”和“水滸”的忠
(一) “三國”的忠
“三國”中的袁紹,年輕時血氣方剛,可謂青年才俊,臨了中年,變成了外強中干、胸無大志的庸主,同時,袁紹也沒能處理好諸子關系,致其二子相殘,基業速亡“三國”袁紹形象正史原型,羅貫中塑造袁紹的悲劇對整部小說主要人物的形象塑造起到了陪襯作用,并推動了歷史情節的發展,也給后世留下了社會借鑒。相反地,羅把諸葛亮則塑造成了中華民族智慧和忠義的象征,諸葛孔明的政治、軍事有力地輔助了蜀漢政權的建立與鞏固。同時,“劉關張”的“桃園結義”無論在歷史意義和社會意義上,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他們與諸葛亮“忠”“信”相呼應,皆表現出忠義報國、匡扶漢室、踐行仁德的君子品質。
(二) “水滸”的忠
施耐庵在“水滸”中對李逵的行為和思想性格描述比較具有典型性,看“李逵”的忠義觀,也從側面揭示了水泊梁山英雄的“忠義”觀念,首先李逵對母親的“忠”,在梁山發達后,接“母“出來,不幸被”虎食“,怒而殺虎;其次,李逵對“宋江”的忠,可謂宋的左膀右臂,這一定程度上具有“江湖性”,也是眾梁山英雄好漢共同的悲劇性“忠義”根源.
再看,施耐庵筆下的重要人物宋江,全書中他的核心思想就是“忠義”二字,宋江的忠義是矛盾的,他要求“忠”,又要求“義”,他不滿于現狀,敢于革命,又瞻前顧后,優柔寡斷,最后又傾向于招安的“忠”君,宋的雙重性格直接導致了宋江的個人悲劇,也造成了整個水泊梁山的覆沒。
(三) “三國”與“水滸”歷史性和社會性
1、歷史性
羅貫中在《三國演義》中,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大多皆有其歷史原型,也有一定歷史性,無論是曹操,諸葛亮,還是“劉關張”三兄弟等,人物基本婦孺皆知,在人物的歷史性方面,羅貫中善于把握歷史意義中的“忠”,將社會動亂、水深火熱的人民生活,與“忠”進行結合,將英雄人物與社會歷史事件進行融合化的描述,比如作者將魯肅形象塑造成極為"忠厚老實"的藝術典型,又兼顧其具有指揮領軍的能力,整體展現了魯肅從文武雙全向忠厚老實的臣子“忠義”形象,這在歷史文學作品中極其罕見,多有歷史借鑒意義。
施耐庵的《水滸傳》,其歷史性又具有爭議性,充滿了蘊的忠義倫理悲劇色彩,一方面它不僅是對正史“忠義傳”所引發的英雄入史情緒的深刻反省,更是對封建忠義倫理規范的反思批判。施耐庵的“水滸”中,以宋江等梁山好漢的“革命事業”注定失敗,這與施耐庵所處的歷史時代息息相關,元末明初期,以朱元璋為代表的農民起義軍所要反抗的是外族“蒙元”的統治,是為了光復漢文化,同時在施耐庵當時又處在與朱元璋對立農民軍張士誠麾下,明處又盛行“文字獄”,這些都對《水滸傳》的創作帶來了局限性,具有歷史的矛盾性,一方面“反抗”,一方面又有“妥協”,反抗是“忠”,妥協也是“忠”,對江湖的“忠”和對廟堂的“忠”,讓二者結合又脫離,“水滸”忠義倫理是具有邏輯悖論及愚民本質,在歷史性方面是矛盾,有一定社會江湖影響,有一定愚民性影響,但最終不得不臣服于歷史王朝的統治。
2、社會性
羅貫中的《三國演義》,將忠義社會屬性描述的淋漓盡致,在“劉關張”三兄弟薦才描寫方面也比較詳實,從“三英戰呂布”,到“關羽斬三雄”,都將人才看作稱霸的基礎,又將忠貫穿其中,從關羽、張飛對劉備的忠,與呂布的“三姓家奴”進行對比,這些已經成為中華民族佳話的故事,都在作者的塑造和情節的發展中得以達到一定的廣度和內涵,也映射出作者對現實的不滿與對理想社會的向往.“三國”思想上將歷史和社會的"大一統"思想與仁忠義追求進行融合,將中華民族的主流意識與百姓心理聯結起來,使得普通百姓從心理上接受“三國”的忠義文化。
而施耐庵的《水滸傳》則具有矛盾性和挑戰性,“水滸”忠君觀念與正史有差別,作為江湖綠林“忠”,首先打破了傳統封建忠君,傾向綠林的“義”,但發展到一定階段,個體的回歸又不得不走回正統的“忠”,從而埋下了悲劇的社會性,這使得《水滸傳》在社會性方面具有復雜性,這在其成書過程和刊印時期,都可不同程度地體現,從“禁書”到逐步放開的復雜形態。
三、結束語
忠義本來是兩個倫理系統的“后天”整合,是辯證否定的關系[3],《水滸傳》又名《忠義水滸傳》,其中的忠義具有一定的歷史價值和社會價值,以宋江為代表的梁山好漢“反貪官”,不反“朝廷”,走上招安之路,也都從其矛盾的“忠義”觀出發,而《三國演義》注重“出身門第”、“踐行仁義”、“同情弱者”、“皇權至上”的文化價值,都在一定程度上顯現了中華民族的“忠義”文化觀,有深厚的社會性和歷史性影響。
參考文獻:
[1] 溫慶新. 文獻傳播學視野下的《水滸傳》作者研究[J].中國文化研究,2018(02):13.
[2] 李永祜. 施耐庵和羅貫中對《水滸傳》成書的貢獻[J].菏澤學院學報,2011(04):005.
[3] 宋錚. 《水滸傳》與忠義倫理悲劇的形成[J]. 淄博師專論叢,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