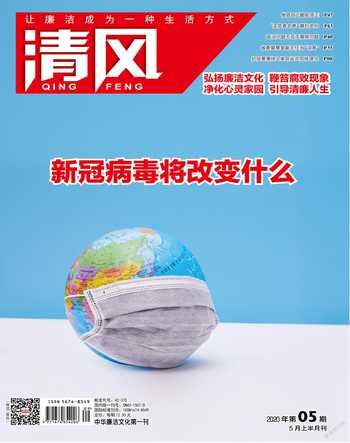做官自己腳底須正
于永軍
“做官自己腳底須正”,這是清初刑部尚書王士禛在教子家訓中提出的一條首要的做官準則。康熙三十六年(1697)七月,王士禛之子王啟汸出任唐山令。王士禛唯恐兒子不能勝任,遂將自己的為官準則50條寫成3009字家訓,讓兒子帶在身上隨時參詳。其中首條開宗明義:“做官自己腳底須正,持門第不得。”
很顯然,這是提醒兒子要自強自立,既不要“拼爹”“啃爹”,更不要“坑爹”。那么,何謂“自己腳底須正”?王士禛進一步指出:“皇上御書賜天下督撫,不過‘清慎勤’三字。無暮夜枉法之金,清也;事事小心,不敢任性率意,慎也;早作夜思,事事不敢因循怠玩,勤也。”可以說,王士禛的“清慎勤”,道出了古代清正為官的精髓,也為現代為官提供了修養圭臬。
不過,讀王士禛教子故事,讓我感動的并不只在于其言之諄諄,而是其言之鑿鑿背后的行為示范。“做官自己腳底須正”,似可與我們今天所說的“打鐵還需自身硬”同義,指向于對外宣示,大義凜然,實為至理名言。但作為教子之道,面向自己家人,卻需要用自己的榜樣作注腳。
首先,這官當得要正。不能想象,像唐代元載、宋代蔡京、明代嚴嵩那樣的貪墨,會敢在兒子面前義正詞嚴地講什么“做官自己腳底須正”。也不能想象,一個過去見利忘義、貪贓枉法、中飽私囊的人,知根知底的兒子會相信他關鍵時刻亮出這條準則。
其次,要有言出行隨的事實。無論家庭還是社會,凡公信力缺失,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教育者“口惠而實不至”。嘴上宣示“公正執法”,結果卻是“看客下菜”,彈性效應;嘴上宣示“廉潔從政”,如果你真的認了實,他心里便不高興,重者還會給你以“顏色”……這種表態,說白了不過是一種打官腔,一種嘩眾取寵,涂涂洗面奶,玩玩小把戲,騙騙“小朋友”。
再次,要有接受監督的真誠。憑心而論,官員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自己的種種愛好。而亮出這個“自己腳底須正”,實質是將矛頭對準了自己,要求自己首先必須堂堂正正,堪稱楷模。沒有一個與私我徹底決裂的境界做不到,沒有一個敢將自我公開晾曬的勇氣同樣也做不到。
正是由這個角度打量,王士禛訓子的這個“做官自己腳底須正”,所彰顯的是一種做官的自信,一種“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王士禛,字子真,號阮亭,別號漁洋山人,世稱王漁洋,清初著名詩人,主持詩壇50年之久,康熙曾征其詩三百首定為《御覽集》,其詩、文、詞共數十種560多卷,故而被譽為“一代詩宗” “文壇領袖”。而與其文名相得益彰的是,他為官幾十載,始終恪守“清慎勤”原則。任揚州推官四載,他“不名一錢,急裝時,唯圖書數十篋”,自贊:“四年只飲邗江水,數卷圖書萬首詩。”榷江浦關專管船政,他革除弊端,凡發銀均足稱足色,毫無扣除,聲震漕運;在戶部任上七年,他始終如一,清廉自守,同僚信服;任刑部尚書,他不畏強權,依法判案,執法如山,深受康熙賞識和同僚贊嘆,被譽為“一代廉吏”。也正是基于這種做官堂堂正正的本真,王士禛才有了“做官自己腳底須正”的底氣,才有了對兒子耳提面命的凜然大義。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建設清明政治、反腐倡廉,我們今天仍然需要若干方面的努力。但無論情況如何,領導干部“先從吾始”的清正齊家風采,始終在全社會有著春風化雨的表率作用。也正是從這個角度認識,王士禛的教子故事尤其是蘊含于其后的自好精神,穿越了時空隧道,閃耀著新時代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