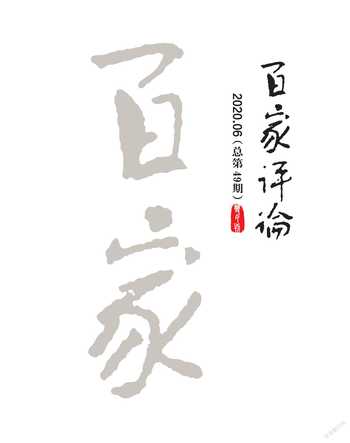阿來《蘑菇圈》的三重象征意蘊
唐小祥
內容提要:阿來的《蘑菇圈》由松茸這種藏地的特殊物產入手,來觀察它與藏地社會和人群間的復雜互動,以及由此所折射出的人性明暗和人生況味。小說塑造了阿媽斯炯這個善良堅韌而又理性智慧的藏地女性形象,充滿著現實主義的反思和憂慮,包涵了多重的象征意蘊:既象征著消費社會中包括藏地在內的邊疆的奇觀化命運,也象征著當代中國鄉村自然史與激進現代性的復雜纏繞,以及在時代劇變中對人性溫暖和悲憫的守護。
關鍵詞:蘑菇圈? 消費社會? 自然史? 現代性
阿來的《蘑菇圈》初刊于《收獲》2015年第3期,后與《三只蟲草》《河上柏影》一起收入“山珍三部”,最近又因其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的新的思考和呈現”而獲得魯迅文學獎。與《塵埃落定》《空山》《瞻對》《格薩爾王》等長篇對藏地歷史的當代重構相比,《蘑菇圈》的故事時間也發生在當代史的內部,但都被處理為單純的時空背景,不構成敘事的主要內容。作者從人們對藏地特殊物產松茸的需求這一切口,來觀察它與藏地社會和人群的復雜互動,以及由此所折射出的人性明暗和人生況味。小說在當代波詭云譎的歷史風云中塑造了阿媽斯炯這個善良堅韌的藏地女性形象,充滿著現實主義的憂患,但同時也借“蘑菇圈”這個核心意象,寫出了多重的象征意蘊:既象征著消費社會中包括藏地在內的邊疆的奇觀化命運,也象征著生生不息的生命法則和精神態度,以及在鄉村自然史與激進現代性的復雜纏繞,在接踵而至的一系列時代劇變中所守護的那一份人性的明亮和溫暖。
一、“消費社會”中藏地的奇觀化命運
小說開頭的第一句話,就預示了藏地未來的某種命運:
早先,蘑菇是機村人對一切菌類的總稱。
“早先”是指1955年以前,人們沒有分門別類的現代科學概念,只是在實用理性的指導下,把蘑菇分作有毒的蘑菇和沒有毒的蘑菇兩類,以便于采摘和食用。“機村”是阿來藏地書寫的根據地,類似于莫言的高密東北鄉或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空山》的副標題即為“機村傳說”,與《空山》寫于同一時段的短篇《水電站》中水電站所在的那個村莊也叫“機村”,最新出版的“六部曲”亦取名“機村史詩”。這一年(1955年)十月,中共七屆六中全會根據毛澤東的報告通過了《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此后全國各地的農業合作化運動急速發展,掀起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高潮。正是在這一高潮中,工作組進駐到機村,不僅帶來了激進的革命理論和思想,也帶來了分類學和命名法,曾經那個統一的“總稱”被解構,“蘑菇”在概念和修辭上有了自己的“家族”和“子孫”。不同種類的菌類植物獲得自己的“命名”,正是蘑菇和藏地參與到激進現代性中來的肇始和標志。
從1955年開始,機村和全國各地的其他任何一個村落一樣,都深深地嵌入到了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的歷史進程之中,從農業合作化到大躍進時期的糧食產量翻一番,從1960年代初的饑荒潮到“文革”時期的破四舊,機村雖然地處偏遠的青藏高原,與主流文化圈隔著重重的山脈,但并沒能擋住政治運動的腳步,因此也就與外界分擔著共同的命運。不只如此,在某個特定的時期,機村還扮演著與漢民族人群的合作者的角色,幫助度過了重大的生存危機。這主要表現在兩件事上。一件是阿媽斯炯對吳掌柜的救助。在機村東頭的茶馬古道上,內地的漢人吳掌柜開了一家代喂馬代釘馬掌的旅店,后來山里通了公路,政府建立了供銷社,茶馬古道就此衰落,吳掌柜也攜老幼回了內地老家。直到六十年代內地鬧饑荒,吳掌柜一家七口餓得只剩他一條命,于是又重返機村。在這個過程中,阿媽斯炯從家里寶貴的鹽巴中勻出一些帶給吳掌柜,延續了他的生命,吳掌柜則教會了阿媽斯炯識別山上的各種野菜,直接幫助全村人度過了那場饑荒。另一件事則是阿媽斯炯和工作組組長劉元萱的恩怨糾葛。在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劉元萱怕影響自己的政治前程和聲譽,狠心拋下阿媽斯炯和膽巴母子,沒有承擔起一個丈夫和父親的責任,這是他有愧于阿媽斯炯的地方。到了新時期,他在生活上夸張地稱贊阿媽斯炯所采的蘑菇之美味,在工作上利用自己的職權助力膽巴在仕途走得越來越遠,以這種方式來緩解自己良心上的不安,來回報那個給他留續香火的阿媽斯炯。
在《蘑菇圈》里,阿來隱而不發,把宏大的對邊疆命運的思考具體化為阿媽斯炯的蘑菇圈的危機,只是在小說的結尾,才以沉重的調子嘆息昔日蘑菇圈的瀕危命運。
小說寫到了人們剛開始感受到自身命運時的那種驚訝和疑惑:
毫無預兆,蘑菇值大錢的時代,人們為蘑菇瘋狂的時代就到來了。
在今天的語境下,這里的“蘑菇”顯然可以替換為“邊疆”。但在它的前面,有必要加一些限定,因為:
不是所有蘑菇都值錢了。而是阿媽斯炯蘑菇圈長出的那種蘑菇。它們有了一個新名字,松茸。當其他不值錢的蘑菇都還籠統叫做蘑菇的時候,叫做松茸的這種蘑菇一下子值了大錢。
松茸“一下子值了大錢”的幕后推手就是“消費社會”的“消費者”。這里的“消費”并不是經濟活動的一個環節或者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次具體消費實踐,而是當今社會普遍化了的一種意識形態,它是“用某種編碼及某種與此編碼相適應的競爭性合作的、無意識的紀律來馴化他們;這不是通過取消便利,而相反是讓他們進入游戲規則。這樣,消費才能只身取代一切意識形態,并同時只身擔負起使整個社會一體化的重任,就像原始社會的等級或宗教禮儀所做到的那樣”①,它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區劃階層,正是在這種區劃中,人們從來不消費物本身,而是把物當做突出自己的符號。消費者只是一個符號秩序,他的消費活動受到符號的操控,真實的物本身死去了。松茸之所以從默默無聞到“一下子值了大錢”,并非因為它比阿媽斯炯蘑菇圈以外的其他蘑菇的營養價值更高,食用口感更佳,而是因為阿媽斯炯的蘑菇圈被建構成了一個差異性符號,使它處于一個在消費者看來更高的等級序列,而消費者購買這種處于更高等級序列的松茸,也就確證了自身比其他消費者處于更高的階層和等級。
最能說明消費符碼化的莫過于丹雅公司的項目了。在離過兩次婚、創過三次業以后,丹雅終于開了竅,決定盤活當地資源,啟動一個野生松茸資源保護與人工培植綜合體的項目。為了讓人們相信她公司的野外培植松茸項目的成功,讓人們看到野生狀態下松茸的生長過程,她在阿媽斯炯隨身的東西上裝了GPS,準確定位到了作為機村秘密的蘑菇圈,然后在蘑菇圈安裝了自然保護區用于拍攝野生動物的攝像機。經過對松茸的這番符碼化過程,丹雅公司生產的任何蘑菇,都可以包裝成阿媽斯炯蘑菇圈里的野生松茸,被投放到城市的各大超市和飯店,被餐桌前各種自認為處于社會較高等級的消費者滋滋有味地咀嚼。
在符碼化的消費社會中,松茸的命運也是藏地乃至邊疆的命運。阿媽斯炯晚年所心傷的蘑菇圈的消失,也正是阿來所心傷的真實邊疆在邊疆書寫中的消失。今天有關邊疆的書寫,已經被“蒼山洱海”“香格里拉”“布達拉宮”等語匯徹底符號化、奇觀化了。特別是在旅游經濟的刺激下,“邊疆”已經成為人們體驗和觀看異民族、異文化和異生活的一個標本,其真實的面目被人隱而不彰、棄而不論;在這種體驗和觀看中,人們的自我形象和心理會發生微妙的變化,某種相對于異民族、異文化和異生活的優越感悄然而生。正是由于這種優越感,旅游才被賦予“療傷”的功能,“出去走一走吧”才成為生活中人們安慰某個失意者的口頭禪。所謂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并非是真的要去“看清”“異樣的世界”,只是通過旅游獲得的那種優越感,來平復先前心里積蓄的不悅或不滿,或者進一步強化先前已有的認知和自尊,而且旅游過程中的“看”也不是因為真的熱愛邊疆的風景,更大程度上不過是熱愛觀看者自己的眼睛,熱愛由風景喚醒的陌生的自己,而這種對觀看者眼睛的肯定又是經由現代“攝影術”實現。與理解是從不接受世界的表象開始相反,攝影恰恰是從接受照相機所記錄的表象出發,由此確證現實和美化經驗,它“已經成為經歷某事的主要裝置,為世界設立了一種長期的看客關系,拉平了所有事件的意義”②。“看客”的這種“看”即是一種消費,一種旁觀而不是進入/介入式的消費,而任何不同人群之間的了解和融合都無法經由旁觀實現,都需要以平等開放的心態真正走進對方,因此這種消費式的觀看,非但不能增進雙方的認同和互信,不能加強一種同情意識和能力,反而會進一步制造疏離或敵視,削弱那種休戚與共感。
這正是阿來作為一個普通的藏族成員最深沉的隱憂,也是他作為一個小說家最大的挑戰。正是這種隱憂和挑戰,構成了馬爾克斯“孤獨”的癥結,因為他和阿來一樣,都“不能用常規之法使人相信這就是我們真實的生活”③。但是在人們想象的建構和旅游經濟已成為重要產業支撐的誘惑下,像希爾頓《消失的地平線》那樣的東方主義敘述,何馬《藏地密碼》那樣的探險故事,在讀者中間仍然頗有市場;而在文學敘事以外,人文學界的某些領域也仍在不斷重復生產著有關邊疆奇風異俗的“地方性知識”,它們構成了消費社會中打造旅游品牌和產品的重要資源。因此如何讓人們意識到“西藏決不是一個形容詞”④,而是一個有實實在在內容的名詞,如何化解把西藏對立于日常生活,把邊疆想象成一個他者、一片有待被“發現”的“風景”的刻板觀念,把西藏還給西藏,就是阿來寫作的內在愿景。
在《蘑菇圈》里,阿媽斯炯的弟弟法海和尚雖然出家在寺,卻并非不沾酒色;“文革”時期,機村的人心也變壞了,人們也喜歡取笑比自己更無助的人;在松茸值大錢之后,法海和尚所在的寶勝寺利用膽巴的關系讓林業局發文把寺院周圍的前后山劃為封山育林保護區,以壟斷保護區內的松茸,與外界想象的不食人間煙火的虔誠的佛教徒形象大相徑庭,而機村人不惜毀滅蘑菇圈,竭澤而漁地瘋狂搶摘松茸,與內地常見的那種逐利而動的小市民并無二致;丹雅在做膩了倒賣服裝這類小本生意后,也利用自己與政府的關系玩起了空手套白狼的商業游戲,與大城市那種投機倒把的貪婪商人也相隔不遠。小說中所有這些祛魅的反浪漫敘述,都是對那種“選擇性看見”的藏地觀察和書寫的反思,對大眾消費行為及其結果的探尋和追問,對消費社會中藏地的奇觀化命運的反抗,這既是文學和文學家的眼光獨特之處,也是文學和文學家存在的理由和價值。
二、自然史與現代性的糾葛
《蘑菇圈》所蘊含的自然或生態題旨,在它甫一問世時,就有人注意到了,比如“原生態文化的挽歌”⑤“文化和自然之鏡”⑥“生態文學的典范”⑦等等。但是如果單純地把它看成梭羅的《瓦爾登湖》,利奧波德的《沙鄉年鑒》和約翰·繆爾的《夏日走過山間》那樣的自然主義文學,則會遮蔽和遺漏掉很多文本信息。因為阿來在小說中處理的并不僅僅是自然主義文學通常討論的敬畏自然和生態保護之類的議題,還表達了對人與自然之間一種嶄新關系的思考,這種關系延伸到當代中國社會的突出表現,就是本土鄉村的自然史與激進的現代性之間的復雜纏繞。迄今為止,人們也尚未找到能解開此一纏繞的有效思路。
在通常有關人與自然關系的討論中,“人”與“自然”被區隔成兩類存在,即使在古人“天人合一”“敬畏自然”等話語中,“自然”也被當做一個外在于人本身的事物,而環保主義者通常所宣傳的“人生活在自然之中”的“在”也只是身體和需要上的依賴,“人們一旦出軌,自然就會挺身而出發揮作用”,等“創傷得到醫治,人們又被重新整合到和諧的川流或系統之中”⑧,并非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里所闡釋的那個“在……之中”。如果從哲學上溯源,這種把“人”與“自然”區隔成兩類存在的思維和觀念,按照黑格爾的說法,是從中世紀開始,并且在近代西方哲學的形而上學建制中進一步得以確立的:“中世紀的觀點認為思想中的東西與實存的宇宙有差異,近代哲學則把這個差異發展成對立,并且以消除這一對立作為自己的任務。因此主要的興趣并不在于如實地思維各個對象,而在于思維那個對于這些對象的思維和理解,即思維這個統一本身;這個統一,就是某一假定客體的進入意識”。⑨“人”和“自然”之間笛卡爾式的二元對立思維就這樣主導了人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思考,并且在對人和自然究竟誰先誰后、誰創造了誰這一問題的追問中進一步鞏固了此種對立。
在《蘑菇圈》里,人與自然的關系,主要表現為阿媽斯炯與蘑菇圈的關系,既不是笛卡爾式的二元對立,也不是天真的浪漫主義者所信奉的人生活在自然之中,而表現為一種人與自然相互生成、彼此應和的特殊關聯。這種生成和應和不是某種神秘主義的特殊感應,也不顯得牽強作態,而是可聞可見、可觸可感的實在關系。在小說開頭,作者運用復沓的手法寫到布谷鳥的鳴叫:
五月,或者六月,某一天,群山間突然就響起了布谷鳥的鳴叫。那聲音被溫暖濕潤的風播送著,明凈,悠遠,陡然將盤曲的山谷都變得幽深寬廣了。
阿媽斯炯說,要是布谷鳥不飛來,不鳴叫,不把白天一點點變長,這夏天就沒有這么多意思了。
聽見山林里傳來這一年第一聲清麗悠長的布谷鳥鳴時,人們會停下手里正在做著的活,停下嘴里正說著的話,凝神諦聽一陣。
不止是機村,機村周圍的村莊,在某個春深的上午,陽光朗照,草和樹,和水,和山巖都閃閃發光之時,出現這樣一個美妙而短暫的停頓。不止是機村,不止是機村周圍那些村莊,還有機村周圍那些村莊周圍的村莊,在某一時刻,都會出現這樣一次莊重的停頓。⑩
布谷鳥的鳴叫,將“盤曲的山谷變得幽深寬廣了”,使夏天變得更有意思了,讓藏地的人們在辛勞的忙碌中出現“美妙而短暫的”“莊重的”停頓。因為機村的村民們都被布谷鳥所代表的那種“靜靜地進行創造”,“主動的、默默無聞的工作” 的思想所打動。在這種人與自然的相互應和中,自然的地理條件變得更加宜人了,人類勞作的疲累感得到舒緩了。除此之外,小說中寫人與自然彼此應和的地方還有很多。比如第107頁,膽巴跟阿媽斯炯講劉元萱主任對自己特別照顧,阿媽斯炯本來想把話回過去,說劉元萱曾經對她也特別關心,但是一看到外面“天空湛藍,河水碧綠”,立即就收住了嘴。又如第177頁,阿媽斯炯倒在蘑菇圈的草地上,等她支撐起身子以后,雨后的太陽照耀著近處的櫟樹、杉樹和柳樹,照著遠山上連成一片的滿眼蒼翠的樹,而在這空濛的蒼翠之中,還橫著一條艷麗的彩虹。這時,阿媽斯炯就聽見自己在心里說,“斯炯啊這一天到來了”。等到阿媽斯炯打電話給兒子膽巴時,她并沒有陳述自己摔倒的事實以及身體上的不適,只是告訴兒子自己看見彩虹了,而膽巴似乎也完全能聽懂“看見彩虹”的意思,回話時不自覺地就帶出了哭聲。在阿媽斯炯那里,蘑菇圈不僅僅是困難年代幫助她養活家人的果腹之物,晚年幫助她給孫女積攢學費的生財之物,而且是她精神情感的伊甸園,是她全部喜怒哀樂的寄托所在。去蘑菇圈里轉一轉,不僅僅是因生存之需,更是一種生活方式。蘑菇圈被商人高價收買,就是拿自己的人格去抵換金錢;蘑菇圈的消失,意味著一種生活方式的消失。這正是阿媽斯炯心傷的深層原因。由此,阿來筆下的“蘑菇圈”就好像契訶夫筆下的那個“櫻桃園”,以其濃厚的象征性而與更宏大的存在聯系起來。
在人與自然這種相互生成和應和的關系背后,其實隱含了阿來自己獨異的自然史觀。在《我為什么要寫“山珍三部”》里,他反復提到土耳其作家帕慕克的一句話:“每一個人都應該對于我們對自然的無知而感到恐懼。” 這種無知既包括對自然本身的無知,也包括對無限索取自然所造成的嚴重后果的無知。前者使阿來意識到尊重和保護自然必須從認知開始,于是身體力行去觀察自己生活的地方的植物,寫出了《草木的理想國:成都物候記》,后者讓他去思考人類對自然的過度索取會有怎樣的后果,于是松茸、蟲草和柏樹就被拿來做試驗,結果自是觸目驚心。在《河上柏影》的跋語“需要補充的植物學知識,以及感慨”里,阿來明確表達了自己的自然史觀:
樹站立在這個世界上,站在谷地里,站在山崗上,扎根沃土中,或者扎根石縫中的歷史是以千年萬年億年為單位來計算的。人當然出現很晚。他們首先懂得從樹上摘取果實。然后,他們懂得了燃燒樹木來取得溫暖與熟食,同時從不安全的黑夜里取得使家人感到安全的光亮。他們懂得用骨制的工具剝下樹皮制成御寒的衣服,進而因為這種成功的遮蔽生出關于羞恥的觀念,或者根據樹皮衣服完好的程度美觀的程度生出關于美,關于尊貴與低賤的觀念不過幾千年時間。
也就是說,樹不需要人,人卻需要樹。人的生存無論在物質需求上還是精神觀念上,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都是在自然界中的生活,都是以自然界為對象,而且正是在這個對象性的活動(“成功的遮蔽”)中,人的感性的豐富性(“羞恥的觀念”“美的觀念”“尊貴于低賤的觀念”)才逐步得以產生和發展。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不僅五官感覺,而且連所謂精神感覺,實踐感覺(意志、愛等等),一句話,人的感覺、感覺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對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產生出來的,五官感覺的形成是迄今為止全部世界歷史的產物。” 因此,從漫長的歷史演進過程來看,人與自然是相互生成的,人類史與自然史也是統一的,具體表現為二者相互關聯和制約。但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這種“統一”也處于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歷史形態。在當代中國社會,“人類史”大致可以概括為激進現代性的歷史,人類史與自然史的關系,也就主要體現在自然史與現代性的糾葛。
在《蘑菇圈》里,由于受經濟利益的驅動,阿媽斯炯的蘑菇圈被村民、丹雅這樣的商人和地方政府所合圍,大規模的開發和蘑菇成長環境的惡化,是遲早要到來的命運,農耕時代阿媽斯炯那種環境友好型的采摘方式一去不返,涸轍之鮒的悲劇不可避免,自然史與現代性的交鋒在這里達于頂端,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不論是阿媽斯炯、法海和尚、吳掌柜、劉元萱、膽巴和丹雅的現實生活遭際,還是1955年后激進現代性所引起的歷史動蕩,都被安置于自然史的基礎上,都各各得到包容,一如陳忠實《白鹿原》中的白鹿原對發生在原上的歷史波瀾的容納。盡管弗洛伊德、韋伯、齊美爾、馬爾庫塞、哈貝馬斯等思想家都曾經指出過現代性的內在緊張,并以審美現代性來對抗資本主義現代性的金錢崇拜,但在現代性還是一項未竟的工程,現代化程度還在如火如荼地推進的當下中國社會,人工蘑菇大棚對天然蘑菇圈的取代,就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阿來并非看不到這一歷史趨向,也不是張承志和張煒那樣的道德理想主義者和文化保守主義者,反而對那種為了滿足“進步社會中某些人對所謂‘文化多樣性’的觀感”,就希望“一些人與國家時時進步,另外一些人與社會停滯不動” 的主張不以為然,只是目睹阿媽斯炯那具有精神家園意味的蘑菇圈的消失,目睹那些唯利是圖者對自己身處自然環境的漠視,而又尚未“找到新的語言方式、新的修辭方式、新的審美,來表達新的內容” ,因而就不能不感到深深的困惑與無奈。
三、守護時代劇變中的人性溫暖與悲憫
《蘑菇圈》的敘事時空中,當代的一系列重大社會和政治事件,從農業合作化運動、人民公社運動到文化大革命,都有明確的交待,而且還圍繞這些事件展開了有細部有情節的敘述:工作組為了完成糧食產量翻番的目標,動員公社社員拼命往麥地施肥,結果因為麥子長得過于茁壯遲遲不肯熟黃而被連續三夜的霜凍給全部凍死,最終莊稼顆粒無收,社長上吊贖罪;文化大革命時期,機村在外上學的紅衛兵開著卡車回來,興沖沖地揪出了村里最大的當權派劉元萱,在村里廣場燃起篝火連夜開批斗大會,散會后又打斷他的一條腿和兩條肋骨。這些在當代史上實有其事的情節,在新時期文學之初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以及蘇童、莫言、賈平凹、閻連科、余華、方方等人的作品中,已經成為經典的敘事場景。不過,令人不解的是,盡管《蘑菇圈》也寫了那些生死打斗,也揭示了那個時代的荒謬和殘酷,卻讓人在讀完之后感受不到憤怒和分裂,更感受不到恐懼和顫栗,這與其他很多描寫同類事件的作品,比如《現實一種》《米》《風景》《檀香刑》帶給人的仇恨、陰森和暴戾之感殊為不同。在它的情節安排和人物形象身上,人們始終感到一份沉甸甸的善意和悲憫。
最能體現這種善意和悲憫的,莫過于小說的主人公阿媽斯炯了。在她與劉元萱的關系上,我們常見的寫法要么是讓劉元萱把阿媽斯炯欺負得更狠,以此召喚讀者對劉元萱道德和情感的義憤,要么是讓劉元萱在新時期歸來者的權力分配中占不到位置,以示對他當年所犯罪過的懲罰。阿來的處理別具匠心,他既沒有讓阿媽斯炯在遭到劉元萱的欺負后,帶著滿腔的恨意隱忍地活著,也沒有呈現劉元萱在新時期懷著負罪感終日寢食難安的狀態。阿媽斯炯什么人也不記恨,只是頑強地勇敢地活下來,把法海和尚和膽巴照顧好。劉元萱在新時期官復原職之后,也沒有過深地懺悔自己曾經的錯誤,只是在對阿媽斯炯的松茸的喜愛和對膽巴事業的提攜上,委婉地表露自己的心曲。從阿媽斯炯善良的天性和劉元萱所處的知識文化水平來看,這是符合實際、也是把自己擺進去了的筆法。不把作者自己擺進去的寫作,是一種置身事外、居高臨下的寫作,當然就可以局外人的身份和姿態,把場景安排得十分戲劇化,把情節設計得極富張力,使作品充滿極端的思想情感和人物行為。從表象上看,后一種寫法似乎更像小說,也更能吊住讀者的胃口,但其實并不符合共同的人性的真實。在真實的生活場景中,黑白分明、善惡有報的事件屈指可數,更多的往往處于一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都無法有效規劃和描述的模糊和混沌地帶,而這些所在正是文學專攻的術業。
阿媽斯炯的善良也體現在她對村民的態度上。六十年代初機村鬧饑荒,阿媽斯炯意外地從吳掌柜那里學得識別山里野菜的方法,再加上她自己背水灌溉所培育出來的松茸,使她不但平安度過了災年,還有余力幫襯村民,每到夜晚就出門挨家挨戶地送野菜和松茸,即使是曾經深深傷害過她的工作組,她也照送不誤。四清工作組那個身材瘦小、領著組員讀《人民日報》的女組長來阿媽斯炯家詢問膽巴的身世,顯然是來者不善、別有用心,但阿媽斯炯卻并不防備和反感,反而看女組長臉色蠟黃心里過意不去,不停地煮熱茶加牛奶煨豬肉給對方吃,等到女組長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阿媽斯炯又主動追進去拿蘑菇圈生生不息的故事來安慰人。這種筆鋒常帶感情的寫法,并非因為阿媽斯炯作為一個藏族女性要比其他民族的女性來得善良和偉大,也不是說阿來在寫作過程中蘊蓄了過量的不忍之心,回避了生活中的冷漠和不義,縱容歷史深處的罪惡和暴行,而是因為在一個劇變的時代,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煙了,大多數人都不是主宰歷史的英雄,都經歷過身心或情感上的犧牲,都或多或少要遭遇無所適從的悲劇,都值得也需要一絲人性的悲憫和溫暖。二戰前夕,本雅明在他那篇著名的《講故事的人》中就描述過時代劇變后人之卑微和無力的境遇和心態:“乘坐馬拉車上學的一代人現在佇立于荒郊野地,頭頂上蒼茫的天穹早已物換星移,唯獨白云依舊。孑立于白云之下,身陷天摧地塌暴力場中的,是那渺小、孱弱的人的軀體。” 在《蘑菇圈》的序言中,作者自己也表達過這層意思:“我愿意寫出生命所經歷的磨難、罪過、悲苦,但我更愿意寫出經歷這一切后,人性的溫暖。即便看起來,這個世界還在向著貪婪與罪過滑行,但我還是愿意對人性保持溫暖的向往。”
但是善良并不意味著愚昧和糊涂。隨著九十年代中國社會的市場化轉型,商品交易的氣息也滲透到了藏地的人心之中。機村人天剛破曉就起身去往林中尋找松茸,在林中踩出一條條板結的小路來,還有一些村民更加心急,他們等不及蘑菇自然生長,就提著釘耙上山,扒開那些松軟的腐殖土,取走連菌柄和菌傘都沒分開的小蘑菇疙瘩。面對村民們貪婪而瘋狂的采摘行為,阿媽斯炯并沒有一廂情愿地去阻止,而且當兒子膽巴準備在村里成立松茸合作社,通過訂立鄉規民約的辦法來保護松茸資源時,她不但不予支持,還說出了下面的一番話來:
你以為你把我的蘑菇圈獻出來人們就會被感動,就會阻止人心的貪婪?不會了。今天就是有人死在大家面前,他們也不會感動的。或者,他們小小感動一下,明天早上起來,就又忘記得干干凈凈了!人心變好,至少我這輩子是看不到了。也許那一天會到來,但肯定不是現在。我只要我的蘑菇圈留下來,留一個種,等到將來,它們的兒子孫子,又能漫山遍野。
這種理性清醒、愛憎分明的處世態度,使阿媽斯炯這位藏族女性形象顯得更加立體和豐滿。特別是在膽巴和他妻子娥瑪帶女兒回機村看望阿媽斯炯的晚上,兩位年輕人傍在阿媽斯炯身邊,靜靜地聽她回憶自己一路走過來的種種。當她聽說劉元萱已逝的消息時,眼睛移向別處:“這下我不用再因為世上另一個人而不自在了”,真是有種說不盡的悲愴和解脫,而娥瑪重復的那句“膽巴,你怎么有這么好一個媽媽”“阿媽斯炯,膽巴是什么命,有你這么個好媽媽”,更讓人潸然動容。
利維斯在《偉大的傳統》中下過這樣的判斷:“所謂小說大家,乃是指那些堪與大詩人相比相埒的重要小說家——他們不僅為同行和讀者改變了藝術的潛能,而且就其所促發的人性意識——對于生活潛能的意識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義。” 阿來能否當得起“小說大家”或者“重要小說家”的稱號,無需時人臧否,自有時間和文學史的篩選,但在《蘑菇圈》這部中篇里,他塑造的阿媽斯炯這個人物形象“所促發的人性意識——對于生活潛能的意識”,也就是那種在多變的塵世帶給人們的命運之中,仍然保持對人性亮色和溫暖的向往,仍然葆有生命的堅韌和情感的深厚,這種“促發”對于遭遇時代劇變、親歷震驚體驗的人們而言,顯然“具有重大的意義”。
注釋:
①[法]鮑德里亞:《消費社會》,劉成富等譯,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頁。
②[美]蘇珊·桑塔格:《論攝影》,艾紅華、毛建雄譯,湖南美術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頁。
③[哥倫比亞]馬爾克斯:《拉丁美洲的孤獨》,《諾貝爾獎的幽靈:馬爾克斯散文精選》,朱景冬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版,第133頁。
④阿來:《西藏是形容詞》,《就這樣日益豐盈》,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135頁。
⑤孫德喜:《原生態文化的挽歌:論阿來的中篇小說〈蘑菇圈〉》,陳思廣主編,《阿來研究》(第3輯),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⑥程德培:《文化和自然之鏡:阿來“山珍三部”的生態、心態與世態》,《上海文化》2016年第11期。
⑦于國華:《生態文學的典范:阿來的“山珍三部”》,《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4期。
⑧[英]以賽亞·伯林:《浪漫主義的根源》,亨利·哈代編,呂梁等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79頁。
⑨[德]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4卷),賀麟、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6頁。
⑩阿來:《蘑菇圈》,人民文學出版社版2016年版,第2—3頁。
[德]席勒:《論天真的詩和感傷的詩》,《席勒文集》(第6冊),張玉書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79頁。
阿來:《我為什么要寫“山珍三部”》,《阿來研究》2017年第1期。
阿來:《河上柏影·跋語》,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頁。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頁。
阿來:《文學和社會的進步與發展》,《當我們談論文學時我們在談論什么》,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41頁,第26頁。
[德]阿倫特編:《啟迪:本雅明文選》(修訂譯本),張旭東、王斑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96頁。
阿來:《蘑菇圈》,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頁,第158頁。
[英]F·R·利維斯:《偉大的傳統》,袁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4頁。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