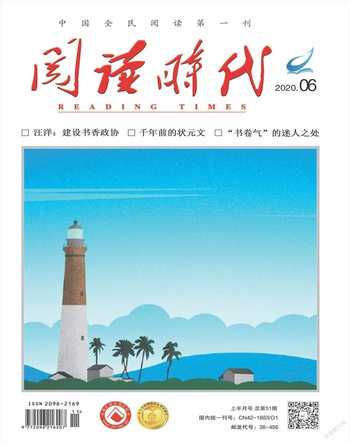瘟疫中,薄伽丘為何寫《十日談》
王晴佳
在人類歷史的演化過程中,瘟疫時時與人相隨。歐洲歷史上更是暴發過多次,14世紀發生的“黑死病”更是讓人難忘。由此緣故,西方作家寫瘟疫的,當然不止加繆的《鼠疫》一本。比如“黑死病”猖獗的時代,便有意大利作家喬萬尼·薄伽丘的《十日談》,為西方文學史上的名著。此書的寫作背景,至少按照作者交代,正是“黑死病”發生的那個世紀。薄伽丘講的是七女三男為了避疫,躲進了一座山莊。為了消磨時光,各人講故事度過了十天,于是取其為書名。
瘟疫降臨,逃向一處“人造的”世外桃源
與《鼠疫》不同的是,《十日談》中的內容,除了在起始的部分交代此書的寫作緣由之后,幾乎沒有怎么涉及瘟疫如何影響人類的行為。薄伽丘似乎只是以瘟疫的發生作為契機,像阿拉伯文學名著《一千零一夜》和蒲松齡寫作《聊齋志異》那樣,其收入的故事嬉笑怒罵、應有盡有,似乎以獵奇、新穎為主要目的。其筆調亦輕松戲謔,并不著意探討瘟疫下的艱難人生及其痛苦的應對。我讀了幾篇之后,便將之放下了。
2月開始,病毒已經走出中國、亞洲,在世界各地大規模流行。3月之后,我所在的美國東部更迅速成為疫情的中心,感染、死亡人數急劇增加,至今尚未看到好轉的拐點。學校、圖書館關門,我閉門不出,時時通過各種渠道了解疫情和人們的應對,時而傷感、時而悲憤、時而又歡喜振奮,情感上的波動可謂五味雜陳,感觸良多。帶著這樣復雜的心情,重新展讀《十日談》,對薄伽丘的處理方式,忽然有了一種別樣的感受。
首先,薄伽丘的寫作突出了瘟疫降臨之出乎意料,如何讓人措手不及。此次新冠病毒的來襲,亦是如此。歐美各國對于疫情在當地的傳播之快,均缺乏心理準備。薄伽丘在書的起始寫道:“在碩果累累的一千三百四十八年,意大利最美麗的城市,出類拔萃的佛羅倫薩,竟發生了要命的瘟疫。不知是由于天體星辰的影響,還是因為我們多行不義,天主大發雷霆,降罰于世人。”
在科學發達的21世紀,大多數人自然不會視病毒為天主的懲罰,但對這次病毒的根源,醫學界仍然莫衷一是。而如果我們遵中國的傳統思維,將“天”視為自然界的代表,那么我們還是可以基本認定,人類的自以為是,對自然界和其他生物所持之頤指氣使、任意對待的態度和行為,應該是這次病毒暴發的最終原因。
薄伽丘對瘟疫傳播的描述,讀來也讓人感慨唏噓,不得不嘆其逼真和形象。他說“那場瘟疫來勢特別兇猛,健康人只要一接觸病人就會傳染上”。他接著形容道:“更嚴重的是,且不說健康人與病人交談或者接觸會染上疫病、多半死亡,甚至只要碰到病人穿過的衣服或者用過的物品也會罹病”。此次新冠肺炎的傳播,又何其相似!
瘟疫對人類社會的突然襲擊,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加繆雖是小說家,但選擇“記事”式的方式來描繪其危害。而薄伽丘則別具一格。他在交代了瘟疫的猖獗之后,筆鋒一轉,向讀者描繪了一個“人造的”世外桃源:俊男美女選擇了一處風景秀麗的場所,衣食無憂、嬉戲玩耍,講故事取樂,而他們所講的故事,則主要以各式各樣的愛情、情愛為主題,似乎與當時人們所經歷的那場災難,毫不相干。
只有遇到巨大災難,才有對愛情的癡迷
《十日談》一書共有十章,以十位男女在山莊避難的十天為框架,每天一章,記錄他們所講的故事。除了第一章之外,幾乎都以男女之間的情愛為主。這些情愛的故事,有著喜怒哀樂的各種不同結局,反映了男女情人為了博取、獲得愛情(包括滿足私欲)而做的種種努力,其中也有讓人覺得有損道德的行為。前人的研究已經指出,薄伽丘此書曾一度被認為傷風敗俗而列為“禁書”,而其價值正是在于他作為文藝復興時期的重要作家,通過此書寫出了人生百態、人性之復雜——人之為人既有高尚、勇敢的品格,又有怯懦、自私等種種缺點,展現了那時開始興起的個人主義思潮。
中國有句老話:大悲若喜,與大智若愚相仿。鄙以為薄伽丘在瘟疫盛行的時刻,以情愛為主題寫作,歌頌愛情,寫出了人們為愛所做出的努力和獲得的歡喜,正是這一成語背后之深切含義的寫照。他在書中描繪的情愛故事,往往超越了常理,跨越了階級,雖然有些結局不夠理想,甚至滑稽,但大多成皆大歡喜之結果。比如薄伽丘借人之口說道:“愛情的力量不是我們所能抗拒的。”在另一處,他又描述了一個婦人為了心愛之人,不顧自己地位的高貴,執意相愛。她的弟弟們嘲笑她,她的回答則是:“我的好兄弟,你們說的情況我很清楚,不過我嫁的是人,我寧愿要一個沒有財富的男子漢而不要沒有男子漢的財富。”
薄伽丘筆下這種對愛情的癡迷,或許只有在人類遇到巨大災難的時候才能體會。這次新冠肺炎病毒的襲擊,人們看到許多生離死別。但這些大悲,又顯現出大愛。有多少人在看到電視上對李文亮父母的采訪、讀常凱給家人的遺書和看著護士長蔡麗萍追著其夫劉智明院長的靈車奔跑的場景落淚,對其中表現出的大愛所深深感動。
筆者所謂的“大愛”,指的是在生離死別的時候,那種穿越了過去、原諒了一切,唯有讓愛凌駕一切的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我們都知道,家人、親人和愛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一直和諧無間,而是常常有爭吵、矛盾的時候。但在疫情襲擊之下,當所愛之人猝然離世、告別親人的時候,對于生者來說,似乎最重要的就是要向其表示自己尚未說出的深愛。筆者以為,薄伽丘在面對瘟疫流行的時候,選擇以愛情為書的主題,足以表現了他對人生的深刻感悟。
揭露和諷刺教會的虛偽與丑陋
今天閱讀《十日談》之價值,除了看到瘟疫中人類所表現出的愛,還應該看到書中所表達的憎。那就是薄伽丘對說謊、欺騙、虛偽等丑行的諷刺和揭露,而書中犯有這些行為的人,幾乎都是有頭有臉的上層掌權人士,如教父、法官和修士。他們道貌岸然,表面上光鮮無比、高高在上、發號施令,充當普通人的救主,但其實男盜女娼、無惡不作,以欺騙、說謊為能事,根本不顧大眾的利益。
在他的筆下,那些加入教會的人中,不少人本來就是無恥之徒,只是為了私利、私欲而成為了教士,但本性不改。比如一個故事講到,一個荒淫之徒披上了法袍,但仍然垂涎一個婦人,而當她拒絕他的時候,他居然大言不慚地說道:“夫人,假如我脫掉這身法袍——這是再容易不過的事了,我就不是教士,而和任何男人一樣了。”
而書中最有諷刺意味的一個故事是,巴黎有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商人,與一個猶太商人亞伯拉罕是莫逆之交,十分希望后者能放棄猶太教而皈依天主教。在他的竭力勸說下,亞伯拉罕說他要眼見為實,去一次羅馬觀摩一下天主教的內幕。這反而讓他的朋友覺得為難,因為他知道如果亞伯拉罕去了那里,深入了解了天主教會的腐敗丑行,一定不會皈依了。亞伯拉罕去了羅馬,看到了教皇、紅衣主教和其他神職人員的行為之后,對他的朋友說:“我在那里根本沒有看到什么圣潔、虔誠、慈善、模范的生活,或者稱得上教士的人。我在各處看到的仿佛只有淫亂、貪婪、饕餮、欺詐、妒忌、傲慢……以致我覺得不是一個神圣的溫床,而是罪惡的策源地。”但亞伯拉罕的最后決定卻讓其朋友大出意外,因為他居然放棄了猶太教,加入了天主教,并在“后來成了一個德高望重的好人”。
薄伽丘在《十日談》中的這些描寫,深入骨髓,明白無誤地表達了他的愛憎。而他在瘟疫猖獗的時刻對這些上層人士的丑行加以如此揭露和鞭撻,堪稱一絕。因為在病毒肆虐全球的時刻,我們不但目睹了人間的摯愛深情,也看到不少謊言、自大、欺詐、輕狂和虛假的行為。后者助紂為虐,為全人類的抗疫造成了阻礙。筆者由此覺得薄伽丘此書,在這個非常時期,非常值得一讀。
(作者為北京大學歷史系長江講座教授、美國羅文大學歷史系教授,4月5日寫于為疫情所困之美國新澤西州)
責編:王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