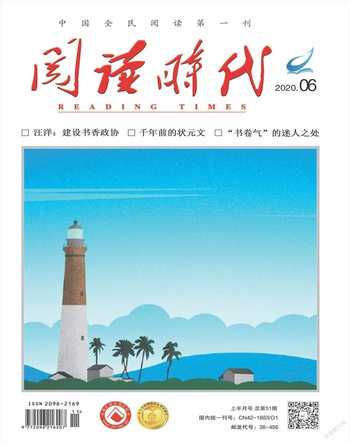中國“最后的大儒”梁漱溟
莫一奧
01
1918年11月7日,一位年過花甲的老者與他二十五歲的兒子有這樣一次對話。
老人問兒子:“這個世界會好嗎?”兒子回答道:“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能好就好啊!”老人說完,就離開了家。
三天之后,老人留下一篇《敬告世人書》,在積水潭投湖自盡。曉風殘月,凄涼、安祥……這是一場精心準備好的死亡——此時,距離老人六十大壽只剩下四天,這個真正的儒者說,我對這個民國,失望到了極致。
1918年的中國,波詭云譎,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中國國內又激戰甚酣,即便如此,老人的去世依舊對京城文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舉凡新舊兩派人物,徐志摩、陳獨秀、李大釗、胡適、梁啟超等人,議論紛紜。
那個二十五歲的兒子,當時已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最年輕的教師。許多年以后,他回憶起與父親梁濟最后的那次談話,感慨頗深:“父子最末一次說話,還說的是社會問題。自從先父見背之日起,因他給我的印象太深,事實上不容許我放松社會問題,非替社會問題拼命到底不可。”
父親的自殺對也想過自殺的兒子是一個啟示——有人說,“民族血脈的新舊交替,這驚遽的時刻總要有人來表現,這位父親選擇了表現;這驚遽的時刻過后總要有人去承擔,這位兒子選擇了承擔。”
這位堅信“世界會變好”的兒子,叫梁漱溟,在中國現代思想史上,他被稱為“中國最后一位儒家”。
02
清光緒十九年(公元1893年)重陽節,梁漱溟生于北京紫禁城腳下安福胡同一間小屋。從曾祖父開始,都是念書人,也都做過官,家境卻始終不寬裕,是陳寅恪先生所謂的“寒素”之家。
在梁漱溟的印象里,父親梁濟跟孩子之間的關系是莊重的、平等的,又是尊重的。在梁漱溟的記憶中,父親對他“完全是寬放”的,甚至“很少正言厲色地教訓過我們”。
到開蒙的年紀,父親不讓梁漱溟讀“四書五經”,倒讓他看《啟蒙畫報》,念《地球韻言》。梁漱溟六歲入北京第一所西式學堂——中西小學堂,學習英文,八歲就讀于公立小學堂、蒙養學堂,十三歲考入地安門外順天中學堂。梁漱溟曾經多次報考北大但始終名落孫山,最后他考入了直隸公立法政專門學校,這便是梁漱溟一生最高的學歷。
1912年,梁漱溟任《民國報》編輯兼外勤記者,總編輯孫炳文為其擬“漱溟”作筆名。由于對人生的迷茫,心理上的痛苦,梁漱溟開始讀佛典。1917年,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讀到了在《東方雜志》連載的長文《究元決疑論》,遂邀請作者梁漱溟去中國最高學府北京大學任教。
沒想到,這個只有專科學歷的24歲青年,竟然在到校的第一天對蔡元培校長說:我不到大學則已,如果要到大學去做學術方面的事,就不能隨便做個教師便了,一定要對儒、釋兩家的學術,至少負一個講明的責任。請問蔡先生,對孔子持什么態度?
蔡元培略一沉吟說:我們也不反對孔子。
梁漱溟正色說:我不僅是不反對而已,我這次來北大,除了替釋迦和孔子發揮外,不做其他的事!
此后,見到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梁漱溟依然這樣鏗鏘有力。
然而就在第二年,父親梁濟沉潭自盡,面對洶涌澎湃的新思潮,曾經數次出世、入世搖擺不定的梁漱溟終于決心入世,推崇儒學,寫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從此開啟了自己的儒學人生。
03
梁漱溟在北大待了七年后,一方面因不滿北大只重知識的西式教育,另一方面不想當個閉門做學問的圣人,于是1924年辭掉了北大教職,先后在河南、山東等地進行鄉村建設實驗,探尋救國救民之路。
梁漱溟特別佩服對于同樣身體力行進行鄉村建設的先驅陶行知先生,直到晚年,他還念念不忘。終其一生,梁漱溟都囑咐自己的二兒子培恕:你不要忘了自己是陶先生的學生。
后來,梁漱溟的鄉村建設事業被迫終止,但思想體系日臻成熟。
梁漱溟曾回憶與當時一些軍閥的交往,這些軍閥不僅請知識分子和學者到軍隊里傳播知識,還請他們當顧問,尊為座上客,禮遇有加,并且盡力支持他們的事業。1924年,駐扎在北京南苑的馮玉祥托人請梁漱溟為其軍隊作演講,共講了五次。
閻錫山也曾請梁漱溟去山西作講演,講了一個月。1930年,閻錫山聘請梁漱溟為高級顧問,月薪五百元。后來因為閻錫山未采納其關于裁軍和停止內戰的建議,梁漱溟辭去了顧問的職務。
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發,日軍進攻香港,避難到香港的文化人士乘船撤離,天上有飛機轟炸,水上有水雷騷擾,滿船的文人學者都惴惴不安,夜不安眠,只有梁漱溟鼾聲如雷,睡得很香。
有人問:先生不害怕嗎?他說:怕什么,我是死不了的,我死了,中國怎么辦?
04
梁漱溟的確說過,“我不是一個學者”,在他心目中“為社會奔走,做社會運動”是一生中最重要的大事。
晚年,他對前來采訪的美國學者艾愷說:我的生活,固然做過記者了,教過書了,做過教員了,可是實際上比較重要的是做社會運動,參與政治。
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大事,就是為國內黨派的團結抗日。因為我去了游擊區一次,在游擊區看見兩黨的軍隊,我就很怕引起內戰,引起內戰就妨礙了抗日,抗日期間不可以有內戰啊,所以我就先搞“統一建國同志會”,后來搞“民主同盟”。旁人就誤以為我是想搞一個自己的黨派,其實不對。我不認為中國需要兩大黨之外,還要一個第三黨派,我沒有這個意思。民主同盟不是第三個黨派,是什么呢?是想推動兩大黨團結抗敵,合作建國。能夠團結抗敵就好了,能夠合作建國就好了。自己不想成一個什么黨派。
1946年,李公樸、聞一多相繼被殺,梁漱溟發表了義正嚴辭的譴責,他說:“我個人極想退出現實政治,致力文化工作。但是,像今天這樣,我卻無法退出了,我不能躲避這顆槍彈,我要連喊一百聲:取消特務!”
梁漱溟踐履篤實,冒著吃“第三顆子彈”的危險,代表民盟赴昆明調查李、聞慘案,終將反動政府暗殺民主人士的罪行告白天下。
05
梁漱溟曾與毛澤東有很深的來往,1918年,在毛澤東岳父楊昌濟家中,兩位同齡人就已相識。二十年后,梁漱溟到延安,在十六天里與毛澤東有過八次交談,有兩次是通宵達旦。
在梁漱溟心中,毛澤東是開天辟地的偉人,他說過:“毛主席這個人呢,我跟他接觸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并且他沒有什么憑借,他不是原來就有勢力的一個人,他都是單身一個人。他的家鄉韶山,我去過兩次,他進修的地方,我都去看,他讀書的地方,他家鄉的人,我們都見到。他十五六歲還在鄉里種地,這么樣光身一個人,居然創造一個新中國,實在是了不起,實在是了不起。”
即便如此,在1953年一次重要會議上,梁漱溟還是為了自己堅持的觀點,當面頂撞毛澤東,進而引起巨大風波。
1953年9月中旬,梁漱溟列席中央政府擴大會議,應邀發言,重點是談農民問題,他指出“我們的建國運動如果忽略或遺漏了中國人民的大多數——農民,那是不相宜的”,由此引發毛澤東極大的不滿。
特別是梁漱溟在發言中引用某人所說“工人農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的話,讓毛澤東火冒三丈,在會上將梁漱溟臭罵一通,說:“蔣介石用槍桿子殺人,梁漱溟是用筆桿子殺人。”
梁漱溟不服氣,登臺發言,多次爭辯,在巨大的壓力下,卻依舊“態度安定從容”。直到晚年,在親友的勸說下,更在自己的反躬自問下,他對當年自己的“氣盛”做了檢討,他意味深長地說:“當時是我的態度不好,講話不分場合,使他(指毛澤東)很為難,我更不應該傷了他的感情,這是我的不對。他的話有些與事實不太相合,正像我的發言也有與事實不符之處,這些都是難免的,可以理解的,沒有什么。”
這位中國“最后的大儒”就是這樣襟懷坦白,坦然處之。
06
十年浩劫中,梁漱溟被趕出居室,住在簡陋的小屋內,尚未完成的《人心與人生》手稿也被抄沒。他寫信給毛澤東說:“若此稿毀卻,我生于斯世何益。假如在或斗或批之后,不發還此書稿,即不可能敘寫,無異乎宣告我的死刑。”
在毛澤東的安排下,該手稿得以退還。1975年,梁漱溟終于完成了這本他一生視若人生至寶的《人心與人生》。
在“四人幫”猖獗時,梁漱溟仍不顧個人身處逆境,仗義執言。當受到圍攻時,他傲然宣稱:“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
終其一生,梁漱溟視自己為佛教徒。他說:佛教徒他把什么事情都看得很輕,沒有什么重大的問題,什么都沒有什么。再說到我自己,我總是把我的心情放得平平淡淡,越平淡越好。
1988年6月23日,梁漱溟的人生大幕垂下,享年95歲。
去世前,他曾接受一位臺灣記者的采訪,只說:“注意中國傳統文化,順應時代潮流。”這可以視為梁漱溟的遺言。
責編:王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