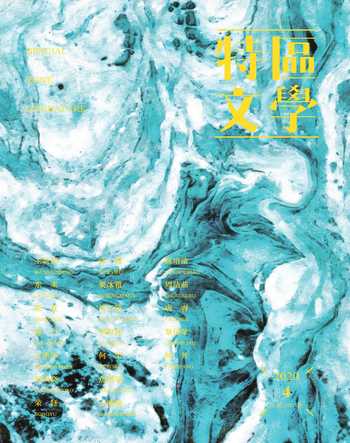剛誕生的詞語乘坐拼圖游戲穿過生猛暗夜
陳思安
《周瓚詩選》是詩人周瓚詩歌創作21年的精選集。身兼劇作家和學者的詩人將全書分為三輯,分類依據的是她如編劇般精妙設計,并與讀者分享自己的創作歷程。我們跟隨著詩人的腳步,由第一輯中她在近年來全新展示出的強勁詩歌面貌開幕,經過第二輯詩人于各個時期的代表作形成高潮,最終由第三輯詩人失而復得的遺珠之作完成結尾,劇情般的推進讓收錄其中的詩作與一位詩人逐漸走向成熟與蛻變的景象形成奇妙回響。
第一輯《生猛的暗夜隨時迫降》,小輯標題來自整部詩集第一首詩《北川的月亮》的第一行詩句。這首寫于2018年5月的詩作里,詩人在震后十年重返災難現場遺址,穿過肅穆群山和連綿羌寨走向垮塌縣城的道路仿佛詩人不斷行入暗夜的道路,溯回重新思考“正是我們從地底掙扎而出,打量自身的塵土與血污”的時刻。那隨時可能迫降的生猛暗夜,如影隨形地籠罩在詩人的車輪之后,也將詩人推向危險境遇而不斷觀照審視自身。
這個“暗夜”究竟是什么呢?是持續逼仄的現實感,是不斷侵擾的“被忘卻的紀念”,是詩人追逐內心審視與詩藝的緊迫感,抑或是以上所有感受的綜合體?在這首詩的最后部分,詩人拋開了那些暗色調的沉重,乘飛碟滑入外天空,落筆于熬湯的嫦娥和繁衍無敵家族的兔子。面對隨時迫降的暗夜,詩人沒有選擇沉淪于痛苦或自閉于無言,而是努力讓語言隨著想象力一同飛升,在古老寓言與現實的碰撞中尋求突破的力量。
這一小輯共收錄詩作32首,是詩人創作于2014年至2018年期間的作品。在詩集自序中,詩人自云:“在這二十年里,我漸漸地清楚了自己的語言質地和聲音特點,明確了在感受、關注和思考時自己猶豫和堅定的方面。”而這一小輯正是在詩人提及的這種“清楚”和“明確”作用下呈現的最新面貌。現實的緊迫感與詩人的想象力互相交織,“暗夜”如影隨形但不能甘于沉淪,在極具鋒芒的語言沖擊下將敘事提升至高處繼而飛升。
詩人近年來偏愛的創作主題是比較清晰的:當下生活的觀察思省(《北京城》《屠霾記》《去年秋天》);戲劇和藝術的給養(《戲劇詩:與科幻有關》《舞者》《約黃茜同觀大衛·霍克尼畫展》);旅行帶來的啟發和觀察(《內蒙古之旅》《中原行》《珀斯小札》);童年鄉土生活的記憶和再認識(《父親的手藝》《收割者》《收聽廣播》);對女性詩人與女性詩歌的關注(《舞者安·薩克斯頓》《致女詩人》《西爾維婭·普拉斯反復做過的夢》);親密關系與日常生活的審視(《交流》《如果真的,在我們之間》《信賴》),等等。
借由這些詩作,我們能夠觸摸到詩人的基本形象和她的精神土壤:童年記憶作為向外出發的起點同時也是不斷回溯的寶貴礦藏,女性詩歌與女性意識奠定詩人的精神基礎能量,戲劇與藝術給予豐富給養,旅行開闊著眼界同時拓展外部審視,對緊切現實與日常的關注則錘煉著詩人的思考能力和語言的銳度。
這一輯中另一較為引人注意的詩作是定稿于2018年的《張三先生的喜劇》。這首組詩顯然是詩人創作于1997年的組詩《張三先生乘坐中巴穿過本城》在時隔21年之后的續編。《張三先生乘坐中巴穿過本城》是詩人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收錄于本書第二輯中。在這首由六小節詩構成的組詩中,詩人刻畫了一位90年代末期較為典型的意氣風發的準中產階級的青年男性形象“張三先生”。讀者跟隨張三先生一同從下午五點出發,“以但丁進入叢林的心情”乘坐中巴橫穿大半個北京城,領略90年代末被蓬勃經濟發展刺激出的躁動浮華的眾生相及城市的喧囂面貌。在這首組詩的最后,詩人寫道,“下一首詩將記載他遭遇靡非斯特”,像是為這首詩未盡的書寫宣告一種延續的可能。
或許是詩人被自己寫下詩句的魔力所影響,又或許是詩人好奇自己創造的人物形象與城市面容究竟將如何變遷,時隔21年后,詩人確實再寫下了“張三先生”遭遇靡非斯特的續篇:《張三先生的喜劇》。在這組詩中,張三先生隨著時代的潮起潮落變成了“人生過半”的中年男人,坐在聚滿了“不自知地表演”人們的餐桌上“擁抱沮喪”,青年時期認為“一切都會有的”的激情已被緊迫的現實逼迫到“退回到內心安靜的角落”。兩首詩之間相隔的二十年,確是這座曾經跑滿中巴的北京城和生活其中人們劇變的二十年,也是整個中國劇變的一個典型縮影。詩人筆下的人物從做著生意憧憬著未來的年輕暴發戶,蛻變為躋身各式高端場合卻目睹種種社會怪現象的中年知識分子。人物的變化曲線與社會的發展不謀而合,張三先生深入叢林般闖蕩世界的小半生終走成了一部嚴肅的喜劇。在這首詩的最末,詩人拋開“張三先生”的囊殼,以代詞“我們”宣告著自己對這部跨越二十年的精神史的最終態度:“但他們封不住我們的記憶/即便以消費日取代,我們仍能夠品嘗苦澀/品嘗苦澀,正是我們新的自我賦權。”一個“張三先生”連綴起詩人二十年間的創作與思想變化,也打通了她持續自我觀察的經脈,令人好奇再二十年后詩人會否續寫這一奇特篇章?
詩集第二小輯《在拼圖游戲中》收錄1997年至2017年間的詩作22首,是從已出版的詩集《松開》《哪吒的另一重生活》中所選,是詩人在過去二十年中的代表作品。如果說第一輯是詩人歷經二十年的自我磨煉后呈現出的最新樣貌,那么這第二輯便是她的“來時之路”。
周瓚作為一位在北京大學度過研究生和博士生涯的詩人,與北大詩人群交流密切,并在畢業后成為當代文學研究學者的詩人,在一段較長的時間里曾被讀者認為是學院派詩人。從選自《松開》書中的半小輯詩作里,確實可以讀到一些學院氣較濃郁的作品,像直接受課業影響而作的《影片精讀》和描寫學院生活的《愛貓祭典,或我們的一年》。
但詩人日后明確的語言風格和精神母題在這一時期已經萌芽,呈現出迥然于他人的獨特面貌,如初步確立詩人女性詩歌追求的《翼》,追溯童年記憶的《童年的死》,風格濃烈頗具記錄時代野心的《張三先生乘坐中巴穿過本城》,以及在旅行中尋求拓寬視野的《在悉尼起伏的道路上》等。
到了《哪吒的另一重生活》時期,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經典形象在詩人的再造下被喚醒,嫁接入當下,賦予古老人物以新的生命力,以這些英雄的形象反向刺激著麻木的現實。譬如有著“火焰的脾氣、海的欲望和必死的命運”的精衛(《精衛》),以及“他是一位詩人,與痛苦、不義、遺忘為敵”的哪吒(《哪吒的另一重生活》)。詩人在喚醒古老想象的詩中探尋的似乎不只是“如果他們生在今時今日會如何”,而更像是“生在今時今日的我們還能否擁有一顆精衛/哪吒之心”的追問。
另一日益明晰的趨向,是詩人對飛速轉變的碎片化時代的記錄與詰問。描述網絡大秀場和粉絲文化的《反肖像》,對全球性災難進行反思的《災難》,刻畫采礦女工生活碎片的《她出現,然后消失》均犀利地指向這一風格。與詩作涉及的內容同步發生微妙反應的,是詩人在這些作品里所使用的語言,既充滿緊張感,更加自信和確定,卻又隨時做好話鋒一轉突襲進入奇想異域的準備。
第三輯《剛剛誕生的一個詞》,收錄詩作14首,是詩人創作于1999年至2013年期間但并未收錄進任何詩集中的遺珠之作。這一輯中的詩作大多較短,這些短詩確實掀開了詩人在已出版詩作中較少流露的一側衣角:它們小巧靈動,語感相對柔和,記敘生活片段,對愛和友情的遐思,四季變遷帶來的隨感。如果說在前兩輯中讀到的詩人如手握甲兵無畏深入冷峻暗夜的斗士,那么這一輯便是詩人卸下裝備后喘息獨坐的片刻拾綴。
通讀整部詩集,不止可窺見一位詩人隨時間而獲得的技藝,更有她在明確自我更新的努力中試圖通過詩句向下接觸實地,向上夠觸星辰的嘗試。詩人以她自己的創作實踐著一種朝向未來的可能性。
(欄目責編:朱鐵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