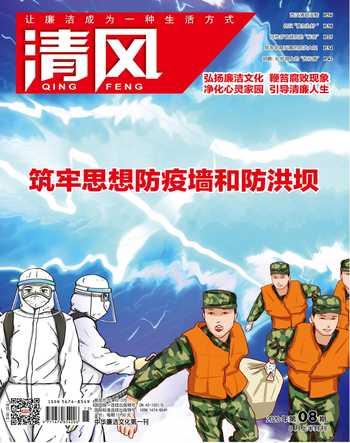北宋“會風”也可攻玉
易國祥
北宋“會風”給筆者留下第一印象的是北宋官員的帽子。那時官帽兩邊有長長的翅翼,據說是“杯酒釋兵權”的宋太祖對文官大臣們也留了個心眼,為防止官員開會時交頭接耳,就讓他們的帽子兩邊長“角”,相互之間不得不保持距離,官員自然無法相互耳語。
照此說法,宋代官帽原來是皇帝從實處著手,整肅會場秩序的一種技術手段。這個辦法若施用到當下維持會場秩序,自然沒有必要。畢竟與會人保持“社交距離”,因為疫情已經成為一種安全性自覺。再說,防止交頭接耳也不是當前會議的主要問題了。
當下與會者的主要問題,除了打瞌睡,多數人的眼力和心思都在手機上。而打瞌睡、玩手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會議繁多冗長、空洞無味、極端無聊。最近媒體報道,一個貧困縣縣委書記和縣長,一個星期要開71場視頻會議。你要他們每個會議都精飽滿、心無旁騖,似乎不可能。在脫貧攻堅和疫情防控雙重壓力之下的今年,基層干部面對開會的苦不堪言,再次在媒體和網絡上噴發出來。
面對這些會風問題,我們可以北宋官員的這頂帽子為向導,走進熱播電視劇《清平樂》里北宋朝堂的朝會,去看看千年前的官場是怎么開會的。
如果你是追劇者,你就不難發現,宋仁宗的朝會上經常吵吵鬧鬧,不同意見者往往上演全武行,會上多有突然襲擊,讓對手猝不及防。碰到這種情況,主持會議的仁宗常常束手無策。會議拖堂成常態,下面的臣子站著打不了瞌睡,倒是坐著的皇帝時有走神。更有甚者,大臣們對皇上當面直諫,無數次讓皇帝下不了臺,收不了場。
這些會場奇觀,比一些西方國家議會打架更富有刺激性,似乎不值得提倡。然而,不論是史料,還是電視劇,從皇上到大臣,雖然對仁宗朝堂開會太長都有抱怨,卻少有發現說那時的會“開多了”的吐糟,也少有“與會人員開會無聊至極”的八卦。
那時的會議固然有很多問題,但筆者發現,他們的會議開得很實在,少有空話大話,多是討論實際問題;少有領導長篇大論“滿堂灌”,多是與會者主動發言,滔滔不絕;那時在會上拖堂的,往往不是會場中的最高領導,而是與會的大臣們。
有一次朝會,司馬光在朝堂批評皇上對公主徽柔嬌寵過度,要求皇上對公主嚴加管束,嚴處公主身邊的內侍。這是司馬光硬塞進會議的一項追加議題,見皇上無意接納,他甚至準備當場死諫。這足以說明,仁宗朝的朝堂會議不是虛開,不是走過場,而是一次次實錘,不錘平釘子不放手。連皇上也躲不過。
當代官員苦會海久矣。會議不僅開得多如牛毛,而且解決會風問題的要求也一波趕著一波。有會議次數的控制,有發言時間的限制,有發言文本的規范。從十八大以來就要竭力攻克文山會海,去年成為“基層減負年”,今年中央繼續下文,持續解決形式主義對基層的干擾。
會風為何久治不愈?依我看,解決會風問題的所有方法,都不如真正砸下開會“實錘法”——每一場會都必須解決實際問題,包括務虛會議也要解決“真問題”,做到“非必要不開會”,開會則允許與會人暢所欲言,對是非對錯做到不明不休,每個單位每年開展評比“無效率最無聊會議”活動,倒逼會議講質量。
相反,把開會當作一種對上表忠的姿態,作為將工作甩責基層的手段,借機立官威顯官味的一個秀場,而幾乎不準備解決任何問題,那會議就很難壓縮下來。你以為把實體會議改成視頻會議就是一種進步?殊不知這只是把不正的會風換了個馬甲,基層官員還是苦不堪言。
筆者無意厚古薄今,只是真的佩服北宋的那些大臣們,他們把會開得使龍椅上的皇上常常下不了臺,開得皇上每次上朝之前忐忑不安。所幸歷史已經證明,這些大臣們并非傲視君權,而是體現了那個時代符合官場倫理的“忠君報國”思想。盡管仁宗不算明君,但仁宗朝政大體還不算太差,那都得益于這些大臣和他們參與的這些朝堂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