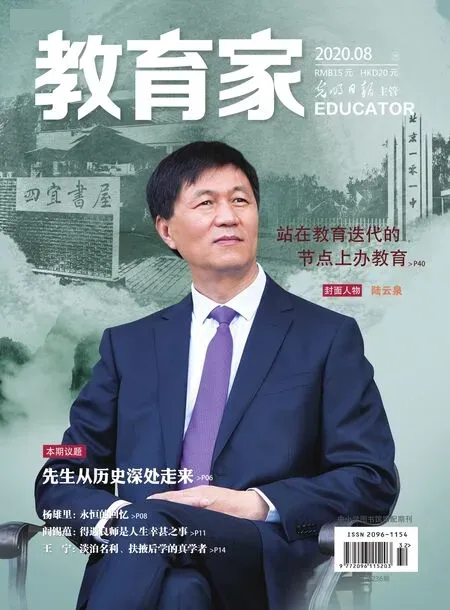悠悠歲月久 清暉時時映心頭
——記高中班主任、語文老師楊克潛及其他先生
嚴寅賢/北京市語文學科特級教師,北京一零一中原副校長
高度發達的現代通訊,常讓人驚喜連連。2020年7月,經在京老鄉熱心相助,我和當年高中班主任、語文老師,已81歲高齡的楊克潛老先生取得了聯系。彈指間,48年過去了!激動之情自不待言。當天我就和先生加了微信,晚上就用夾雜著南腔北調的鄉音和先生視頻通話。先生面色紅潤,說話中氣十足,氣度不減當年,完全不像年已八旬的老人。
悠悠歲月久,先生清暉,時時映心頭。
48年來,從未和先生取得聯系。雖平素多方打聽,終未如愿。又加上“文革”特殊時期,師生關系相當松散,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所以,對先生個人情況完全停留在那個年代的簡單與模糊。
與先生通話之后,才對先生有了前所未有的了解,并油然增添十二分敬意。先生告訴我,他1965年畢業于南京師院(今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之后,便被分配到我的高中母校——江蘇省泰興縣南新(公社)車馬莊中學任教。母校建于1956年,原是初中校,“文革”期間成為完全中學,直屬縣教育局管理。盡管地處農村(離我家三華里),但校園規劃合理,校舍和家鄉民居一樣,清一色青磚青瓦平房,校園里樹木參天,綠草如茵。基礎設施很不錯,圖書館、實驗室一應俱全。但2017年“五一”我回老家專程去母校時,才發現母校被宗教人士買斷,改建成禪院了。但學校格局和校舍依舊,我在當年教室廊前徘徊良久,拍照留念,感慨萬千。
先生說,我們畢業不久,他就出任母校校長并一直堅持上課。后來,在張灣中學、分界職業中學任校長,并一直擔任高中語文老師。再后來,調縣教育局職教中心,負責全縣職教系統語文教學研究工作,直至退休。這讓我大為驚訝。一是記憶中的先生當年的才情才氣得到印證;二是感慨家鄉教育之發達。在20世紀60年代那樣一個經濟文化教育全面貧困的年代,南京師院本科生竟然到農村中學任教,讓人驚嘆。當然,先生當年從未向我們提及這些。也許先生曉得,在那樣一個文化荒漠時代,我們壓根兒就不懂什么叫“中文系”,遑論“大學本科”。
更讓我想不到的是,先生通過微信連發幾幅他的書法大作照片賜我。雖是照片,但仍鮮明感受到作品氣韻撲面而來:筆法蒼勁,筆鋒峻峭,似有橫掃千軍之勢;骨力外顯,功夫內隱,不輸專業書家風范。我立刻向先生提出不情之請。我告訴先生,近30年前,我曾在《杏壇讀書絮語》一文結尾寫四句話以表心志:讀書教書寫書,育德啟智鑄魂。淡泊寧靜致遠,吾輩永世無憾。時至今日,頌之念之,內心仍澎湃不已。我對先生說,請理解弟子之心,若獲恩賜,不勝榮幸。

楊克潛生于1940年4月,江蘇泰興人。1965年畢業于南京師范學院。1965年8月-1993年8月在泰興市車馬莊中學、張灣中學、分界職業中學任校長,并一直擔任高中語文老師。1993年9月-2000年10月在泰興市教育局職教研究中心工作。2000年10月退休。

先生極為爽快。第二天清晨,書就,拍照,發我。
字如其人。仔細端詳先生風骨不減當年之墨寶,先生往昔才華橫溢、灑脫俊逸的形象瞬間從記憶深處騰躍而出。
先生多才多藝。他不但教我們語文,還給我們上音樂課。當年的感覺是:他高亢脆亮、極富感染力的男高音,與當時的專業男高音有一拼。每次音樂課后,教室里余音繞梁,縷縷不絕。
先生書法功夫深。但當年只是覺得他的粉筆字蒼勁有力,全然不知其軟筆功力。印象最深、至今還時常給同事朋友津津樂道的是,一次,先生教我們唱《毛主席走遍祖國大地》這首時代歌曲。上課鈴一響,先生就走進教室,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下“通欄標題”——“毛主席走遍祖國大地”。先生板書時的翩翩風度,板書過程中的愔愔氣場,先生那龍蛇飛舞、鸞翔鳳翥的粉筆字,永鐫心底,不可磨滅。
自己做老師近40年,雖才學終身不能望先生項背,但時至今日,語文課上拒絕PPT,習慣“人工板書”,當是先生之風影響了我。長期教高中,因板書量大,課時緊,總是習慣于“嚴氏狂草”。最近幾年教初中,童真少年接受不了。于是,無論是板書還是作業批語,我改“狂”歸“正”,歸“楷”,贏得少年喜愛,有孩童竟模而仿之。
先生是那個時代的語文名師,更是明師,故善為人師。他時常用“鋼板”刻印他親自選中的短小精練、意蘊豐厚的文言文讓我們閱讀。印象最深的是先生教我們《葉公好龍》。先生教學極風趣,當講到“天龍聞而下之,窺頭于牖,施尾于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時,先生竟模狀擬聲,惟妙惟肖,令全班同學捧腹。而當先生告訴我們“葉”不讀yè,而讀sè(家鄉方言,本讀shè)時,語文常識極度貧乏的我們這些懵懂年少大惑不解、一頭霧水:活生生好端端一個“葉”,為什么要讀“色”?但“葉公好龍”的典故和意蘊讓我們眼界大開并對先生景仰有加。
先生的語文拓展閱讀真切地引領了我的職業生涯。一輩子教語文,一輩子引領學生課外閱讀。1972年高中畢業,1981年當老師。十個年頭,先生或許未曾想到,“長大后我也成了你”。從80年代初開始,我也和先生一樣“刻鋼板”,刻《論語》,刻《孟子》,刻其他名言警句、短小文章。后來,引領學生從單篇文章讀到整本書,多讀書,讀好書,持之以恒,樂此不疲。先生或許更未想到,其不才弟子一路“招搖撞騙”“掛羊頭賣狗肉”,竟也混成了所謂“磚家”。
先生關于怎樣學語文的教誨讓我的職業生涯明鑒萬里。就在寫此文時,我饒有興趣地重新翻閱當年的兩本語文書,竟有諸多驚喜和“新發現”。課文每一頁幾乎都留下一行行幼稚而凌亂的涂鴉:圈點批注;段落大意;在先生要求背誦課文旁寫下的“背誦”二字(當年課本無背誦要求);隨文詞語解釋;讀書名句摘抄等。我驚喜地發現,在語文第一冊最后一頁,竟抄錄《林海雪原》“天上的星星俯首如泣,林間的樹木垂頭致哀”的句子。這兩句在書中哪里出現,自己什么時候抄的,早已全然忘卻。但在那時候,當年的我,認定這就是世上最美的語言!
并且,它似乎成了我一生追求美的語言的精神動力!
“不動筆墨不看書”,“好記性不如爛筆頭”;下功夫背書等,都是先生當年的諄諄教誨。幾十年來,我一直也是這樣要求我的學生的。而我從年輕時就喜歡圈圈點點、寫寫畫畫的讀書習慣,當也是受了先生的教導。
翻閱舊課本另一驚喜,第三冊第18、19頁,竟有我同時工整寫下的“楊克潛老師”五個字。書寫背景早已忘卻。但毫無疑問,它是我對先生充滿敬意的“歷史見證”。
克潛先生為師兩年,卻影響我一生。歲月悠悠,先生清暉,時時映心頭。
高中階段,還有幾位先生留在記憶深處。一是老校長蔣文質,當年已經年近六旬。現在想來,他一定是一位學富五車之鄉賢。上學時只和他打過一次交道。記憶中當年有一份家庭材料需他簽字。我怯生生走進校長辦公室,只見他拿起毛筆,在材料上大筆一揮,“同意”二字和他的尊姓大名、簽署日期瞬間落定。當年不諳書法,但老校長的寶楷和書寫風姿讓我過目不忘。對老校長最生動的記憶是,每天課間操,他都會在操場最前面和我們一起做。老校長五短身材,微胖;做操動作不太協調,微拙。每當此時,我們一幫男生總在他身后竊笑不已,有時甚至還搞一點模仿其動作的惡作劇。蔣校長無兒無女,一生以校為家。蔣校長1985年離世,縣政府舉行追悼會,分管縣領導致悼詞。
我的數學老師鄧余欣,早年畢業于揚州師范學院(1992年與其他院校聯合組建揚州大學),1962年師范解散,他被派往我們學校。我天生愚鈍,數學成績差。但十分佩服鄧先生的講課風格和水平,他的教學能力在歷屆學生中有口皆碑,在京城,我至少遇到兩位曾是鄧先生弟子的同鄉。80年代中期,先生曾被評為全國優秀教師。楊、鄧兩位先生我是同時取得聯系的。前不久電話問候并致敬先生。但因先生貴體有恙,且據楊先生說,他們二人同庚,80高齡。雖只是短暫通話,但我明顯感到和先生交流已經很是困難了!
鄧先生是無錫人,戴眼鏡,一派書生氣。年輕時帥氣干練,籃球打得相當好。如今,當年英姿,想必難尋!
歲月悠悠,先生清暉,時時映心頭。
愿鄧先生健康長壽晚年安度!
印象中,化學肖先生說話幽默,但也不失尖刻。記得高一時,我同桌不知因為何事惹得肖先生大為光火。一氣之下,同桌冒出一句:“我不上了!”沒想到肖先生慢條斯理:“可以。你走了,我們教室的空氣也會新鮮很多。”搞得同桌尷尬異常。我為人師之后,也曾多次和同事朋友憶及此事。對化學老師至今不能忘記的,還有那個年代難得的健康常識提醒:咳嗽遇痰,必及時吐之;若下咽,則傷肺。
回憶自己近半個世紀前的高中生活,感受最深者有三。
一是社會性優質教育環境至關重要。我當年有幸享受了優質師資教育,但整體教育環境全方位沙化。我所遇見的良師,充其量是當年教育荒原上的幾棵參天大樹,他們只能給有限的生命灑下綠蔭,制造陰涼。
優質教育,一定是優質師資和優質環境的有機融合,缺一不可。
二是做老師是否名師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明師。明明白白做老師,一如吾之恩師楊公克潛、鄧公余欣諸先生。
三是一名真正的教師,其氣場與氣度、才情與學識具有遙遠而強勁的時空穿透力。坦率講,在我們那個特殊年代,幾乎完全沒有今日教師的耳提面命、苦口婆心,更沒有今天精致的個性化、針對性教育,充其量只是教師的“泛性傳道”,是一種高度粗放型教育。但他們對我們產生了縱貫一生的生命印記,我們對他們產生了超越時空的思慕景仰,這不能不發人深思。
值此難得機會,衷心祝愿克潛、余欣二位先生,祝愿健在的我的所有先生和天下為人師者健康幸福到永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