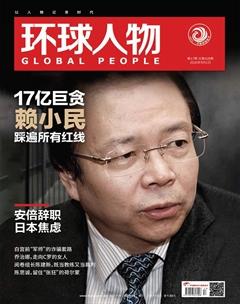莫言把“莫言”寫進小說
陳娟
高粱初紅,作家莫言回到高密東北鄉。眼前是一派熱鬧景象,電視劇《黃玉米》的拍攝地成了旅游熱點,車輛排大隊,游人擠成堆。他家那5間破房子,搖搖欲墜,門口卻掛上了牌子,每天都有人來參觀,包括外國游客。這讓他覺得有點兒不可思議,但很快就接受了——一切變化都發生在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
老鄰居蔣二比莫言更早融入這變化。他先在莫言舊居旁擺攤賣書,兼銷當地土特產,之后低價買下舊居西邊的洼地,在上面蓋了5間屋,又在老屋與新屋間搭起一個大棚,設下幾十個攤位,出租給買賣人,新屋則租給一位來自青島的作家,每年租金數萬。早些年,蔣二腦子出了點兒問題,村里人都拿他當傻子看,如今卻走在發家致富的前列。每次莫言回來,他都要設宴款待,在酒桌上,蔣二吐真言,說:“我們蔣家人有個特點,那就是:晚熟!當別人聰明伶俐時,我們又傻又呆;當別人心機用盡,漸入頹境時,我們恰好靈魂開竅……”
這是莫言中篇小說《晚熟的人》中的一段故事,寫于2020年。小說中的“我”是一個叫“莫言”的作家,他獲獎還鄉,回憶和兒時伙伴之間發生的那些事。不久前,同名小說集《晚熟的人》面世,莫言和好友畢飛宇、李敬澤一起直播對談,當晚吸引150萬人圍觀,還上了熱搜。自獲獎后,有關“諾獎魔咒”的說法就始終環繞著莫言,而《晚熟的人》的出現,多多少少算是對這一質疑的回應。
小說集中共有12個故事,除《天下太平》外,莫言都把自己寫進小說,參與到故事的進程之中。而且他借用的正是自己當下的年齡和身份,比如《晚熟的人》里講到獲獎后鄉人的反應,提到有人假冒莫言書法騙錢,蔣二口無遮攔:“我哥的字無論多么丑,那上面也有我哥的氣息,那就像臭豆腐,無論多么臭,那也有人喜歡。”
“諾獎事件使我作家的身份添加了一種更加復雜的色彩。在當今商業、網絡社會里,這樣一種身份的人回鄉,所遇到的人和事,比過去豐富得多了。”莫言說,他與小說中的“莫言”互相對視,“這種關系就像是,孫悟空拔下一根毫毛,變出了另一只猴子”。
在《詩人金希普》中,金希普是個文痞,一邊寫著“大饅頭大饅頭/潔白的大饅頭/芬芳的大饅頭”的詩,一邊拉大旗作虎皮四處招搖撞騙;在《紅唇綠嘴》里,主角是一個外號“高參”的鄉村婦女覃桂英,手下有上百個鐵桿水軍,嫻熟地進行網絡操作,不斷制造事端,并從中漁利;《火把與口哨》寫的則是三嬸,丈夫死于礦難,兒子被狼吃掉,女兒喝農藥自殺,在多難的命運面前,她制定復仇計劃,殺死一窩狼,之后決絕地死去……他看到的一個個人物,經歷的一個個故事,看似不相干,卻共同構成了一幅當下中國鄉村圖景。
“在老莫言之外跑出一個新莫言。”畢飛宇在讀完《晚熟的人》之后如是說。至于莫言本人,他身處變化之中——時代在變,周遭的人在變,故事在變,同時也感受著自己的變化。他不希望過早成熟、定型,想做一個“晚熟的人”,“不斷超越自己,讓自己的藝術生命更長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