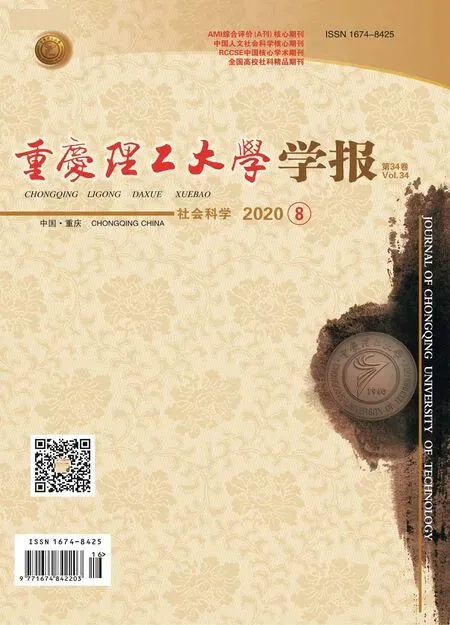基于知識共享的供應鏈協同創新利潤分配研究
張悟移,孫雪蓮,向海林
(昆明理工大學 管理與經濟學院, 云南 昆明 650093)
一、引言
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知識共享已成為創新的重要因素。張旭梅等提出企業間的知識共享強調各成員企業都要專注于提供自身獨特的知識資源,通過成員企業間的知識流動獲取知識或通過這些知識有機組合創造出新知識,促進企業間的交互學習,真正實現企業間的協同創新[1]。在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有限的情況下,企業從外部企業獲取知識是企業增長知識和創造知識的有利保障。通過資源和要素的有效匯聚,突破創新主體間的壁壘,充分釋放企業彼此間的創新要素活力而實現合作,企業間的知識共享對單個企業的協同創新起著重要的促進作用,通過知識共享可以真正實現企業間的協同創新,而協同創新的最終目的是提高成員企業的利益,并獲得競爭優勢。
供應鏈是圍繞核心企業,通過對信息流、資金流、物流的控制,從采購原材料開始,制成中間產品以及最終產品,最后由銷售網絡將產品送到消費者手中的將供應商、制造商、分銷商、零售商直到最終用戶連成的一個整體功能網鏈結構[2]。供應鏈是由許多節點企業組成的供需網絡,供應鏈上的節點企業進行知識共享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潤最大化,以發揮最大的競爭優勢。在供應鏈上進行知識共享能使流動在不同企業間的知識流迅速增加,還能整合不同企業的資源與能力,使得供應鏈企業進行知識共享時更加深刻地考慮協同創新的作用,由此表明供應鏈企業間的競爭更加傾向于知識能力的競爭。
企業間基于知識共享的協同創新效益日益突出,在此進行合理的利潤分配機制探討,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供應鏈上各節點企業合作的積極性,并為供應鏈節點企業維持合作伙伴關系提供重要的保障。供應鏈企業之間的知識共享對于企業獲得競爭優勢至關重要,科學合理地制定相關的利潤分配策略對提升供應鏈企業間的績效和公平感有著重要的意義與現實必要性。本文的創新點是把供應鏈企業間知識共享這種外部獲取知識的手段作為企業進行協同創新的突破點,從知識共享的角度建立三級供應鏈的協同創新模型。現階段關于知識共享的研究集中于對知識共享的影響因素、知識共享機制的探討,本文在三級供應鏈進行知識共享的基礎上,研究供應鏈三方利潤分配最為合適的分配系數。
二、相關理論研究
(一)國外研究現狀
在企業進行協同創新的過程中,有著高層次知識水平的企業往往會具有高的創新能力。Kim提出制造商通過向供應商提供創新的補貼,可以使得供應商加大零部件的創新開發力度,降低原材料的成本[3]。Fawcett等提出供應鏈成員企業間的知識可以進行互補,并且好的互信可以使得供應鏈更好地幫助制造商實現突破式的產品創新[4]。Liao等認為在供應鏈環境下,轉化來自不同知識環境的知識對企業間的協同創新起著關鍵的作用[5]。
供應鏈治理問題研究的兩個視角,一是契約理論中交易成本的理論視角,強調用正式的契約治理來防范機會主義行為,化解沖突;二是關系交換視角[6-7],關系交換視角是限制交易伙伴可接受行為規范來對組織間的交換進行調節。Weng對一個制造商和一個銷售商之間的協調訂購問題進行了相關研究[8]。Samuel等研究了農業種子供應鏈中的協調問題,分析了各種情況下的合作協調契約[9]。有關以上兩個視角的研究,基本上給出了供應鏈上的治理方法,但是供應鏈上治理的手段遠不止用契約或者規范來約束,在供應鏈企業之間存在不少的協同創新行為。
現階段關于供應鏈知識共享的研究集中于企業協同創新的創新手段和企業創新效益方面。Changfeng等基于知識管理和創新能力理論,旨在通過研究影響供應鏈網絡中企業創新績效的關鍵因素之間的復雜關系,揭示協作創新過程的機制,其中對中國236家公司的調查結果發現,協作創新活動、知識共享、協作創新能力和企業創新績效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10]。Qiankun等提出一種基于監督機制的知識共享激勵方法,以促進會員企業間的知識共享,引入監督獎勵提高了知識共享所產生的努力水平和預期收益,但減少了工業建筑供應鏈中成員企業已確認的平等收益。在知識共享產出的估計中,不考慮顯性知識,也未考慮監督成本。研究結果表明,會員企業應注重知識共享的成本,以獲得更多的利益[11]。
(二)國內研究現狀
國內的學者大都是從模型、策略等角度進行供應鏈上知識共享的研究。張巍等比較分析了創新和不創新兩種模式下的收益情況,研究表明供應鏈三方只有進行協同創新時才能得到最優的協調效果[12]。覃艷華等通過建立供應鏈上一個上游企業和N個下游節點的模型,分析企業間的知識共享和合作創新行為[13]。吳成鋒等分析了知識共享和知識創新的基本內容,構建了基于知識共享和知識創新提升供應鏈核心競爭力的內在演化機理[14]。杜欣等提出核心企業與配套企業的協同創新博弈模型,并得出協同創新比單獨創新對市場更有利的結論,同時提出協同創新能令產品的市場銷量和兩個企業的整體利潤更高,但無法保證每個企業都能獲得創新帶來的增益[15]。
在研究供應鏈利潤分配問題的文獻中,大多學者從農產品供應鏈出發,從不同的角度探究了合理的利潤分配策略,為供應鏈利潤分配相關的研究奠定了基礎。馬士華等利用Shapley值模型研究了農產品供應鏈合作博弈模型的利潤分配[16]。趙曉飛等研究了基于修正Shapley值法的農產品供應鏈聯盟利益分配策略[17]。張巍等研究了由單一供應商、制造商和銷售商組成的三級供應鏈在三方非協同創新、三方協同創新情形下的供應鏈總收益、創新投入以及產品產量的情況,并分析了縱向溢出效應、創新系數的大小對供應鏈總收益、創新投入以及產品產量的影響[18]。劉納新等從供應鏈上各節點企業之間隱形知識共享的角度,建立了供應鏈各節點企業之間的利潤分配靜態博弈模型[19]。李軍等總結了用Shapley值解決供應鏈協同創新利潤分配問題相關研究的3個層次,并提出考慮創新資源投入、創新創造收益和創新承擔風險3個因素的Shapley值利潤分配模型[20]。周業付針對農產品供應鏈利潤分配不均的現象,綜合考慮了風險、合作意愿與質量投入等因素,基于改進Shapley值模型研究了農產品供應鏈的利潤分配機制[21]。胡湘云等提出采用修正的Shapley值模型,研究了中小企業供應鏈協同創新收益分配[22]。滕鄭等提出了從智慧整合投入、智慧整合收益、綜合風險因子出發改進的Shapley值模型,有利于研究農產品智慧供應鏈利潤分配[23]。
現階段,供應鏈企業間的知識共享研究集中于在特定環境下,例如沈娜利等在大數據環境下,對供應鏈企業間客戶知識共享的股權激勵機制進行了模型建立,研究得出從制造商角度設計預期承諾契約——股權激勵機制促使零售商提高客戶知識共享的努力水平[24]。此處強調了關于供應鏈上客戶知識共享的重要性,為之后類似的研究提供了研究方向。胡健等提出個體隱形知識共享行為在虛擬社區中發生與原始知識共享行為共享方式不同的共享過程,研究得出社區中的個體隱形知識共享水平會在虛擬社區知識共享氛圍、知識個體共享意愿和社區技術環境的作用下成倍增長[25]。莊彩云等通過構造一個核心企業和n個從屬企業組成的創新網絡在協同知識創造過程中知識投入決策的stackelberg博弈模型,引入知識內溢系數等變量,研究了系統成員之間的知識投入決策和知識產出分配問題[26]。段萬春等利用ANP方法,提出從組織知識共享整體協同度方面整合優化組織協同知識共享系統作用的決策方法[27]。
以上有關利潤分配的研究中,大多是運用修正Shapley值模型的利潤分配系數進行的,而本文從基于知識共享的協同創新模型入手,借助非協同創新時的利潤分配系數,以此為基礎,確定在協同創新條件下的利潤分配系數的范圍,為供應鏈上各節點企業進行合理的利益分配提出可供參考的建議。
本文從傳統單一供應商、單一制造商和單一銷售商組成的三級供應鏈角度,分析在采用非協同創新獨立決策和基于知識共享的協同創新集體決策情形下,供應鏈上三方總體利潤、知識共享成本、產品訂購量的情況,并分析知識共享成本系數的大小對知識共享產出效率的影響。在此基礎上研究供應鏈三方利潤分配系數的大小問題,進一步為供應鏈上合作企業探討出合作共贏的利潤分配機制,為企業進行合理的決策提供參考。
三、模型描述

四、 模型建立
(一)非協同創新供應鏈獨立決策模型
假設供應商向制造商供應制造產品的零部件,制造商向銷售商供應產成品,銷售商再將產品銷售給顧客。根據產品需求規律,設銷售價格P3和產品的訂貨量q的關系如下:P3=a-bq(a>0,b>0)。在供應鏈上的企業進行非協同創新時,企業間不進行任何的知識共享。
設在完全信息條件下供應商、制造商和銷售商進行動態博弈,在動態博弈中由于各博弈方的行動先后會導致利益不對稱,對博弈方的行動選擇和結果都會產生影響。根據貨物流動的順序,先確定P1,再確定P2,最后確定q。在使得供應鏈整體利潤最大化的前提下,根據博弈的逆向歸納法求相應的解。
假設供應商的利潤函數為π1=(P1-c1)q
(1)
制造商的利潤函數為π2=(P2-P1-c2)q
(2)
銷售商的利潤函數為π3=(P3-P2-c3)q
(3)
根據博弈的逆向歸納法進行以下求解:
第三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

(4)

(5)
(6)
(二)基于知識共享的協同創新供應鏈集體決策模型

(7)
(8)
(9)
(10)
供應鏈上三方企業考慮從總收益最大化的角度來選擇x′、y′、q′,
(11)
(三)模型分析
1.非協同創新和協同創新總體利潤、總訂購量的比較
結論一:在供應商、制造商和銷售商三方協同創新時,供應鏈上的總體利潤大于非協同創新的總體利潤。原因是在進行知識共享的協同創新時,供應鏈上的企業本著三方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來思考,銷售商根據客戶需求向制造商提出采購申請,制造商利用本身的核心優勢為供應商提供產品設計要求,供應商充分利用制造商的設計理念進行零部件的研發,因此供應鏈上所需零部件供應量、產成品生產量是最合適的。
2.創新系數對知識共享成本、訂購量和總利潤的影響
結論二:在供應商、制造商和銷售商三方協同創新時,供應鏈上的成本系數越大,供應鏈上三方的知識共享成本越少、產品訂購量越少,并且供應鏈的總利潤值越少。原因是通過知識共享進行協同創新時,隨著知識共享成本系數增大,創新效果會隨知識共享成本系數一直增大而降低,供應鏈上的訂購量會遞減,總利潤值也會隨著創新效果降低而減少。
五、利潤分配系數大小研究
(一)非協同創新的供應鏈利潤分配系數大小

制造商給予銷售商的批發價格為:
P2=P1+c2+Φ
(12)
銷售商的利潤是:

(13)
用式(13)對P3求導,得到最優銷售價格
(14)
從而結合需求函數P3=a-bq,得到最優銷售量:

(15)
此時的制造商利潤為:
(16)
供應商的利潤為:
(17)
因此得到供應商給制造商的價格為:
P1=2[a+c1-(c2+c3+Φ)]
(18)
結合式(16)和式(18)得到制造商最優利潤
Φ=2[a-(c1+c2+c3)]
(19)

(二)基于知識共享協同創新的利潤分配系數大小
傳統的Shapley值法僅僅把成員企業對系統或者整個聯盟體的貢獻率作為分配的唯一依據,而忽略了影響利潤分配的其他方面。當然,進行協同創新時,供應鏈上各個企業的利潤分配應該主要考慮投資成本大小、貢獻率大小、風險因子大小等。到目前為止,基于修正Shapley值法進行利潤分配研究的學者居多。相較傳統的Shapley值法,修正Shapley值法已經極大地減少了對影響利潤分配因素考慮不周而導致的結果不準確現象。此處不作論述。
現就知識共享的協同創新模型,本文利用供應鏈上三方已經進行知識共享的前提下,對三級供應鏈企業間的利潤分配進行如下假設。
假設一:在三級供應鏈中,制造企業是核心企業,供應鏈上游的供應商是在核心企業制造商的推動下進行零部件協同創新的。銷售商在核心企業制造商的帶動下,銷售商為供應鏈上游企業提供客戶知識相關的資料,《大數據環境下供應鏈企業間客戶知識共享股權激勵機制研究》一文對客戶知識的重要性給出了相應的論述[24]。
假設二:假設供應鏈之間通過緊密合作進行了基于知識共享的協同創新,使得供應鏈上總體利潤最大化,則各企業的利潤分配會成一定比例。設供應商、制造商和銷售商的利潤分配系數分別為:λ1,λ2,1-λ1-λ2,對分配系數的大小進行以下研究。

六、結語
通過建立三級供應鏈模型,對供應鏈上三方在非協同創新和協同創新時的總訂購量、總體利潤以及基于知識共享的協同創新時知識共享成本系數大小對供應鏈上的知識共享成本、訂購量和總體利潤的影響進行比較分析。分析表明,進行協同創新時的供應鏈上訂購量和總利潤值更大,并且隨著知識共享成本系數的減小,協同創新的知識產出效率會增強,供應鏈上知識共享成本、訂購量和三方總利潤會增大。并在此基礎上分析了合理的利潤分配系數大小,在供應鏈三方進行非協同創新的情況下,基于三方利潤之比為1∶4∶2的理想狀況,確定基于知識共享的協同創新三方企業利潤分配系數的范圍,得出供應鏈上三方企業合理的利潤分配。
在供應鏈進行知識共享的基礎上,探討供應鏈上三方企業合理的利潤分配系數大小。假設供應鏈上制造商為核心企業,并為供應商和銷售商進行知識共享協同創新的倡導者。通過供應鏈上核心企業進行利潤協調來提高企業間合作的積極性,以此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鼓勵三方企業積極參與到供應鏈上的知識共享中來。結合上述分析,從利潤分配的角度為供應鏈企業間進行基于知識共享的協同創新提出建議:建立供應鏈三方合理的利潤分配機制,須從契約、合同的角度出發,建立有利于供應鏈三方企業進行基于知識共享的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利潤分配機制。在此基礎上,保證各企業在采取知識共享相關措施之后,利潤相比之前進行非協同創新時有一定提高,并且做到“誰主導,誰負責”的原則,使得核心企業不僅成為基于知識共享協同創新活動的發起者,也成為保證利益合理分配的實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