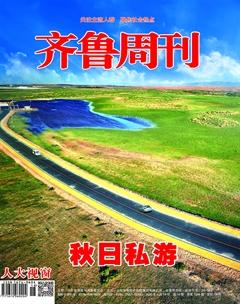浮來山:尋根莒文化
七年后,我再次來見它,它依舊枝繁葉茂,慈眉善目,我已歷盡滄桑,不復少年光景。
四千年,七年,無法對等的時間,在這片低緩的丘陵上對接。嶙峋遒勁的枝干,托舉出古老銀杏樹的蒼茫歲月。
浮來山,海拔只有三百米,但山不在高,丘壑在胸中。小山丘上,有大文明。浮來山上,作為老祖的銀杏樹,見證了東夷文化的繁衍生息,見證了古老民族對太陽的崇拜。
兩次文化之旅,專為“莒”而來。
一
那時,它正年輕。

綠樹掩映中的定林寺,收藏著文壇巨匠劉勰的身世之謎。
以近四千歲的年齡而論,一千余歲時,可看做正值壯年。彼時,蒼勁的枝干亦如現在般挺立,樹蔭遮蔽了周邊大部分天空。一個秋天,銀杏樹葉金黃燦爛,掛滿枝頭,只需一陣微風將其掃落,樹下人聲喧嘩,一場影響歷史進程的會議正在召開。
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記載:“莒雖小國,東夷之雄者也,其為患不減于荊(楚)、吳。”在東夷諸國中,莒國面積不如萊國,但其軍力雄厚,論起對外征伐,當屬第一。自西周后期開始,莒不斷對外攻伐,滅掉向國、鄫國,并長期騷擾魯國,《左傳》中記載過許多次莒國襲擾魯國邊境,魯國無奈,向晉國求助。
《左傳》載,襄公二十三年,齊侯襲莒,“傷股而退”,再戰,莒君親鼓而伐之,殺齊大夫札梁。昭公二十二年,“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君“擊敗齊師”。在與齊魯兩大國的對抗中,莒國屢屢秀肌肉,展示出東夷強國的實力。
陳為楚所侵,請齊魯莒相助。在當時,華夷之間還是有很大界限的,陳為華,莒為夷,莒國以強大的實力,證明了自己的存在。
另一次證明存在的,就是發生在浮來山的魯莒會盟。
兩國長期不合,相互攻伐,各有損傷。作為華夏最正統的魯國,自然不把莒國放在眼里,莒國便用實力,用戰場上的對決,把魯國一步步拉到談判桌上來。
兩個敵對的國家最終走到一起,中間人很重要。這時候,熱心的紀侯出現了——2012年,沂水縣紀王崮崮頂發現了春秋時期國君級別的墓葬,一時之間,歷史煙塵中的紀國再次廣受關注。
紀侯先是找到莒子,進行了一次會盟,調和莒魯兩國關系。莒紀會盟后,紀侯又赴魯做說服工作,經多次斡旋,魯公終于同意到莒地會盟。
公元前715年農歷9月26日,魯隱公與莒子在浮來山會盟。銀杏樹下,兩個“國家領導人”冰釋前嫌,握手言和。這次會盟,也將作為東夷之國的莒國拉到了魯國的行列,華夷界限逐漸模糊。
莒人變得溫和了,莒地成為許多流亡者的避難地,大有世外桃源之感,也說明莒國有實力保證流亡者的安全。流亡者中,有譚子、魯公子慶父、齊高無咎、齊王何、齊工僂灑。這其中,最著名的是齊公子小白,也就是后來的齊桓公,莒國為他提供了積蓄能量的舞臺,回到齊國后,他最終成為一代霸主,并留下“勿忘在莒”的成語。
莒國后來為楚國所滅。后疑似復國,又為齊所滅。齊人以莒為“五都”之一。公元前284年,燕將樂毅聯合五國攻齊,占領齊國大部,田單輔佐齊襄王憑借莒、即墨二城復國。
莒,最終成為一個地理名詞,并專用于地名,沒有延伸出別的含義。山東號稱“齊魯”,并不恰切,應為“齊魯莒”。
銀杏樹,作為莒地的活化石,見證其文明史,足以彪炳史冊。
二
一年年草木凋零,銀杏樹下變得冷清,直到周圍建起庭院,一座寺廟把樹囊括其中。從此,青燈佛號成為樹的另一張面孔,孤寂,卻又懷抱千年佛法,顯得神秘又睿智。
寺是定林寺,建于晉代,距離魯莒會盟又過去了近千年。
一位叫慧地的僧人,仿佛身側的銀杏樹般,洞徹生死,睿智的目光穿透樹蔭,直達藝術的殿堂。
僧人的俗名叫劉勰,祖籍莒縣,世代僑居京口。劉勰少時家貧,篤志好學,依靠名僧僧祐,到他住持的位于建康郊外鐘山上的定林寺里幫忙整理佛教經典。
三十二歲,劉勰開始寫作《文心雕龍》,歷時五年,中國第一部集大成的文學專著悄然而成,共十卷,五十篇,縱論天下文章。“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多少偉大著作是在作者寂寂無名之時,憑一腔熱血而寫就?后世的杜甫、蒲松齡、曹雪芹當向劉勰致敬。
文學的魔力何其玄妙,《詩經》和《離騷》,一出手即是高峰。理論的概念剛剛萌芽,《文心雕龍》又樹了一座豐碑。后世越千年,依舊一覽眾山小。
《文心雕龍》得到宰相沈約稱贊,授奉朝請,劉勰自此入仕,歷任臨川王記室、步兵校尉、太子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蕭統去世,傷悲欲絕,請求出家,沒有得到梁武帝許可。他燒發明志,法號慧地,出家并圓寂于定林寺。
一個一生與佛親近的人,一個因知己隕落而內心寂滅的人,一個通曉文學來處與去處的人,一座豐碑。
“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流淌在《文心雕龍》里的詞句,何止于文學理論?那是一種通透了人生的體悟,是生命和自然的融合。
定林寺,歷史記載中有好幾處,南京有上定林寺和下定林寺,京口也有定林寺,浮來山上的定林寺仿佛一個最終的宿命。歷史記載,劉勰出家后不久去世,又有后世考證,并非如此,他又活了至少五年。最終,他潛回故里,重建定林寺,守著古老的銀杏樹直至去世。他的一生有種難以言說的緣分:始于定林寺,終于定林寺。
定林寺內,郭沫若手書的“校經樓”幾個大字,攜帶著劉勰的身世之謎,靜靜守著這片山水。
銀杏樹,作為自然的精神之魂,護佑著莒地;劉勰,作為人文思想的精神之魂,和銀杏樹形成對照。
樹下,依舊是那個孤寂的身影,來來去去,提筆著文章,落筆觀滄海。
三
《說文》曰:“夷,東方之人也。”
《后漢書·東夷列傳》曰:“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
在莒州博物館,透過玻璃罩,一個身穿金縷玉衣的東夷人吸引了我的注意。他從一堆陶器里抬起頭來,皮肉飽滿,鎧甲锃亮,矛和戟的武器充滿光澤。
仿佛,這個遠古的東夷人,正在用石塊書寫我的過去,交談從我們對視的眼里源源流出。古老的東夷文化,攜帶著太陽文明的光輝撲面而來。
除了戰爭,還有對日月的崇拜,對命運新的注解。仿佛回到東夷的城邦,駕一輪戰車,長驅在綿延至海濱的丘陵上,那些出土的蛋殼陶、古酒樽、蒸餾陶器,那些畫像石上的故事分明灌輸了當代的意義。
夷,一個帶有貶義的稱謂。但東夷最早融入華夏,亦成為華夏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東夷文化中熠熠生輝的莒文化,同樣極具魅力。

浮來山上的千年銀杏樹,是莒文化的活化石。吳永強/圖
七年前,我在銀杏樹下,陪它坐了一會兒;七年后,又是一個夏天,我再次坐在同樣的位置,和它說話。它見證的歷史正在我眼前浮現,戰爭、攻伐、孤寂、文學,分別占領不同的枝葉,籠罩在我的天空。
而我,也成為它的歷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