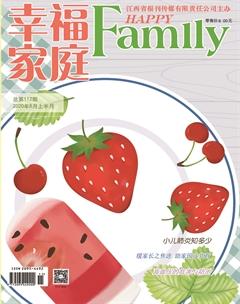談談智能手機對農村空巢老年人的積極影響
吳文云 魯冰
一天,老媽在電話中和我叨咕一遍生活瑣事后無奈地說:“現在的年輕人,連對面看見都不打個招呼。我那天坐車,上來好幾個同村的年輕人,但一路上一個人都沒有和我說話。”經過我的解釋和開導,老媽才釋然。這件事讓遠在千里之外的我感謝信息化時代,感謝智能手機。
老媽在某種意義上還不算是農村空巢老年人的典型代表,因為她還要幫忙帶孫子,這意味著她被充分需要,情感上有所寄托,生活也很充實。但她若脫離了“奶奶”的角色,比如乘車時,她就成了獨立個體,希望與他人互動。當被“外人”無聲拒絕時,她會用各種話自我安慰,但掩飾不住的是渴望與他人聯系的需要。而這種需要是精神基本需求。
基本需求就如同空氣、水和食物一般重要。在衣食無憂的年代,精神基本需求是否能被充分滿足是沒有老幼城鄉之分的。而現實中,受身心特點和生活環境等主客觀因素影響,空巢老年人群體的精神需要被忽略。
在信息化時代,老年人習慣的聯系方式——面對面交流,正在慢慢弱化。即便是生活充實、有文化的老媽,還是要借助智能手機與子女聯系,幫助她緩解寂寞、無奈的情緒。老年人太需要一個及時的“連接”,幫助他們及時聯系子女,滿足精神上的基本需求。人們要科學而多視角地了解智能手機對農村空巢老年人身心健康的具體影響和作用,并努力以智能手機為媒介推動農村空巢老年人跟上時代,樂在這個時代。
智能手機與掌控感。疫情下,老年人就醫成了大問題。健康碼、掃碼乘車、網上預約掛號……可能讓部分老年人去不了醫院等地方。當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手機掃碼”掌控時,曾經有能力的“我”什么也干不了,無能和自卑,氣憤和無奈的負面情緒就很容易出現。而面對這種情況時,老年人多是回避和退縮,會變得更加依賴子女,有的老年人甚至會產生自責和羞愧感。智能手機對生活的改變讓農村空巢老人身心都受到了束縛。掌控了智能手機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決策自己的生活,這是多么現實又迫切的身心需求。
智能手機與情感連接。在農村,針對老年群體的社區活動有限,而子女卻又常常都在外地工作和生活,很少回家。即使在節假日,由于私家車的便捷和現代生活的忙碌,子女也很少能在家里住上一晚,飯后基本就返城。與子女孫輩的情感連接也有限,彼此之間了解和共同話題越來越少,老年群體更加孤獨,很多情感和需求都壓抑在心中。智能手機的運用,比如微信朋友圈,可以讓他們及時了解子女親人的心情、生活和工作,從而可以放下他們惦記孩子的心。看到孩子的快樂和成長,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自豪感會增強,甚至花了好長時間寫上一句帶錯字的評論,也會讓他們覺得開心。他們雖然生活在小小村落和鄉鎮,但看到孩子動態時的心情是與孩子、親人同步的。這種同步就是一種活在當下的感覺,這種感覺會沖淡無望感、無用感以及焦慮無意義感。
智能手機與積極老齡化。農村的老齡化與城市老齡化有很大區別,城市更傾向于積極老齡化。城市中的老年人,琴棋書畫旅游會友,人老環境不老,更容易被環境激發出“夕陽紅”的生活。而在農村,特別是經濟欠發達的地區,老年人更多的是消極老齡化。很多老年人眼神和語氣里的無奈壓過了心底的渴望。但智能手機的普及和使用,能夠擾動空巢老年人的心。比如抖音、快手以及老朋友、老同學、老戰友或老鄰居的朋友圈和群聊,讓他們看到了同齡人原來可以活得那么精彩。也許只是群里斗斗圖,轉發幾條身心健康專家的文章或者只是點開那個引人發笑或者熟悉的老歌小視頻,但老年人的心卻被激活了,老年人想要的滋味兒就多了起來。
看到一則消息說上海某社區針對老年人進行智能手機培訓推廣,我不禁想到,針對農村空巢老人的智能手機推廣和培訓是不是也要加速開展起來呢?
(作者單位:江蘇省丹陽市訪仙鎮社區教育中心江蘇省丹陽市第六中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