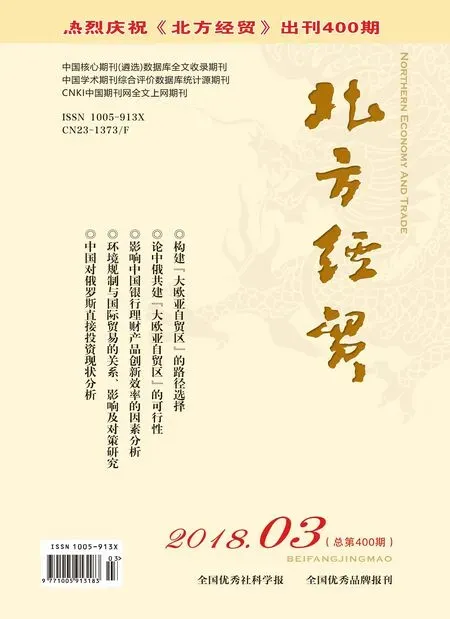濟南市政府海綿城市建設對武漢市的啟示
張 瑜
(哈爾濱商業大學,哈爾濱150028)
近年來,我國許多城市頻繁發生“城市看海”現象,城市內澇問題日益嚴重,不僅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而且對市民的人身和財產安全帶來了重大的威脅。為此,我國積極推進海綿城市建設,以期最大程度地減少城市開發和建設對城市生態環境的影響。海綿城市是一種全新的城市發展理念和建設模式,是指把城市建設得像海綿一般,讓其具有一定的“彈性”,即當遭遇雨水天氣時可以隨時將雨水進行吸收、儲蓄、滲透和凈化,當遇到長期干旱少雨天氣時又可以將儲存的雨水進行“釋放”并加以科學利用,對改善城市水生態環境,提升城市水生態安全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濟南市海綿城市建設主要做法及經驗
濟南市是全國首批海綿城市建設試點城市之一,也是全國海綿城市建設典范。為有效緩解城市內澇,改善城市水生態環境,提高居民居住質量和生活,從2015年開始,濟南市政府積極推進海綿城市建設,目前已經取得了較為明顯的成效,并且形成了可以借鑒和推廣的“濟南經驗”。截止2016年底,濟南市安排的43個試點建設項目已全部開工建設,建設面積達24.07平方公里,占全部建設項目的63%,且已經在多次強降雨天氣中經受住了考驗,發揮出了“海綿體”的重要作用。濟南市海綿城市建設的經驗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建立海綿城市建設組織機構
海綿城市建設是一個系統性、綜合性的工程,需要各相關部門和單位的協調配合。為此,濟南市政府成立海綿城市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負責統籌和協調海綿城市建設工作。該工作領導小組采用矩陣式管理架構,即在領導小組下設置了城市水系(城區水系)、城市水系(內河水系)、規劃與土地利用、道路交通和園林綠地等等八個項目部,并且對每個部門的工作任務和職責進行了明確的劃分。同時,對辦公室的工作任務與職責進行調整和完善,設置綜合組、專家組、資金組和宣傳動員組等六個職能組,從而形成了一個系統的指揮與管理體系,為海綿城市建設工作的順利開展提供組織保障。
(二)拓寬海綿城市建設融資渠道
海綿城市在前期建設和后期運營、維護方面都需要投入大量資金,僅靠政府財政投入是遠遠不夠的。為此,濟南市政府積極拓寬融資渠道,大力推廣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設立海綿城市建設專項資金,吸引社會資本參與海綿城市建設。同時,為規范海綿城市建設過程中的投資控制和資金使用,加大對資金的監管力度,真正實現專項資金的有效利用,濟南市政府出臺了《濟南市海綿城市建設專項資金管理辦法》和《濟南市市政公用行業PPP模式項目管理辦法(實行)》,為海綿城市建設的順利進行提供了資金保障。
(三)加強人才培養和技術研究
海綿城市建設專業性強、技術要求高,專業人才和技術是海綿城市建設的重要保障。一方面,濟南市政府聘請北京建筑大學專家團隊,為海綿城市建設提供技術咨詢和指導。同時,積極打造本地專業人才隊伍,通過專家講授、技術研討和專題講座等形式,對政府管理部門人員、規劃設計人員和施工人員等進行專業培訓,全面提升海綿城市專業知識,為海綿城市建設儲備人才。另一方面,濟南市政府成立海綿城市工程技術研究中心,鼓勵和扶持有能力的企業對海綿城市建設技術進行研發與推廣,科學制定海綿城市相關技術和產品的標準體系,為推進海綿城市建設提供技術支撐。
(四)倡導全民參與海綿城市建設
濟南市政府采取多種方式和通過多種渠道進行宣傳教育,向公眾普及海綿城市相關知識,如政府部門工作人員到社區、企業和學校等場所進行海綿城市知識專題講座、發放海綿城市宣傳冊等,從而提高公眾對海綿城市建設重要性的認識。同時,濟南市政府創建海綿城市官方網站,將海綿城市相關政策文件和建設進展進行信息公開,讓市民及時了解和掌握海綿城市建設的基本情況,并且網站設置留言板塊,公眾可以提出建議和意見,從而提高公眾參與海綿城市建設的積極性。
二、武漢市海綿城市建設現狀及存在的主要問題
近年來,武漢市政府積極推進海綿城市建設,通過大力整治黑臭污水、建設海綿社區和海綿學校、在道路上鋪設透水磚、建立雨水花園等方式,大大地改善了武漢市的水生態環境。但是,武漢市政府在海綿城市建設中仍然存在諸多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海綿城市建設組織機構有待健全
雖然武漢市政府成立了海綿城市建設工作領導小組,但是各部門職責分工不明確,在建設過程中易發生部門之間相互扯皮和推諉的現象,導致有事無人管或者一事多人管。同時,武漢市政府尚未將海綿城市建設管理工作納入政績考核之中,產生武漢市海綿城市建設進程緩慢、海綿體質量普遍不高且基礎設施重復建設等問題。
(二)海綿城市建設資金存在較大缺口
海綿城市建設涉及多方面的內容,如在道路上鋪設透水磚、建設下沉式綠地以及對城市自然水生態系統進行修復等,資金需求量大。雖然武漢市政府在海綿城市建設中通過政府財政投入、爭取中央財政補貼和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PPP)模式來籌措建設資金,但是目前武漢市政府財政投入有限且中央是否會繼續對海綿城市進行財政補貼尚處于未知狀態,導致資金存在一定缺口。同時,盡管武漢市政府積極推廣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但由于社會資本以盈利為目的,而海綿城市建設項目大多屬于公益項目且在短期內難以帶來經濟效益,導致社會資本參與積極性不高。
(三)海綿城市建設專業人才和技術嚴重缺失
海綿城市建設在我國剛剛起步,技術水平較為落后,專業人才嚴重短缺,難以滿足建設需求。一方面,海綿城市建設涉及專業較多,如市政工程、建筑、水利、園林設計等,并且對復合型人才的需要較大,但目前國內高校還未建立相應專業,相關課程也嚴重缺乏,未能大規模培養專業人才,導致人才供給不足。另一方面,我國對海綿城市的研究起步較晚,建設經驗和技術多借鑒國外,自主創新能力欠缺,缺乏與我國城市發展相適應的專業技術。同時,以海綿城市為研究對象的機構較少,技術力量相對薄弱,難以為海綿城市建設提供技術支撐。
(四)社會公眾缺乏海綿城市建設參與意識
海綿城市是一個全新的城市建設理念,社會公眾對海綿城市的概念、內涵、所帶來的效益等方面缺乏全面、具體的認識與了解,從而導致公眾參與熱情不高。同時,有些民眾對海綿城市建設仍然持消極態度,認為海綿城市建設是一項勞民傷財的工程且與自己的生活關系不大,直接導致海綿城市建設理念難以推廣,先進的建設技術難以得到廣泛利用,海綿城市建設進程緩慢。
三、濟南市海綿城市建設對武漢市的啟示
(一)加強海綿城市建設組織機構建設
海綿城市建設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程,政府必須發揮主導作用,需要完善海綿城市建設組織機構,加強對海綿城市的統籌與組織領導能力。武漢市政府應積極調整和完善海綿城市工作領導小組的組織構成,增設職能組,如專家咨詢組、資金管理組和檢查監督組等,對海綿城市建設進行統一領導和統一協調。要對各部門的職責進行明確劃分,確立責任主體,加強溝通與配合,形成聯動機制,避免出現多頭領導、管理混亂的現象。同時,在對政府工作人員進行政績考核時,將海綿城市建設納入考核指標之中,并降低GDP在考核指標中的權重,真正對海綿城市建設重視起來,更好地推進海綿城市工作的順利進行。
(二)多元化籌措海綿城市建設資金
海綿城市建設需要大量資金予以支持,資金的籌措對于海綿城市建設來說至關重要。一方面,武漢市政府應增加政府財政投入,在財政預算中優先考慮海綿城市建設項目,盡快出臺《武漢市海綿城市建設專項資金管理辦法》,設立海綿城市建設專項資金,專門用于海綿城市建設項目。要給予從事海綿城市建設的企業一定的稅收優惠,提高企業參與海綿城市建設積極性。另一方面,武漢市政府要逐步完善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相關制度,要明確各方責任,建立公平合理的風險分擔機制,創新收益模式,為投資企業提供收益保障,如在停車場收取停車費、實施雨水管理收費制度和在某些生態公園收取門票等。
(三)加強海綿城市建設人才和技術保障
在人才引進和培養方面,武漢市政府應根據本地實際建設需求,對所需要的人才進行科學分析和預測,明確人才引進的具體標準,定期去各大高校和人才市場召開海綿城市建設人才招聘會,主動吸引人才。要加強與武漢市內各個高校的合作交流,在高校內設置相關學科,定制人才培養計劃,簽訂定向培養合同,專門用于海綿城市建設。同時,加強對從事海綿城市建設的人員進行業務培訓,定期舉辦技術交流和研討活動,不斷提高知識水平和建設能力。
在技術研究與推廣方面,武漢市政府成立海綿城市建設技術聯盟,加強對本土技術力量的培育,積極研發新的技術和材料,不斷突破海綿城市建設中所遇到的技術難題,要加強與高校和企業進行技術交流與合作,幫助企業實現技術創新。同時,要積極推進海綿城市智慧化,利用信息技術對海綿城市各個項目進行智慧化管理,如健全雨水監測系統和遠程監測水位等。
(四)開展宣傳教育倡導全民參與海綿城市建設
從濟南市海綿城市建設經驗中可以看出,海綿城市建設不能僅靠政府單方面發揮作用,還要在全社會廣泛開展宣傳教育,讓海綿城市理念深入人心。武漢市政府應借助媒體的力量,如互聯網、電視、廣播和報刊等,對海綿城市的概念和重要性等相關知識進行宣傳,讓公眾對海綿城市建設有一定的了解。在街頭、社區和學校定期舉辦豐富多彩的宣傳互動,如知識競賽、發放宣傳資料、設置展板等,增強公眾對海綿城市的認知。同時,創建官方網站,定期發布建設進度,并且定期對居民的留言進行查看和回復,提高公眾參與積極性。
[1 ]耿 瀟,趙 楊,車 伍.對海綿城市建設PPP模式的思考[J].城市發展研究,2017(1).
[2]袁 赟,邱立平.濟南市海綿城市建設的對策研究[J].門窗,2017(1).
[3]鄭昭佩,宋德香.山地城市海綿城市建設的對策研究——以濟南市為例[J].生態經濟,2016,32.
[4]梁亞楠,周 林,武艷芳.海綿城市建設過程中的問題與對策——武漢市案例研究[J].凈水技術,20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