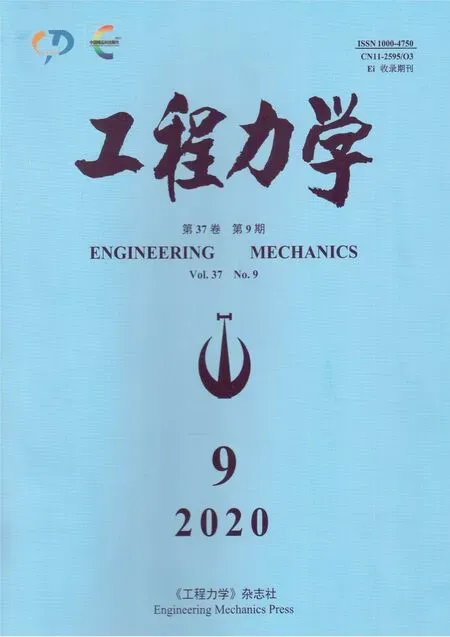內嵌鋼板及邊緣框架相互作用對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受力性能的影響
王 萌,郭勇超
(北京交通大學土木建筑工程學院,北京 100044)
隨著社會經濟不斷發展,日益增長的人口、文化、經濟等對建筑空間的需求越來越多,因此城市建筑向空間、縱向發展成為必要趨勢。在高層建筑抗側力構件中,鋼板剪力墻自20 世紀70 年代以來憑借其承載能力高、延性好、耗能能力強等優點受到大力推廣,如圖1(a)所示[1]。傳統鋼板剪力墻結構通常布置在建筑中心部分形成電梯井、設備井等。然而,隨著人們對空間靈活性要求的提高,建筑往往需要在中心部分開洞,傳統鋼板剪力墻結構的適應性有所降低。因此,學者們對帶連梁鋼板剪力墻結構開展研究工作,如圖1(b)所示[2]。帶連梁鋼板剪力墻結構通過連梁將2 片甚至多片傳統鋼板剪力墻連接在一起,改變結構耗能機制,使其協同工作。為進一步提高帶連梁鋼板剪力墻結構的抗震性能,利用低屈服點鋼材延性好、耗能能力強等優點[3?4],將低屈服點鋼材與帶連梁鋼板剪力墻結構相結合,提出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體系[5]。

圖1 鋼板剪力墻結構Fig. 1 Steel plate shear wall structures
鋼板剪力墻結構內嵌鋼板與邊緣柱、邊緣梁(以下稱:邊緣框架)的相互作用機理較為復雜[6?8],國內外學者對此開展了研究工作。Qu 等[9]基于塑性分析研究邊緣框架與內嵌鋼板對結構承載力的貢獻,并提出一種考慮邊緣框架與內嵌鋼板共同作用的設計方法。Borello 等[10?13]通過試驗及數值模擬的方法對帶連梁鋼板剪力墻受力行為及作用機理展開研究,證明帶連梁鋼板剪力墻結構抗震性能優越,且提高了建筑靈活性及材料利用率。金雙雙等[14]針對不同跨高比與內嵌鋼板厚度的單層單跨鋼板剪力墻進行靜力推覆分析,研究表明內嵌鋼板與邊緣框架剪力的疊加無法準確估計鋼板剪力墻結構水平承載力。Hosseinzade 等[15]也曾指出,多層鋼板剪力墻構件中內嵌鋼板與邊緣框架的相互作用使得結構整體承載力提高,且不是內嵌鋼板與邊緣框架承載力的簡單疊加。錢鳳霞[16]對非加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內嵌鋼板剪力分配進行研究,根據邊緣框架柱的剛度不同,內嵌鋼板剪力分配系數范圍在14%~94%。Wang 等[17]研究邊緣框架在傳統鋼板剪力墻及帶連梁鋼板剪力墻結構中的作用,根據連梁耦合度不同,內嵌鋼板分擔剪力范圍39%~60%,證明在帶連梁鋼板剪力墻體系抗震設計過程中,不能忽略邊緣框架對承載力的貢獻。目前國內外學者對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研究較少,連梁使得邊緣框架的受力行為及邊緣框架與內嵌鋼板的相互作用變得更為復雜。因此,亟需探討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內嵌鋼板與邊緣框架的相互作用機理及其對帶連梁鋼板剪力墻結構受力行為的影響。
因此,本文首先采用有限元軟件ABAQUS建立帶連梁鋼板剪力墻結構有限元模型,結合國內外典型試驗驗證有限元模型的準確性。其次設計5 個不同連梁耦合度的鋼板剪力墻模型,對比分析其承載性能、滯回性能、損傷機制等,探討內嵌鋼板與邊緣框架相互作用對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受力行為的影響,進而對此類新型結構的設計應用提供參考依據。
1 有限元模型與試驗驗證
為驗證有限元方法模擬帶連梁鋼板剪力墻結構破壞模式、承載性能及滯回性能的準確性和合理性,選取Choi 等[18]、Li 等[19]的試驗進行驗證。
1.1 有限元模型
采用通用有限元分析軟件ABAQUS 建立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模型,框架梁、框架柱、連梁、內嵌鋼板均采用殼單元(S4R)進行模擬。連梁與鋼板剪力墻肢通過Tie 命令組合。為準確模擬薄鋼板在循環往復作用下屈曲、平面外變形等非線性行為,采用ABAQUS 6.14 顯示動力模塊計算[20]。
1.2 Choi 等[18]的試驗驗證
Choi 等[18]的試驗研究了不同內嵌鋼板連接方式對鋼板剪力墻結構承載能力的影響,共設計5 個鋼板剪力墻結構試件。本次驗證選取其中帶連梁鋼板剪力墻結構試件,試件詳細尺寸及有限元模型如圖2 所示。材料參數采用文獻[18]給出的實測數據,循環加載制度與文獻保持一致。

圖2 文獻[18]試件詳細尺寸及有限元模型 /mm Fig. 2 Dimension and numerical model of specimen in reference [18]
有限元計算結果與試驗結果對比如圖3(a)所示,計算結果與試驗曲線吻合良好。典型破壞形態對比如圖3(b)所示,其中1~6 區域拉力帶發展情況基本一致,7、8 區域內嵌鋼板變形一致。對比圖說明有限元方法可以有效地模擬試件受力行為,較準確地預測試件出現損傷的位置及破壞程度。

圖3 文獻[18]試驗有限元結果對比Fig. 3 Comparison between test and numericalsimulation in reference [18]
1.3 Li 等[19]的試驗驗證
Li 等[19]的試驗驗證了所提出的帶連梁鋼板剪力墻結構設計方法的有效性。試驗采用縮尺比例制作單榀雙肢帶連梁鋼板剪力墻結構試件,試件詳細尺寸及有限元模型如圖4 所示。試驗中采用MTS 加載系統對試件施加豎向軸力、水平地震力及上部傾覆彎矩。材料參數、加載制度與文獻[19]保持一致。

圖4 文獻[19]試驗試件尺寸及數值模型 /mm Fig. 4 Dimension and numerical model of specimen in reference [19]
有限元計算曲線與試驗數據對比如圖5(a)所示,典型破壞形態對比如圖5(b)所示。從圖5(a)可知,計算得到的結構承載力略高于試驗結果,這是因為試驗過程中內嵌鋼板與邊緣框架連接處過早開裂失去承載能力。從圖5(b)可知,計算結果與試驗結果破壞形態基本吻合,其中1、2、5、6 區域有明顯的塑性發展,3、4、7、8 區域拉力帶發展情況基本一致。

圖5 文獻[19]試驗有限元結果對比Fig. 5 Comparison between test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in reference [19]
以上對比結果說明,有限元方法可以有效模擬結構的滯回行為,較為準確地預測拉力帶出現的位置及發展情況、內嵌鋼板的變形以及框架梁柱的局部屈曲現象。
2 鋼板剪力墻結構參數設計
2.1 模型參數
為研究不同連梁耦合度對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受力性能的影響,以文獻[19]試驗試件為原型,在保持墻肢尺寸不變的前提下,改變連梁截面尺寸設計5 個不同的鋼板剪力墻結構試件。包括:單肢鋼板剪力墻結構試件(SPSW);理想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試件(C-SPSW),其連梁抗彎剛度無限大,即結構性能不受連梁塑性狀態的影響;連梁彎曲破壞的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試件(C1.0);連梁彎剪混合破壞的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試件(C2.0);連梁剪切破壞的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試件(C4.0)。試件如圖6 所示,連梁的破壞模式根據連梁與相應樓層框架梁塑性抵抗彎矩的比值MpCB/MpHBE來描述,MpCB/MpHBE在C1.0、C2.0、C4.0 試件中分別為1.0、2.0、4.0。試件邊緣框架構件均采用工字形截面、內嵌鋼板采用非加勁平鋼板,其詳細尺寸如表1 所示。其中C-SPSW 試件連梁在有限元軟件中采用如下處理方法:不設置實際連梁,僅將連梁兩端相應位置使用coupling 命令耦合連接,使其運動狀態保持一致。因C-SPSW 不設置實際連梁,故其用鋼量低于C1.0、C2.0、C4.0 試件。

圖6 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試件示意圖 /mm Fig. 6 Sketch of coupled steel plate shear wall structures

表1 試件參數說明 /mmTable 1 Parameters of specimen
為探究內嵌鋼板與邊緣框架的相互作用對邊緣框架的影響,將C1.0、C2.0、C4.0、SPSW、C-SPSW 試件內嵌鋼板取出,形成純框架試件(以下簡稱:純框架,記作BF),如圖7 所示。

圖7 純框架試件示意圖 /mm Fig. 7 Sketch of bare frame
2.2 材料本構說明
試件材料參數參見文獻[19]試驗標定取值,其中內嵌鋼板采用LYP225 低屈服點鋼材,fy=220 MPa,fu=288 MPa。框架梁、柱及連梁均采用Q345 鋼材(fy=345 MPa)。
2.3 加載制度
為研究內嵌鋼板與邊緣框架相互作用對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受力性能的影響,對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進行單調靜力推覆分析及循環加載分析。GB 50011?2010《建筑抗震設計規范》[21]規定,多高層鋼結構彈塑性層間位移角限值為0.02 rad,為驗證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具有高效的承載性能,結構位移角(頂端位移除試件高度)最大為0.045 rad。所有模型在試件頂端施加如圖8 所示位移加載制度。其中位移幅值分別取0.1 倍、0.2 倍、0.3 倍、0.5 倍、0.75 倍、1 倍、1.5 倍、2 倍、3 倍、4 倍、5 倍C1.0 試件屈服位移(43.4 mm)和結構位移角為0.045 rad 時結構頂層位移,每級循環2 次。

圖8 荷載加載制度Fig. 8 Loading pattern
3 內嵌鋼板及邊緣框架相互作用對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受力性能影響
3.1 承載性能影響分析
3.1.1 承載能力及破壞模式分析
圖9 為5 個試件單調靜力推覆的破壞形態,從連梁狀態可知試件實現了預期的破壞模式:C1.0 試件連梁表現為明顯的彎曲破壞,兩端形成塑性鉸;C2.0 試件連梁表現為彎曲、剪切混合破壞;C4.0 試件連梁以剪切破壞為主。圖10 所示為結構剪力分配情況及各構件破壞順序。
結合圖9 及圖10 分析可知,鋼板剪力墻結構受力全過程可分為以下幾個階段(其中A點、B點、C點、D點分別代表內嵌鋼板、連梁、框架梁、框架柱開始屈服的位置):在加載初期彈性階段,內嵌鋼板提供大部分抗側剛度,幾乎承擔全部剪力。由于內嵌鋼板采用低屈服點鋼材,伴隨加載位移的不斷增大,內嵌鋼板最先屈曲、屈服,此時邊緣框架仍處于彈性工作狀態;隨著加載位移的進一步增大,內嵌鋼板全面屈服,拉力場充分發展,隨之框架梁、連梁端部屈服,出現塑性鉸,邊緣框架承擔剪力逐漸增加;最后邊緣柱底區域逐漸屈服,進入塑性階段。不同連梁耦合度結構邊緣框架的屈服順序不同:C1.0 試件連梁最先屈服出現塑性鉸,然后框架梁開始屈服;C2.0、C4.0 試件的框架梁先進入塑性,隨后連梁屈服(C4.0 試件連梁剪切屈服晚于C2.0 試件),最后框架梁柱連接處出現塑性鉸;C1.0、C2.0、C4.0 試件柱底區域均最后屈服,同時外側框架柱塑性發展明顯大于內側框架柱。根據結構達到最大位移時的應變分布,內嵌鋼板的最大應變遠小于低屈服點鋼材的伸長率[5?7],有效提高結構延性。上述現象說明,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是具有多道抗震防線、有效保護豎向承重構件的結構形式,易形成“墻板—梁(框架梁及連梁)—柱”延性損傷控制機制。

圖9 試件破壞形態Fig. 9 Failure modes of specimens
由圖10(a)、圖10(d)、圖10(g)、圖10(j)及圖10(m)試件總剪力曲線對比可知:在墻肢相同的前提下,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水平承載力遠大于傳統鋼板剪力墻結構;且隨著連梁耦合度的提高,試件水平承載力不斷增加,承載效率提高。根據表1 可知,C2.0、C4.0 試件相較于C1.0試件用鋼量分別增加3.45%、8.21%,將承載效率定義為單位質量(kg)鋼材提供的抗側力(kN),C1.0、C2.0、C4.0 試件承載效率分別為0.75、0.78、0.81。
以上結果表明,隨著連梁耦合度的提高,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邊緣框架整體性加強,體系協同工作性能提高。在內嵌鋼板不變的前提下,二者的相互作用提高了結構的承載力及承載效率,并改變構件屈服順序、優化損傷機制,保證承重構件承載性能充分發揮。
3.1.2 對剪力分配影響分析
內嵌鋼板與邊緣框架分別承擔剪力及純框架承擔剪力對比曲線如圖10(a)、圖10(d)、圖10(g)、圖10(j)及圖10(m)所示,其中T 代表整體結構,P 代表內嵌鋼板,F 代表框架,BF 代表純框架。為進一步揭示內嵌鋼板與邊緣框架相互作用對剪力分配的影響,試件各層內嵌鋼板與邊緣框架承擔剪力比值如圖10(b)、圖10(e)、圖10(h)、圖10(k)及圖10(n)所示,試件各層內嵌鋼板與總剪力比值如圖10(c)、圖10(f)、圖10(i)、圖10(l)及圖10(o)所示。由圖10(a)、圖10(d)、圖10(g)、圖10(j)及圖10(m)各部分承擔剪力曲線可知,塑性穩定發展后,五個試件內嵌鋼板承擔剪力基本保持一致,均為940 kN 左右;而隨著連梁耦合度的增加,邊緣框架承擔剪力明顯增大。由圖10(c)、圖10(f)、圖10(i)、圖10(l)及圖10(o)內嵌鋼板承擔剪力比例可知,塑性穩定發展后,傳統單肢鋼板剪力墻內嵌鋼板承擔總剪力的62%;隨著連梁耦合度提高,邊緣框架整體作用不斷增強,邊緣框架承擔剪力增加,內嵌鋼板承擔剪力比例不斷減少,C4.0 試件中內嵌鋼板僅承擔總剪力36%,但內嵌鋼板承擔剪力的減小是有限的,C-SPSW 試件內嵌鋼板承擔剪力比例最少約為總剪力34%。利用上述分析數據,使用數學優化分析軟件1stOpt,采用麥夸特法(Levenberg-Marquardt)優化算法建立連梁與相應樓層框架梁塑性抵抗彎矩比值MpCB/MpHBE與內嵌鋼板承擔剪力比例VP/VT關系如下式:

圖10 內嵌鋼板剪力分配及各構件損傷順序Fig. 10 Shear distributions of SPSW structures and damage sequence of each component

擬合曲線與原始數據對比如圖11 所示,均方根誤差為2.76×10?6;相關系數接近于1.0,說明表達式可以較好地預測MpCB/MpHBE與VP/VT之間的關系。

圖11 MpCB/MpHBE 與VP/VT 關系擬合Fig. 11 The fitting result between MpCB/MpHBE and VP/VT
由圖10(a)、圖10(d)、圖10(g)、圖10(j)及圖10(m)結構邊緣框架承擔剪力與純框架承擔剪力對比曲線可知:傳統鋼板剪力墻結構(SPSW)邊緣框架承載力與相應純框架的承載力基本一致,而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邊緣框架承載力明顯大于相應純框架的承載力,且連梁耦合度增加,承載力差異增大,C1.0、C2.0、C4.0、CSPSW 試件框架承載力分別比相應純框架承載力提高5.14%、7.02%、9.74%、36.35%。同時,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構件邊緣框架初始抗側剛度也明顯大于相應純框架。
在傳統鋼板剪力墻設計時,通常認為內嵌鋼板承擔全部剪力,不考慮邊緣框架對承載力的貢獻[22]。但上述分析結果表明: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內嵌鋼板與邊緣框架的相互作用,可以有效提高邊緣框架初始抗側剛度及承載力,在塑性穩定發展以后邊緣框架能夠承擔比內嵌鋼板更多的剪力。因此,在對此類結構進行設計時,建議同時考慮邊緣框架與內嵌鋼板對抗側力的貢獻,進而減小內嵌鋼板設計厚度,優化邊緣框架截面尺寸,獲得更高材料利用率與設計經濟性。
3.1.3 對構件內力影響分析
類比混凝土聯肢墻可知,在水平荷載作用下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與傳統鋼板剪力墻結構受力如圖12 所示:傳統鋼板剪力墻僅靠墻肢截面抵抗矩抵抗側向力所產生的彎矩[23];而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可依靠各墻肢截面抵抗矩及墻肢軸力形成的力偶來抵抗水平力產生的彎矩[23?24]。

圖12 聯肢剪力墻在水平荷載作用下受力模式Fig. 12 Lateral force resisting mechanism of SPSW
將墻肢產生的彎矩記為Mpier、軸力記為Npier,連梁產生的附加彎矩記為MCB。連梁附加彎矩為墻肢軸力與墻肢凈距的乘積,如下式所示:
式中:L為墻肢寬度;e為墻肢間距[17]。
連梁耦合度表示連梁對結構整體性貢獻大小,通常定義為連梁附加彎矩MCB與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總傾覆力矩Mtotal的比值,如下式所示:

提取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墻肢軸力Npier及彎矩Mpier,如圖13 所示。隨著耦合度的提高,Npier逐漸增大,Mpier逐漸減小。當結構位移角達到0.03 rad,C2.0 試件軸力相對于C1.0 試件增加50%,彎矩減小8.1%;C4.0 試件相對于C2.0 試件軸力增加76.5%,而彎矩減小15.4%。這說明連梁耦合度變化主要影響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的墻肢軸力,而對墻肢彎矩影響較小。

圖13 墻肢內力分布Fig. 13 Axial force and bending moment of piers
為進一步分析連梁耦合度對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構件內力的影響,分別提取3 個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框架柱的軸力及彎矩如圖14 所示(柱編號如圖12 所示)。

圖14 框架柱內力分布Fig. 14 Internal forces of columns
對比框架柱的軸力、彎矩可知,連梁耦合度變化對外部邊緣柱(1、4)的影響明顯小于對內部邊緣柱(2、3) 的影響。C2.0 試件內柱彎矩比C1.0試件內柱彎矩增大約11.7%,而軸力減小約26.4%;C4.0 試件內柱彎矩比C2.0 試件內柱彎矩增大約9.3%,而軸力減小約56.9%。
因此,結合墻肢內力及邊緣柱內力分析可知,連梁耦合度改變了邊緣框架受力性能,從而改變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的內力分布,減小框架柱軸力,其中邊緣內柱減小程度高于邊緣外柱,因此在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設計過程中,應考慮耦合度變化對柱截面內力的影響,適當減小內柱截面尺寸,以提高材料利用率。
圖15 所示單調加載過程中連梁耦合度的變化:C1.0、C2.0、C4.0 的耦合度在加載初期均有增長,結構位移角達到0.005 rad 以后,C1.0、C2.0試件耦合度出現下降,C1.0 下降程度大于C2.0,C4.0試件則繼續保持增長趨勢。這是因為C1.0 試件連梁相對墻肢較弱,加載初期連梁先于墻肢屈服,隨后墻肢為主要構件抵抗外力;C2.0 試件連梁剛度有所提升,C4.0 試件連梁剛度最大,連梁可以持續參與到抵抗外力的過程中,邊緣框架提供更多的承載力貢獻。

圖15 連梁耦合度Fig. 15 Degree of coupling
學者El-Tawil 等[25]指出:混凝土聯肢墻連梁耦合度一般不低于0.3,上限值通過限制墻肢軸力值來確定。連梁耦合度反映聯肢墻的協同工作性能與經濟性,耦合度越大,體系協同工作性能越好,但無限增大連梁剛度可能造成在水平荷載作用下墻肢先于連梁屈服,無法充分發揮連梁耗能及“保險絲”作用。當耦合度過小時,結構將過早始失去協同工作優勢。由3.1.1 節承載能力分析可知,C-SPSW 試件承載力是C4.0 試件的1.06 倍,因此,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極限水平承載力不會隨連梁塑性抵抗矩的無限增大而無限增大,綜合材料利用率與承載能力建議連梁耦合度控制在0.45 以內。
3.1.4 連梁轉角分析
連梁轉角是評判帶連梁鋼板剪力墻結構受力行為的指標之一,按照圖16 將每一層墻肢轉動角度定義為θpier,i,連梁兩端相對轉角定義為θv,i,連梁相對于初始狀態發生的總轉角定義為θCB,i[17]。

圖16 連梁轉角示意圖[17]Fig. 16 Definition for rotation of coupling beams[17]
C1.0、C2.0、C4.0 試件在單調水平荷載作用下連梁轉角如圖17 所示,C1.0 試件連梁轉角最大,C4.0 試件連梁轉角最小。墻肢轉角θpier,i幾乎不隨連梁耦合度變化而變化,內部邊緣柱運動引起連梁轉動θv,i隨連梁耦合度的增加而減小。由3.1.3 節分析可知,隨著連梁耦合度的提高,內部邊緣柱軸力下降,彎矩變化不大,這導致內部柱豎向位移減少,進而引起連梁轉動減小,保證結構在水平荷載作用下有較好的整體性。因此,在設計使用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時,建議適當加大連梁耦合度以減小連梁在水平荷載作用下的轉動。

圖17 連梁轉角Fig. 17 Rotation of coupling beams
3.2 滯回性能影響分析
為評估內嵌鋼板與邊緣框架相互作用對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滯回行為及耗能能力的影響,按圖8 所示加載方式對試件進行低周往復加載。
3.2.1 對剪力分配影響分析
試件整體滯回曲線如圖18(a)、圖18(d)、圖18(g)、圖18(j)及圖18(m)所示。為進一步揭示鋼板剪力墻結構剪力分配情況,底層內嵌鋼板承擔剪力如圖18(b)、圖18(e)、圖18(h)、圖18(k)及圖18(n)所示,底層框架與純框架剪力對比如圖18(c)、圖18(f)、圖18(i)、圖18(l)及圖18(o)所示,其中F 代表鋼板剪力墻中的邊緣框架,BF 代表純框架。
從圖18(a)、圖18(d)、圖18(g)、圖18(j)及圖18(m)試件整體滯回曲線可知:與單肢鋼板剪力墻SPSW 試件相比,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承載力顯著提高,且隨著連梁耦合度的增加,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整體承載力增加,C4.0 試件承載力約為SPSW 試件兩倍,同時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的滯回曲線更飽滿。

圖18 循環荷載下試件剪力分配Fig. 18 Shear distribution of SPSW structures under cyclic loads
從圖18(b)與圖18(c)、圖18(e)與圖18(f)、圖18(h)與圖18(i)、圖18(k)與圖18(l)、圖18(n)與圖18(o)鋼板剪力墻結構內嵌鋼板與邊緣框架承擔剪力的對比可知:在循環荷載作用下,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框架承擔剪力明顯大于內嵌鋼板承擔剪力,且框架滯回曲線呈飽滿的梭形;而內嵌鋼板由于在反復加載過程中發生不可恢復的面外變形及局部屈曲,滯回曲線呈現“捏攏”現象。
從圖18(c)、圖18(f)、圖18(i)、圖18(l)及圖18(o)鋼板剪力墻邊緣框架滯回曲線與純框架滯回曲線的對比可得:內嵌鋼板能夠提高邊緣框架的彈性剛度及承載力,且隨著耦合度的增加,提高效果越明顯。
3.2.2 對構件內力影響分析
提取循環加載過程中墻肢軸力與彎矩,如圖19 所示。墻肢軸力滯回曲線呈現飽滿的梭形,而墻肢彎矩滯回曲線呈現“捏攏”現象。與單調荷載作用下規律相同,隨著連梁耦合度的提高,墻肢軸力有明顯提升,而彎矩變化較小。

圖19 循環荷載下墻肢軸力與彎矩Fig. 19 Axial force and moment of piers under cyclic loads
為探討循環荷載作用下連梁耦合度對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框架柱內力的影響,邊緣柱1、2 內力滯回曲線如圖20 所示。

圖20 循環荷載下框架柱內力分布Fig. 20 Internal forces of columns under cyclic loads
與單調荷載作用下邊緣柱內力表現出一致的規律,邊緣柱1、2 的彎矩與邊緣外柱1 的軸力變化不大,而邊緣內柱2 的軸力隨耦合度增大有明顯減小。因此,在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設計過程中應考慮相互作用對整體結構受力性能的影響,合理設計耦合度,減小內柱的截面尺寸,提高經濟性。
3.2.3 對耗能行為影響分析
分別提取鋼板剪力墻結構各組件在循環荷載作用下耗散能量情況,如圖21 及圖22 所示,其中W 代表整體結構耗能、F 代表體系框架耗能、P 代表內嵌鋼板耗能、CB 代表連梁耗能。

圖21 各組件耗能對比Fig. 21 Energy dissipation of components
由圖21(a)、圖21(b)、圖21(c)與圖21(e)對比可知:在墻肢等寬的前提下,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總耗能遠大于單肢鋼板剪力墻結構。在位移角0.045 rad 處,C1.0、C2.0、C4.0 試件內嵌鋼板耗能略低于C-SPSW 試件內嵌鋼板耗能,略高于SPSW試件內嵌鋼板耗能。C1.0 連梁耗能約687 kN·m,C2.0 連梁耗能約1205 kN·m,C4.0 連梁耗能為1052 kN·m。以上結果表明:隨著連梁耦合度的增加,邊緣框架整體性增強,內嵌鋼板與邊緣框架相互作用可以提高邊緣框架耗能能力,但當耦合度增加到0.4 左右,耗能能力增幅減緩。
由圖21 各組件耗能對比及圖22 各組件耗能比例可知:在水平荷載作用下內嵌鋼板最先進入塑性狀態開始耗能,隨著荷載的進一步增加,連梁與邊緣框架幾乎同時開始參與耗能,結合3.1.1 節破壞模式分析可知,C1.0 試件連梁先屈服繼而邊緣框架梁屈服,C2.0、C4.0 則是邊緣框架梁先屈服繼而連梁屈服。這與單調荷載作用下體系屈服機制的發展規律一致,實現了內嵌鋼板-連梁(邊緣框架梁)-邊緣框架柱腳的預期破壞順序及破壞模式。

圖22 各組件耗能比例Fig. 22 Energy dissipation proportion of components
圖21、圖22 中紅色豎虛線為邊緣框架耗散能量超過內嵌鋼板耗散能量的位置,從圖中可得:單肢鋼板剪力墻結構主要由內嵌鋼板耗能,SPSW試件位移角達到0.045 rad 時,內嵌鋼板耗能占結構總耗能54%。而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在位移角達到0.02 rad 以前,主要由內嵌鋼板耗能來保護整體結構,其中C1.0、C2.0、C4.0 試件在位移角為0.02 rad 時內嵌鋼板耗能分別占總耗能58%、48%、52%,當結構位移角超過0.02 rad以后,邊緣框架耗能逐漸增多,塑性穩定發展以后邊緣框架耗能占總耗能比例遠超過內嵌鋼板耗能占比,試件位移角在0.045 rad 時,C1.0、C2.0、C4.0 內嵌鋼板耗能分別占總耗能35%、27%、28%。說明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框架充分利用框架與內嵌鋼板的相互作用,優化損傷機制及耗能性能。
4 結論
本文采用數值模擬的方法對5 個不同耦合度的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工作機理展開分析,研究內嵌鋼板與邊緣框架相互作用對其受力性能的影響,得出如下結論:
(1)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水平承載力及耗能能力大于傳統鋼板剪力墻結構。且隨著連梁耦合度的增加,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體系協同工作性能提高,其承載力、耗能能力不斷增加。綜合材料利用率、承載能力及耗能能力,建議連梁耦合度控制在0.45 以內。
(2)結合破壞模式及耗能行為分析,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具有多道抗震防線,有效保護豎向承重構件,易形成“墻板-梁(框架梁及連梁)-柱”延性損傷控制機制。同時,充分利用邊緣框架與內嵌鋼板的相互作用,優化破壞模式及耗能行為。
(3)傳統鋼板剪力墻結構在塑性穩定發展后,邊緣框架承擔38%的水平剪力;而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邊緣框架最多可承擔總剪力的60%。因此,在對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設計過程中,建議同時考慮邊緣框架與內嵌鋼板對抗側力的貢獻,進而減小內嵌鋼板設計厚度,優化邊緣框架截面尺寸,獲得更高材料利用率。
(4)隨著耦合度的提高,邊緣框架內柱的軸力有明顯降低,而彎矩變化較小。因此,應適當減小內柱截面尺寸,提高材料利用率。
(5)帶連梁低屈服點鋼板剪力墻結構試件C1.0、C2.0、C4.0、C-SPSW 框架承載力分別比相應純框架極限承載力提高5.14%、7.02%、9.74%、36.35%,說明內嵌鋼板與邊緣框架的相互作用有效提高了邊緣框架的初始抗側剛度及承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