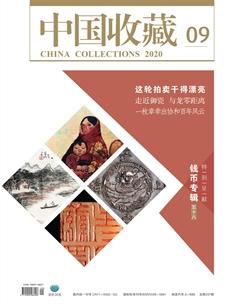臺兒莊大捷的嘉獎
韓英麒
抗日名將龐炳勛在臺兒莊大戰期間死守臨沂,功勛卓著。然而長久以來對其“為國流血紀念”章的研究卻處于空白,以至在網絡如此發達的今天,仍然難尋得勛章頒行背景的蛛絲馬跡。而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使賦閑在家的筆者偶得一枚帶有“為國流血紀念”“軍團長龐炳勛贈”字樣的抗戰紀念章(圖1)。筆者在對大量史料、勛章實物、地方志進行考證后,對該勛章的頒行地點及背景做出推斷——此章為臺兒莊大戰臨沂保衛戰期間頒行。

圖1 龐炳勛“為國流血紀念”章
鎖定臨沂
龐炳勛(1879年至1963年),字更陳,河北新河人。歷任國民革命軍第40軍軍長、第三軍團軍團長、第24集團軍總司令等職。1938年3月龐部奉調古稱瑯琊的臨沂,參加臺兒莊會戰,固守魯南重鎮。與來援的張自忠部59軍共同擊潰板垣師團之坂本旅團,為臺兒莊大捷奠定了基礎。臨沂大捷后,《大公報》也以《臨沂之捷》發表社論,予以高度評價。
龐炳勛任軍團長期間常駐臨沂,為勛章頒行地確認提供了有力佐證。1937年12月,他調歸第五戰區指揮,后升任第三軍團軍團長;1938年2月便被調往臨沂參加臺兒莊會戰,直至1939年9月升任第24集團軍總司令,不再稱軍團長。“為國流血”必指抗戰,而任軍團長期間,龐部常期在臨沂駐扎,對日作戰中也沒有取得除臨沂戰役外的大規模軍事勝利。于龐部而言,頒行此章的本質是為了犒賞將士、表彰戰功,筆者因此斷定龐炳勛“為國流血紀念”章是為紀念兩次臨沂保衛戰勝利而頒發的。
臨沂大捷于40軍意義重大,龐部兩次守城代價慘重,在臨沂頒行勛章嘉獎士卒,紀念“為國流血”的可能性最大。“年年當雜牌,天天孤哀子,不求向上爬,但愿不餓死。”龐炳勛原為馮玉祥轄下的雜牌軍,抗戰早期險遭遣散。所謂第三軍團實際也只轄40軍一軍,而臨沂保衛戰期間40軍“以久戰疲憊之將士、殘破之武器”固守日精銳師團進犯的臨沂城近兩月,傷亡慘重、險遭覆滅。此戰后40軍原有一個師兩個旅的兵力銳減到不足一個旅,幾近失去作戰能力。
臨沂戰役對40軍而言意義重大,一方面該軍為圍殲臺兒莊日軍爭取了時間;另一方面,如此大的兵員虧損也需要主帥適時地鼓舞士氣,盡快恢復建制。龐炳勛早年以善于保存兵力著稱,在軍中素有榮辱與共的傳統。他能與士兵同甘共苦,將士在戰火中被沖散、被敵所俘,一有機會都會潛返歸隊。40軍以如此大的傷亡數字搏得慘勝,他必然要對將士有所交代。據此分析,大捷后不失時機地頒發勛章祭奠亡靈、撫恤家屬、嘉獎傷員,以期恢復部隊士氣,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對勛章所刻“為國流血紀念”的合理詮釋。

圖2 2019年河南關愛抗戰老兵公益團隊為原國民革命軍第40軍抗戰老兵頒發的紀念勛章。
口述佐證
據時任40軍野戰補充團連長李宗岱回憶:“3月18日,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將軍特派員到臨沂第一線各部慰問并發了犒賞,除授給我兩枚獎章外,還特別對我連扼守葛溝的戰斗功績給予嘉獎”(《血戰臺兒莊——國民黨高級將校抗日戰爭親歷記》)。文中所提“兩枚獎章”是40軍官兵回憶錄中為數不多的線索,而對龐炳勛“為國流血紀念”章地點及背景的定性提供了重要現實參考的,是2019年河南關愛抗戰老兵公益團隊為40軍抗戰老兵頒發的紀念勛章(圖2)。
此紀念章完全以龐炳勛“為國流血紀念”章為模板進行復制,而40軍最榮耀、最值得銘記的獎章頒行必起于臺兒莊大戰臨沂保衛戰。由此推斷,當年李宗岱所受的兩枚獎章中應有一枚為龐炳勛“為國流血紀念”章。
兩種版別
龐炳勛“ 為國流血紀念”章直徑約4.8厘米、厚0.16厘米、重約16.6克,因沿用清末民國流行的銅制琺瑯工藝,受保存狀態影響尺寸差異較大(琺瑯脫落、磨損等)。在對該勛章的收藏研究過程中,筆者發現該章至少存在兩種版別,區分點主要有兩處,一處在勛章背面落款處,另一處則在“為國流血紀念”的“念”字上。

版別1正面“念”字的“人”下無“、”(圖3-1),背面為橫向打制的“漢謙和永”落款(圖3-2)。而版別2正面“念”字為正常書寫(圖4-1),背面為縱向打制的“謙和永造”(圖4-2)。且版別2較版別1多見,存世品相也相對較差。筆者認為產生版別差異的原因,應為外包廠商或銀樓下屬供應商不同所致。關于“謙和永”歸屬于何地現已難考,一說在湖北武漢,但無資料佐證,僅供參考。

由于當年臨沂抗戰的40軍官兵多已辭世,受后續兵源參軍年限不一、文化程度有限等客觀限制,已很難得到該勛章頒行背景的準確信息。筆者對勛章頒行地點及背景進行的還原,既是對歷史史實的尊重,更表達了一名臨沂人對龐炳勛將軍抗戰守土的敬重之情。希望拙文能夠填補龐炳勛臨沂抗戰期間頒發勛章資料的空白,為臺兒莊大戰史料的補充貢獻筆者的綿薄之力。